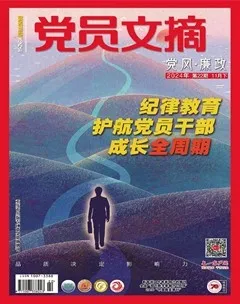謹防“非升即走”走偏
近年來,“雙一流”等重點高校借鑒國外經(jīng)驗改革教師人事制度,推行以“非升即走”為主的“準聘—長聘制”。
但部分高校把“非升即走”異化為競逐“科研GDP”的工具,存在淘汰率較高、以論文和項目為主的考評體系相對單一等情況,引發(fā)較大爭議。
一些高校“非升即走”出現(xiàn)異化
今年,部分高校“非升即走”讓一些青年教師承壓等話題受到社會關(guān)注。“非升即走”簡單說就是學校保障“準聘”學者的生活和科研待遇,學者需限期拿出代表性成果以獲得“長聘”。
隨著越來越多“雙一流”乃至部分地方院校推行“非升即走”,這一旨在激發(fā)教師創(chuàng)新活力的改革舉措,在一些高校變形走樣。
一方面,“走”的比例過高。
此前有媒體報道,南方某高校曾以“特聘研究員”“師資博士后”等名義,6年引進8000余人,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能留下。
東部一所水利高校商學院的留美海歸剛剛經(jīng)歷“走”的全過程,“7月初學校人力資源處通知我不再續(xù)聘,8月就停了工資和五險一金”。
另一方面,“升”的標準較為單一。
“‘非升即走’說起來簡單,只要6年內(nèi)評上副高就行,但難點是‘國字號’基金項目中標率很低。我的課題經(jīng)費、論文數(shù)量都夠,就缺‘國自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所以一直評不上副高。”一所“211”高校的90后講師說。
實際上,高校青年教師不僅要忙科研,還需承擔教學和日常管理事務,但一些學校的考評指標對這些方面體現(xiàn)較少。
“作為一名教師,我肯定想把課上好,備課至少要花掉全年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但在考評指標里,一學期上兩門專業(yè)課的評分,不如發(fā)表一篇C刊論文。這種‘重科研輕教學’的考評導向,我感覺不太合理,用心教學沒有得到公允的評價。”一所“雙一流”高校90后講師說。
“非升即走”變味侵蝕高校生態(tài)
大學應當是全心全意做學問、面對誘惑不盲從的地方,一些高校目前的考評導向在一定程度上誘發(fā)了侵蝕創(chuàng)新精神、學術(shù)“近親繁殖”、輕視教學育人等消極現(xiàn)象。
上海交通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楊希對1099名高校理工科教師的問卷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準聘—長聘制”改革后,教師群體的職業(yè)不安全感增強,對失敗的容忍度下降,為了保證準聘期內(nèi)有成果產(chǎn)出,或多或少“不敢”嘗試新方向或新方法。
東南大學數(shù)學學院副研究員孫燁通過挖掘論文數(shù)據(jù)庫,分析了近900萬篇論文署名和引用信息中包含的24.5萬組師生關(guān)系。結(jié)果顯示,學術(shù)成就呈現(xiàn)出一定的繼承模式。
此外,一些高校“非升即走”的考評“指揮棒”輕視教學育人的情況,進一步加劇了教學和科研“兩張皮”現(xiàn)象。有的教師不愿花太多精力備課,有的教師日常對學生的思想動態(tài)關(guān)心不夠。
廣東金融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陳蘊哲觀察到,這一矛盾在思政領(lǐng)域更為突出。“上好思政課關(guān)鍵是溝通心靈,需要教師以身作則,走到學生中間。”陳蘊哲說,一些青年思政教師不得不將重心放在申報項目、發(fā)論文、拿獎項上,課堂教學質(zhì)量難以保證。
多措并舉規(guī)范“非升即走”
平衡好激勵和淘汰的關(guān)系,合理確定淘汰比例。
“大學治理現(xiàn)代化不能狹隘理解為企業(yè)化,‘準聘—長聘制’也不等于‘非升即走’。”陳蘊哲建議,聘任制改革宜分類施策,明確哪些高校、學科宜于試點,科學設定淘汰率;針對部分高校“非升即走”引發(fā)的法律爭議,教育、人社等部門組織專項整治,全面審視聘用合同、考評體系是否合理、合規(guī)。
遵循人才成長規(guī)律,彈性設置準聘期。
蘇州大學東吳智庫副理事長陳一建議各學科根據(jù)自身實際,在6年準聘期的基礎上彈性安排,學校、院系也應為新進教師提供完善的科研配套條件,特別是以“老帶新”等方式幫助他們盡快融入。
在教師考評方面立體多維,培育“教研相長”的高校生態(tài)。
“教書、科研和管理,都是高校教師的工作內(nèi)容。大學既需要科學家也需要教育家,科學家當然可以同時成為教育家。”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事處處長、高級人才辦公室主任崔海濤建議,“破立結(jié)合”推進教師評價改革,一方面突出教書育人導向,另一方面實行多維綜合評價,完善包含教學、管理等事務在內(nèi)的立體評價體系。
陳蘊哲還表示,有不少學科存在知名學者同時牽頭多個省部級以上課題、青年學者多年未中一題的情況。因而,需為青年學者存留發(fā)展空間,如在立項環(huán)節(jié)為他們開辟專門賽道。
此外,針對我國高校師資供求失衡存在地域差異的情況,中西部不少高校仍面臨人才缺口,需重點增強其人才吸引力。
(摘自《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