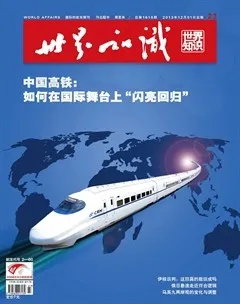特朗普“叫停”烏克蘭危機尚無清晰路徑
早在2023年5月,仍在競選狀態的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就開始在媒體上談起推動俄羅斯與烏克蘭立即停火的好處。此后,特朗普的觀點日漸明晰,成為主張美國停止援助烏并對俄妥協的“旗手”。后來,隨著特朗普當選概率的不斷走高,烏克蘭政府對于美國對烏政策大調整的憂慮與日俱增。烏總統澤連斯基在2024年9月訪美時,公開批評特朗普團隊提出的各種促談想法“過于激進”,并專門訪問了關鍵搖擺州賓夕法尼亞的斯克蘭頓陸軍彈藥廠,被美國共和黨人指責替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助選”。隨即,“上任后將在一天之內結束俄烏戰爭”成為特朗普的口頭禪,但對于如何實現這一點,他卻始終諱莫如深。在烏克蘭和西方其他國家,很多人并不認為特朗普是在“說大話”,而是真的在為切斷對烏援助、徹底拋棄烏克蘭做輿論鋪墊。
如今,特朗普贏下大選,眾多跡象顯示他上臺后將把了結烏克蘭危機視為最優先事項,其如何兌現相關競選承諾也就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迄今為止,特朗普本人仍未詳細說明到底會拿出什么樣的施壓促談方案,外界只能從其團隊和用人入手加以推測。
并非單方面“棄烏”
在烏克蘭問題上,特朗普陣營中談得最清楚的可能是退役陸軍中將基斯·凱洛格。他在特朗普首個總統任期內擔任過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主任和副總統彭斯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當年在弗林等人辭職時多次被視為接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熱門人選。2024年4月,由眾多特朗普主義者占據的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出臺了一份題為《美國優先,俄羅斯及烏克蘭》的研究報告,作者是凱洛格和同樣在特朗普首任擔任過白宮國安會辦公室主任的弗雷德里克·弗萊茨。兩人在報告中提出了對烏政策六項基本點,前三點關乎美國對烏政策的基本目標和手段,后三點關乎實現和平的具體條件:其一,將戰略目標由求勝轉為促和;其二,改變之前“由烏克蘭自由決定和平條件,美國始終給予支持”的立場;其三,如果烏克蘭拒絕和談,美國應以停援作為施壓籌碼,而如果俄羅斯拒絕和談,美國則以繼續援烏作為施壓籌碼:其四,烏克蘭應接受損失領土的現實,但不必在法理上放棄主權;其五,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但應獲得全面和可驗證的安全保障;其六,俄烏雙方應先停火和建立非軍事區。7月,凱洛格還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更詳細地說明了自己的促談方案,強調促談并非單方面對烏施壓,絕非“一棄了之”,也包括對俄施壓。凱洛格還尖銳批評了拜登政府“在該援助的時候不援助”,聲稱如果一年半之前美國就向烏提供足夠多和遠的進攻性武器,那么完全有可能借助赫爾松戰役切斷俄方戰線并扭轉戰局。
與特朗普看似“不著邊際”的模糊表態相比,凱洛格和弗萊茨的報告更加全面縝密,可謂“能進能退”:一方面,報告提出的方案能夠兌現特朗普的競選承諾,滿足選民期待;另一方面,不至于讓特朗普二任顯得完全將美國的國內政治凌駕于全球戰略利益之上。此后,包括副總統候選人萬斯在內,特朗普陣營的不少成員都在烏克蘭問題上做出表態,基本上沒有提供超出或者細化凱洛格和弗萊茨“六點”的內容。直到特朗普勝選后,才開始有更多實質性信息釋放出來。
與之前公開發布署名報告不同,新的信息是由所謂“匿名的知情人士”告知《華爾街日報》,從三個方面細化了凱洛格的方案:其一,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進程“凍結”20年,這并非做出北約不會接納烏克蘭的永久承諾,且在停火后烏會得到持續軍備援助以增強自身防衛能力;其二,雙方沿著現有戰線就地停火;其三,停火后雙方建立800英里長的“去軍事化地帶”,由德國、法國、英國、波蘭等歐洲國家派出維和部隊,確保烏邊境安全。與7月的報告相比,細化后的方案相對更有利于烏克蘭,因其就對烏安全保障問題做出了更具體的承諾,也沒有完全斷絕烏加入北約的希望。11月12日,特朗普宣布提名佛羅里達州共和黨國會眾議員邁克·沃爾茲出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就在被提名前,沃爾茲剛剛就烏克蘭問題接受了媒體采訪,表示美國有將俄羅斯帶上談判桌的“杠桿”,如其拒絕談判,美國將解除對烏利用美國提供的遠程武器打擊俄縱深目標的限制。
從現有信息看,特朗普的促談決心并不足以被解讀為“單方面棄烏”或將任由俄贏得對烏戰略勝利。從目標上看,特朗普的國家安全團隊并沒有改變將俄視為“戰略威脅”的立場,而是強調要接受現實、“及時止損”,仍致力于將烏克蘭的大部分留在西方陣營內。在手段上,特朗普團隊認識到,要想實現停火,僅對烏施壓是不夠的,還必須威脅甚至真的采取有限升級措施,以獲得談判籌碼。在取得大選勝利后,特朗普及其團隊甚至表現出向烏方而非俄方“接近”的姿態。特朗普9月27日在紐約與澤連斯基會面,11月7日接聽了澤連斯基的祝賀電話,通過兩次直接接觸釋放的共同信號是“將找到俄烏雙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路徑”。

將引發新一輪戰略博弈
當前由媒體披露的促談方案總體而言與俄方要求有較大距離。首先,在烏軍尚控制俄境內庫爾斯克部分地區的情況下,俄方不可能接受就地停火,相反,會將烏軍撤出庫爾斯克作為先決條件。其次,俄方對烏政權的“去納粹化”和“去軍事化”要求,是要保證烏克蘭不會繼續向西方陣營靠攏,更不能在停火重建之后成為西方對俄的“第一道壁壘”,僅得到烏克蘭不加入北約的承諾不足以實現這一目標,遑論“凍結入約”。再者,烏放棄奪回已被俄控制的領土不會被視為足以促成和談的“讓步”,因為這被俄視為理所應當,而在當前,俄軍在頓涅茨克地區攻勢正勁,戰果不斷擴大,俄方恐怕會要求烏方必須再額外做出領土讓步才能啟動和談,因而未必急于投入談判。美國戰略界也在猜測,俄方接下來可能在北線發起進攻,力求將烏軍趕出庫爾斯克,以減少烏方談判籌碼,同時掃清就地停火的最主要障礙。
作為強勢方的俄羅斯固然想積極“做牌”,爭取更大幅度戰略勝利,但作為弱勢方的烏克蘭也并非毫無博弈空間。面對嚴峻形勢,澤連斯基政府和烏克蘭社會開始接受可能要事實上放棄領土的現實。相對于保全領土,獲得可靠的安全保障正在成為烏方更優先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烏方有可能爭取把和談無法立即實現的責任推到俄羅斯身上,推動特朗普政府兌現“通過加大援烏力度向俄施壓”的威脅。對烏而言,更理想的局面是特朗普在促談無果之后遷怒于俄羅斯,進而大幅調整美國的對烏政策,從而形成新的“機會窗口”。
當前在烏政府內部,有不少人贊成特朗普對拜登的批評,那就是“無限制的援助”加“嚴格管控沖突烈度”只會導致沖突長期化,而“有期限的援助”加“減少沖突烈度管控”反倒有可能扭轉戰場態勢。就此而言,烏方先表態愿意放棄領土參與和談,誘導特朗普將促談失敗的“責任”歸咎于俄方,再爭取美國解除對俄使用遠程武器的限制,進一步攪亂危機態勢,有可能成為短期政策選擇。
鑒于烏克蘭危機的復雜性,新一屆特朗普政府要想找出一條切實可行的促談之路并不容易。相比更加墨守成規的拜登政府,特朗普的交易思維固然更有可能破局,但也蘊含著放大危機不確定性的風險。唯一可以確定的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和談方案不會讓沖突立即走向終結,而是將開啟各方戰略博弈的新階段。也要看到,美國戰略界相當一部分人出于這樣那樣的原因,并不愿看到特朗普取得成功,他們必會尋找機會推動特朗普政府對俄施壓,最終目的還是要延續美國的對烏援助,甚至繼續擴大沖突。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已開始在媒體上宣揚,正如從阿富汗倉惶撤軍是拜登政府的污點,放棄烏克蘭將是特朗普政府的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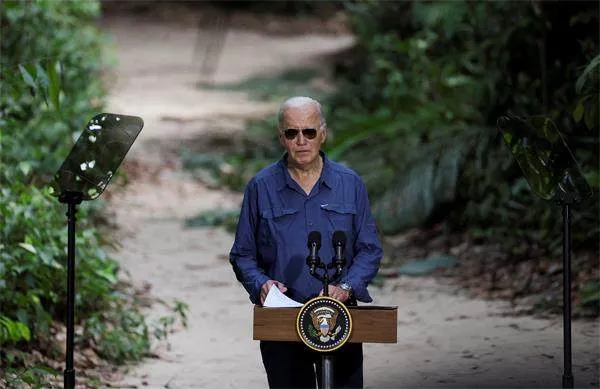
無論如何,烏克蘭危機的尖銳性和復雜性遠非“一天之內就結束戰爭”這樣的口號就可以抵消,俄烏雙方都會竭盡全力在真正承壓之前爭取有利地位,特朗普政治意義上的自信將會遭遇烏東地區和庫爾斯克軍事意義上的殘酷現實,危機的繼續延宕不是他想改變就能改變的。11月16日,澤連斯基接受烏媒體專訪時稱,將爭取在2025年以外交手段結束沖突,同時強調烏不會被強迫進行談判。17日,正在巴西訪問的美國總統拜登突然宣布已授權烏軍使用美國提供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ATACMS)襲擊俄境內縱深目標。另據福克斯新聞報道,特朗普很快就會任命一名“烏克蘭和平特使”。這些消息從某種意義上講顯示出烏克蘭危機在短期內仍將是一個繼續升級的態勢,也從旁印證了特朗普及其團隊很可能沒有充足把握提供能盡快了結烏克蘭危機的有效路徑。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