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清醒”的我,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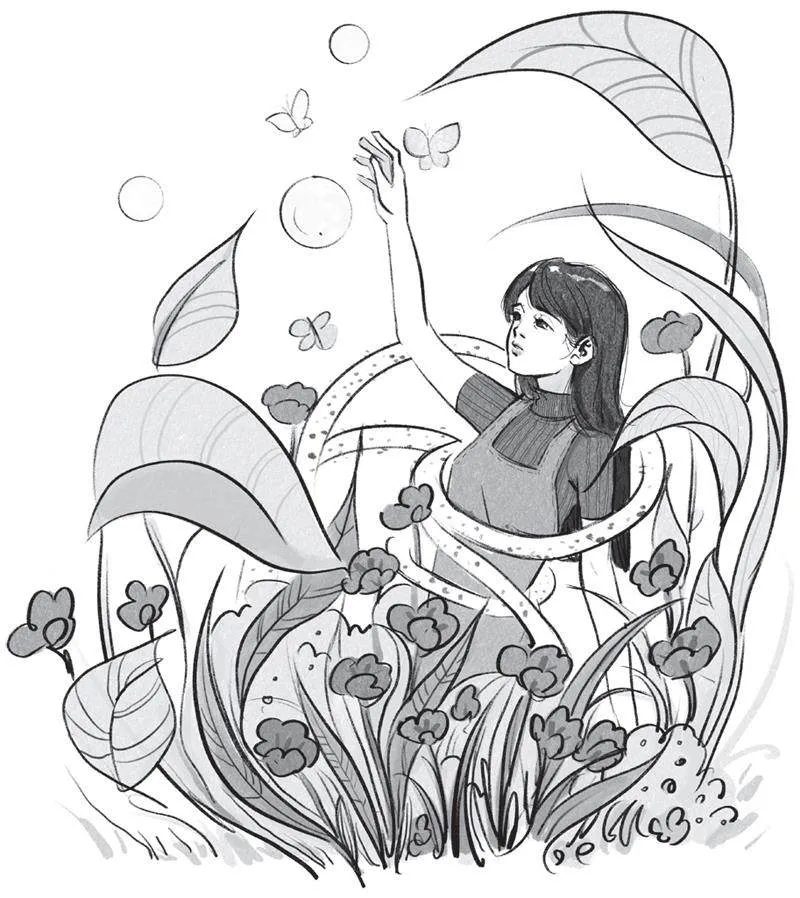
我真是獨立清醒的大女主嗎
大二的暑假,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對手機做到了百分百戒斷。這并非對學習愛得深沉,只因當時的我談了段戀愛,一段將“獨立”和“清醒”貫穿始終的戀愛。
男友說“我等下要打會游戲”時,我忍住了千萬次想告訴他“可不可以陪陪我”的沖動,溫柔地告訴他:“好,我現在正好有篇文獻沒看完。”在他疑惑地問出“你的世界好像不太需要我,你總是回避我”時,我沉默了,事實上,每當我一個人學習遇到困難、一個人搬著幾十斤重的行李時,都特別想和異地的他傾訴,但次次都咽了下去,在我看來,這都是我“獨立”的象征。
我的這段感情,僅僅維持了幾個月就毫無意外地走上了“獨立清醒”的我,錯了“蘭因絮果”的道路。我們從未吵過架,因為每一次溝通的機會都用沉默巧妙避開了。當他再次說出“你的世界好像不需要我”時,我平靜地回應他,“我們確實不太合適”,然后刪光聯系方式,卻在分手之后躲被窩里哭了一個晚上。
“你簡直是當代獨立女性代言人。”“你太清醒了,好棒!”自打分手之后,我的清醒人設算是在好友圈夯實了:見勢不對立即撤退、只篩選不改變等互聯網流行的“優秀品質”在我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此后,這種“優秀品質”又在一段又一段的關系中復演。
之后,又有一個互有好感的異性向我表白,我頓時張皇無措:怎么突然提這個?我還會“大發善心”為其指點迷津:你現在太不理性了,你冷靜一下。
“可是感情當中有這么多理性可言嗎?”對方反問道。我氣勢絲毫不減:“當然得理性,不然人人都當戀愛腦嗎?那山上的野菜都得薅禿了。”
“那能不能溝通一下你的想法,不要這么回避呢?”對方直戳我痛點。
因為聽到“ 回避” 二字,所以我腦子一嗡,頓時惱羞成怒。之后不負責任地扔下一句“ 那你要是這么想, 我也沒辦法”,就逃之夭夭。
我這是怎么了?為什么總是處理不好親密關系?而在每次冷淡逃避后,我卻又悔之不迭。直到我看了一本有關愛情心理學的書,才了解到“回避型依戀”一詞,它毫不留情地撕下了我看似是旌旗、實則是遮羞布的“大女主”人設,我簡直是“回避型依戀”行走的活教材,幾乎條條對應。
“對方表達愛意或關系變得逐漸親密時,回避型依戀會感受到很大的壓力,認為自己的獨立性處于危險之中”——是我。“通常,回避型依戀會采取后撤或回避的行動,不表達自我需求,壓抑自我”——還是我。
的確,我足夠理性,從不在自認為“錯誤”的感情上消耗。我還夠勇敢,敢于及時止損當斷則斷。但我更是百般拒絕溝通,喜歡把人越推越遠。至此,我才明白,如今網絡上情感指導的風向標“不能戀愛腦”“保持獨立”“談戀愛必須得自己開心”對部分人或許奏效,但對“回避型依戀”的人來說,是讓你病而不自知的麻醉劑。
做自己的“養育者”
我從“回避型依戀”的成因開始捫心自問,對自己的童年經歷追根溯源。“‘回避型依戀’者大多在童年時期,其正當需求遭受過父母忽略,為了自我防御,便像刺猬一樣武裝自己,形成了‘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沒有無條件的愛’的信念,所以在親密關系中擁有極強的心理界限。”確實,我從小被要求“你必須考滿分”“你的舞蹈興趣班必須堅持上”,如果沒有達到要求就是一頓“竹筍炒肉”,或者在我想要外出玩耍時屢屢遭到拒絕,或許是從這個時候起,我的內心形成了“回避型依戀”的雛形吧?童年時期的我已經開始認為“我不考滿分父母就不會愛我”“我的需求父母不在意是正常的”,這些觀念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深刻,逐漸形成了“回避型依戀”的典型信念——世界上沒有無條件的愛;除了自己,沒有人靠得住。
找到根源后,我只想心疼地抱抱自己,告訴自己只是因為害怕被拒絕、不被愛才這樣。如果能夠和小時候的自己重逢就好了,我會告訴她:你即使成績一般也沒事,即使偷跑出門,玩滑梯摔個底朝天也沒關系,我仍然在十幾年之后無條件地愛著你。
想到此處,我不禁思考:“回避型依戀”的人總是認為沒有人會無條件愛自己,卻忽略了我們可以無條件地愛自己啊!我們或許可以試試重新“養育”那個曾經遭遇過養育者拒絕和忽視的小孩?把自己在情感關系中想要回避的想法想象成受過創傷的小孩在叫囂,身為母親,我應該如何安撫她呢?
我會在她再一次恐懼步入或經營一段親密關系時,溫聲告訴她:你盡情地去投入吧,受傷了也沒關系,我永遠是你堅實的后盾。我會在她想要表達自我需求時鼓勵她:快,說出你想要對方做的事情,對方肯定樂開了花呢!
就這樣,我在給自己當“養育者”的過程中也療愈著自我,如今的我已經不再以“獨立”“清醒”為掩飾的口號,但奇怪的是,我的“獨立”一點沒有被消解,我仍然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和學業,只是內心深處多了幾分篤定:我有信心坦然迎接每一份愛,我一直被我自己無條件愛著。或許,心靈上的獨立,才是真正的獨立吧!
(摘自《大學生》2024年第9期,子昕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