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質人的“萬卷書”和“萬里路”
原來課本不是重點
大三剛開始,在輔導員的鼓勵下,我打算考研。
經過專業分析后,我選了南京大學的地質學專業,這是全國高校地質學中的王者。之后的備考難度很大,讓我壓力倍增,甚至一度想要放棄。這時,輔導員的話在我耳邊響起來:“如果沒有在C9 讀研,對你來說就是遺憾。”我決定不留遺憾。也正是這份決心,引領著我敲開了南京大學的校門。
來到南大,我不是遇到了各種“書呆子”,而是見識了非常活躍的思想。幾乎每堂課的前幾排都擠滿人。同學們會積極回答老師提問,甚至質疑老師。
半個學期后,我后知后覺地發現每門課都要閱讀極多的文獻,每堂課都輪流有兩個學生上臺分享自己的文獻閱讀成果,我才知道還有一種課件展示方式叫Keynote。研一上學期試卷上的發散類題目比死記硬背的知識考得更多,我第一學期的成績慘不忍睹,很大原因就是吃了“埋頭苦讀”的虧。
“你要記住,對地質學來說,課本是你的起點,但不應該是你的重點,更不是你的終點。”老師對我說。在我以后的求學生涯里,一直都記著這句讓我醍醐灌頂的話。
野外課堂千山萬水
我曾經幻想著地質學家是像《國家地理雜志》上的作者那么逍遙,掛著相機,輕松走遍天下,用拍照和寫字完成閉環。確實,出野外是地質學生不可缺少的一節課,只不過我們的裝備是鐵鍬、麻袋、遮陽帽、溯溪鞋……
和其他專業的學生比起來,地質學生更像是苦行僧。每次在野外,根本不敢去想直升機,有車便已經是奢求,更多時候,雜草小路能好走一點就是最大的盼頭了。但是,近60 歲的老師身體力行,帶著我們披荊斬棘,大家都心生敬仰,沒有了抱怨。
晚上回到賓館, 口袋里、帽子里、衣服縫隙里全都塞滿了土和石頭,衣服洗了好幾遍,水都還是黃的。第二天老師聽聞后安慰我們:“風沙是最好的防曬霜,女生不用怕被曬黑,男生皮膚也被鎖住了水分。”大家聽完會心一笑,苦中作樂是地質人的必備操守。
不過采樣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做實驗,出數據,寫論文,修改,發表,這才是地質學生的一次理想閉環。
然而更多的情況沒那么理想,整個周期會遇到太多彎路和斷崖,就像莫比烏斯環一樣,最常發生的是數據解釋不通,又要打回原形,重新回到讀文獻的階段,多少人都籠罩在“白干了”的延畢恐懼中,或者反復在做實驗、出數據的迷宮里出不去。
我的整個讀研回憶,就像解數學題一樣——找到了合適的采樣地點,仿佛想到了公式;實驗出來理想的數據,像是解出了答案;寫完了文章,就像是檢查確認;等到見刊,和看到了試卷的成績一樣,終于可以長舒一口氣,繼續解下一道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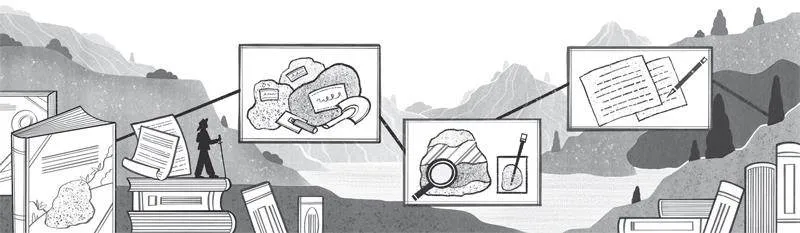
在我的研究生生涯里,踏遍了千山萬水,見識了對末次冰期以來的古氣候重建,學習了溫鹽環流和氣候變率的關系,研究了東亞季風的耦合影響,最終回歸到身邊的青山綠水。回顧整個路程,從南京方山的第一次野外開始啟程,到西藏拉姆拉錯結束,感慨萬千。最后一次出野外,我面對一望無際的青藏高原說:“也許這三年里走過的路可以繞地球好幾圈了,但是我沒有隨意丟棄一個空塑料瓶、一個垃圾袋,也算為全球環境做出了一點貢獻,我是一個合格的地質學生。”
這是修煉,也是福祉
同學開玩笑說:“地質課題組有把女人當男人使、把男人當動物使的傳統。”我也開玩笑說:“一入地質深似海,以后一定會勸退學弟學妹。”
后來,有個本科學弟打算報考地質專業研究生,找我咨詢,希望能打滿“雞血”,但當他聽到南京大學的地質學竟然是如此,瞬間對學習失去了動力。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史鐵生的一句話:“孩子,這是你的罪孽,也是你的福祉。”便不假思索地發送給了他。這句話,既是回答他,也是回答我自己。
這三年里我收獲的,并不是安逸舒適,也不是就業前景,而是品行的修煉,這才是讓我終身受用的。
我想,全國的地質學生大概都是如此,“靜若處子、動若脫兔”形容的是地質學生,“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形容的也是地質學生,在別的專業看來似乎是“人格分裂”,對我們來說卻是情理之中,因為很難找到一個統一的詞來形容讀了萬卷書、還要行萬里路的地質人。
如果再細化到我自己——在野外,我學到的是踏實和堅毅;在實驗室,我學到的是耐心和謹慎;在閱讀文獻中,我學到的是專注和發散。它們像是幾味淬火,磨煉著我的品性,讓我腳踏實地,給我洪荒之力,陪我攻克難關。
(摘自《大學生》2024年第9期,姜敏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