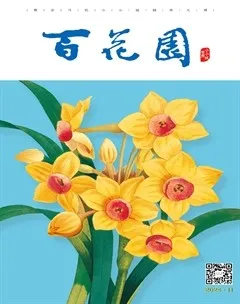麝香蛋蛋

我去大山里看望三舅。三舅是護林員,住在離村五公里遠的酸刺溝口。三舅常年巡山,櫛風沐雨,腰佝僂臉黧黑。我的到來,使三舅和舅母老兩口合不攏嘴。三舅宰了院里跑的雞,舅母摘來屋后地里的菜,忙乎著做了一桌子晚餐。吃著食材新鮮的菜,喝著辣烈的酒,我和三舅打開了話匣子。臉通紅的三舅抿口酒,嘆氣說:“要是那孩子能保住,現在和你一樣大了。”舅母在旁低垂下頭,抹起眼淚。三舅和舅母沒生養孩子,對此我一直納悶。三舅向我聊起了往事。
靠山吃山。山高屲大,山林里有狐貍、狍子、旱獺、馬鹿等野物,山民們布扣套、挖陷阱、撒迷藥、用土銃,爭相獵殺野物。在那物資匱乏的年代里,這些野物的肉可解饞,皮可賣錢。尤其是香子,身上的麝香蛋蛋能賣十幾元,是天價呀!三舅偷賣了三個麝香蛋蛋才得以娶回舅母,三舅說:“這婆娘是三個蛋蛋換來的。”
香子即林麝,形似鹿,有羊羔般大,耳朵大而直立,全身灰褐色,背部有白色的斑點,前肢短后肢長。香子機敏警覺,有一丁點兒風吹草動,就跳躍飛躥而去,眨眼間不見蹤影。捕捉香子不易,山民把能捕捉到香子的人尊稱為“香子匠”。年輕的三舅是有名的“香子匠”。他早上趕羊上山,傍晚回來,肩上常扛著野兔、旱獺、山雞,隔兩三個月能扛回來一只香子。
松樹林里,一棵大樹下發現了比羊糞蛋稍大點兒的一堆糞蛋,這里是香子固定的“廁所”。林子這么大,香子不隨地大小便。離糞蛋十幾米,會找到一根高四五十厘米、油光可鑒的枯樹樁,散發著濃郁嗆人的麝香味,這是香子的蹭樁。香子用麝香蛋蛋蹭樹樁,來標記自己的領地。
麝香蛋蛋是公香子肚臍與睪丸之間的香腺,呈袋狀。蛋蛋的形成跟珍珠的形成有異曲同工之處:香子水足草飽,伸展開四肢躺在大樹下,肚下的腺體外翻,放射香味,吸引來螞蟻、蚊蟲等進入腺體;腺體受刺激而收縮,分泌腺液包裹住蟲子,久之腺體內就形成了扁豆大的褐色顆粒。成年香子的麝香蛋蛋有雞蛋般大,重約二三十克。山里流傳著一個故事:兩個婆娘去林中拾柴,碰到一只死了的香子。先發現的婆娘沖上去,揮起柴刀割下了香子的睪丸,滿臉堆笑地回家向男人報喜。男人臉色醬紫,跺腳罵:“瞎婆娘,天天摸老子的還沒摸夠嗎?”另一個婆娘割了香子肚臍旁的麝香蛋蛋,發了筆意外之財。
三舅和舅母結婚五年,舅母的肚子一直沒鼓起來。有人出主意,以馬鹿胎作藥引補身子準能懷孕。三舅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偷捕到一只馬鹿,舅母吃了鹿胎,喝了中藥,不久竟真懷孕了。
有身孕的舅母后背痛,前胸脹,身體一天天瘦弱下去。三舅進山了。山民們禍害野物,野物越來越少,香子幾乎絕跡了。在酸刺溝半山腰的松林里,發現了新鮮的糞堆,三舅的心怦怦狂跳——天助我呀,有了麝香蛋蛋,就能帶婆娘去城里看病了。三舅在糞堆方圓五十米的樹木間隙里布下了獵夾、扣套。
第三天下午,山溝里傳來香子“呦——”的凄厲嚎叫。三舅撂下挖地的鐵鍬,飛快地奔向半山腰。香子性剛烈,絕望中的香子有時會吃掉自己的麝香蛋蛋,讓山民竹籃打水一場空。
三舅爬到半山腰,被眼前的景象嚇呆了。觸發了機關的獵夾上留下了半截血肉模糊的香子腿,想必是香子為了活命,生生咬斷了自己的腿。三舅心中戰栗,可為了有身孕的舅母,三舅咬緊了牙關。
“香子舍命不舍山”,香子癡戀故土。即使逃脫了,香子不久還是會重回到這兒。三舅深諳香子的特性。
一個月后,三舅發現那糞堆上有了新鮮的糞蛋,他抿嘴笑了。這次,三舅在糞堆方圓一百米的樹木間隙里鋪下了扣套。第六天,三舅去半山腰,看到三條腿的香子被鋼絲扣套住了腦袋,高高地吊在大樹上。
三舅扛回了香子,割下了麝香蛋蛋。舅母捧著麝香蛋蛋,瞇縫眼細瞅。三舅做了蔥爆香子肉,這是他和舅母時隔好幾個月才嘗到肉味,那香味令二人大快朵頤。
當晚,舅母突然肚子劇痛,三舅拉架子車把舅母送到了鎮衛生院。路上,舅母雙腿間鮮血直流,胎兒流產了。醫生說,是麝香動了胎氣。舅母捶打舅舅:“都是你造的孽呀!”三舅扯著自己的頭發,發出了像香子般的慘叫。
三舅砸了獵夾,扔了扣套,再也不進山捕獵了。舅母落下了病根,再沒懷孕。
幾年后,大山里封山育林,三舅應聘做了護林員,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工資雖不高,可三舅喜歡這工作,整天穿梭在山林中,看護林草,看護野物。三舅說,現在“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觀念深入山民心中,山民們保護林草,愛護野物。大山的天更藍了,水更清了,山更綠了,野物更多了。
“呦——”“嗷——”“啾——”窗外黑魆魆的密林中傳來野物的叫聲,三舅瞇眼歪頭豎耳。舅母扯三舅的胳膊:“老頭子,早點兒睡覺,明早還要早起巡山呢。”
[責任編輯 冬 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