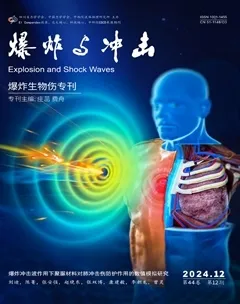基于爆炸損傷的頭部有限元模型建立與驗證


















摘要: 為了更好地理解爆炸沖擊波作用下頭部的力學響應和損傷機制,利用計算機電子斷層掃描與核磁共振醫學圖像獲取了頭部幾何信息,開發了具有骨縫結構的精細化頭部有限元模型。基于已有的激波管尸體實驗,開展了正面、側面與背面爆炸沖擊數值模擬,通過對比顱內壓-時間歷程曲線與顱內壓峰值,驗證有限元模型的有效性。結果表明:在3 種沖擊方向下,顱內4 個區域的壓力峰值與文獻實驗仿真數據吻合較好;爆炸仿真中顱骨骨縫處有明顯應力集中,骨縫線處頭部有更大的損傷風險;同等爆炸沖擊強度下,正面和背面沖擊比側面沖擊對頭部造成的損傷更嚴重。建立的頭部模型可應用于爆炸載荷下的頭部損傷研究,同時可探究骨縫對于頭部生物力學響應的影響,對爆炸損傷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爆炸;有限元模型;模型驗證;生物力學;顱內壓力
中圖分類號: O389 國標學科代碼: 13035 文獻標志碼: A
現代軍事沖突中,爆炸是常見的戰爭危害形式之一。對于爆炸造成的人員傷害,Connelly 等[1] 對6 950名住院的美軍士兵進行了篩查,發現61.9% 因爆炸性損傷入院。同時,美國海軍陸戰隊戰斗創傷登記處的數據顯示,爆炸沖擊導致的顱腦損傷患者占52%[2]。為了研究爆炸引發的顱腦損傷,研究人員進行了大量的動物實驗、尸體實驗以及數值模擬,旨在深入探討損傷機制和組織的耐受閾值[3-7]。康越等[8] 為提高單兵裝備的防爆性能,開展了在實爆場和激波管環境下對頭部爆炸損傷的研究。本文建立了一個適用于爆炸損傷研究的頭部有限元模型,對于深入理解頭部爆炸損傷機制、提升頭部保護性能以及改進損傷治療方案具有重要意義。
近年來,針對腦損傷的研究,Mao 等[9] 開發了一種較為詳細的人體頭部模型,該模型是通過醫學CT(computed tomography)/MRI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圖像并利用Block 方式建立的頭部有限元模型。為國內外研究學者提供了新的頭部建模方法。Cotton 等[10] 建立了一種高度逼真的頭頸部有限元模型,該模型旨在用于沖擊模擬,具備高度的幾何準確性,能夠適應不同的研究需求。Ghajari 等[11] 通過計算模擬,預測了慢性創傷性腦病(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CTE)病理變化的發生位置。該模型結合了生物力學特性,揭示了不同類型腦損傷對腦組織的影響,為理解創傷后腦病理機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并為未來的臨床應用和治療策略的制定奠定了基礎。Carmo 等[12] 為評估頭部重復性沖擊及其對女性大腦的影響,建立了一種具有生物形態特征的女性頭部有限元模型,所建模型有助于深入研究創傷性腦損傷的機制。聶偉曉等[13] 針對破片侵徹對戴防彈頭盔的頭部靶標造成的鈍擊效應進行了數值模擬。這項研究為改進防護裝備設計、提升其防護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數據支持。栗志杰等[14] 基于三維頭部數值模型,深入探討了顱腦碰撞損傷的機理。該研究為理解顱腦碰撞損傷的發生機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持,并為相關防護措施的改進奠定了基礎。張文超等[15] 通過爆炸沖擊波對顱腦造成沖擊傷的數值模擬,揭示了沖擊波的傳播特性及其對顱腦內部壓力和應力分布的影響。
雖然目前大多數有限元模型能夠對頭部的顱內壓力、腦損傷和顱骨骨折等進行損傷分析,但大多數模型都是通過碰撞實驗來驗證其有效性,鮮有通過爆炸實驗進行驗證。經過爆炸驗證的頭部模型更適合用于研究爆炸場景下的頭部損傷。本文中,基于已有的模型建立方法[16],通過對一名35 歲、50 百分位的中國中等身材男性志愿者進行計算機斷層掃描和核磁共振成像,模擬人體頭部特征。基于這些數據,建立一種具有顱骨骨縫線的頭部有限元模型,并利用激波管實驗[17] 驗證該模型的有效性。
1 材料與方法
1.1 模型建立
掃描一位35 歲、50 百分位中國中等身材特征男性志愿者的頭部,獲取CT/MRI 斷層圖片,掃描層厚度為0.625 mm,共601 張斷層圖像,通過這些DICOM 圖像,精確提取頭部的幾何信息。本文采用醫學建模軟件3D-Slicer 對顱腦與顱骨進行了分割,成功構建了三維模型,為后續的生物力學分析和研究提供了基礎數據。
本研究旨在構建具有詳細顱骨結構的頭部模型,需分割出顳骨、顴骨、面骨、枕骨和蝶骨等顱骨解剖結構。為探討骨縫線對顱內力學響應的影響,需保留顱骨間的骨縫幾何信息。根據CT 斷層圖像,保留相關的幾何特征,以便后續進行網格化處理。圖1(a) 展示了志愿者顱骨的分割模型。由于顱腦MRI 圖像閾值接近,將顱腦分割為大腦、小腦和腦干,并保留大腦表面溝壑。對分割后的模型進行平滑處理,以去除不利于構建模型的噪點,平滑后的顱腦分割結果如圖1(b) 所示。由于3D-Slicer 生成的STL 文件是由大量三角面擬合而成的曲面模型,無法直接用于網格劃分,采用Geomagic Design X 64 軟件進行逆向建模,將STL 轉換為STP 實體文件。頭部各結構的逆向建模分別進行,處理過程中,接觸表面存在的交叉干涉情況,因此模型需要在HyperMesh 軟件中進行簡單的幾何處理。獲取到的模型幾何圖形如圖1(c) 所示。顱骨骨片之間通過布爾運算進行連接,形成完全嚙合的鋸齒形結構。為了避免HyperMesh 自動劃分網格可能出現的網格干涉問題,首先在頭部幾何表面生成三角形2D 網格,然后填充這些2D 網格包絡的封閉空間,以生成內部網格。在已劃分好的顱骨與顱腦網格基礎上,通過顱骨內表面與顱腦外表面包絡的封閉空間,進一步劃分腦脊液網格。同時,在腦脊液的表面生成殼單元,其中外表面代表硬腦膜,內表面則對應軟腦膜。
通過上述的方法,成功獲得了包括顳骨、顴骨、額骨、枕骨、蝶骨、頂骨、面骨及下頜骨的顱骨以及包括大腦、小腦、腦干、腦脊液、硬腦膜與軟腦膜的顱腦結構。在建立好的四面體網格模型中,經過模型整合和網格質量檢查,確保99% 以上的網格雅可比值不低于0.3,長寬比不超過5,網格尺寸約為4 mm。各解剖結構采用共節點連接方式,骨片之間則通過鋸齒形的共節點連接。最終建立的模型包含95 563個節點、525 076 個單元,頭部總質量為4.9 kg。最終的頭部有限元模型如圖1(d) 所示。
1.2 材料屬性
已有研究[18] 表明,骨組織具有彈塑性材料特性,在屈服點之前,彈塑性材料表現出彈性行為,而在屈服點之后,骨組織則可能發生斷裂。因此,在模型中采用彈塑性材料來模擬骨組織的特性。在LSDyna軟件中,顱骨組織采用MATL_003 材料模型進行建模,而面骨組織則選用MATL_001 材料模型。顱骨組織材料參數如表1[15-16] 所示,表中ρ 為密度,E 為彈性模量,ν 為泊松比, σy 為屈服極限, 為切線模量,n 為硬化參數,C 和P 均為Cowper-Symonds 模型參數,εp 為塑性失效應變。
由文獻[18] 可知腦組織材料具有黏彈性,在LS-DYNA 軟件中,腦組織選用MATL_006 材料來模擬其黏彈性特性。黏彈性材料變形與其剪切模量密切相關,剪切模量的計算公式為:
G(t) = G0 +(G0 -G1) e-βt (1)
式中:G0 為短時剪切模量, G∞為長時剪切模量, β為衰減常數,t 為時間。
對頭皮和腦膜采用常用彈性材料進行表征。腦組織結構材料參數如表2[15, 18-19] 所示,K 為體積模量。
本文數值模擬中設定的炸藥為100 g TNT 炸藥,模擬該炸藥在空氣域中爆炸,以再現實際的爆炸場景。在LS-Dyna 軟件中,對空氣選用MATL_009 材料模型,其狀態方程采用線性多項式方程:
式中:pa 為壓力,ea0 為體積內能,Va 為相對體積, C0、C1、C2、C3、C4、C5 和C6 為多項式系數。空氣材料及狀態方程參數[20] 分別為ρa=1.225 kg/m3, C0=C1=C2=C3=0,C4=C5=0.4,C6=0,ea0=2.58×105 J/m3。
在數值模擬中,對TNT 炸藥采用MATL_008 材料,并利用JWL (Jones-Wilkins-Lee) 狀態方程[20] 來描述其爆炸過程。JWL 狀態方程通常用于高能材料的爆炸模擬,其形式為:
式中:pe 為爆轟壓力,Ve 為初始相對體積,ee0 為體積爆轟能量,A、B、ω"、R1和R2 、 均為多項式方程系數。TNT 炸藥的具體參數[20] 分別為ρe=1.63 g/cm3,爆速D=6 930 m/s,A=371 GPa,B=3.23 GPa,R1=4.15,R2=0.9,ω=0.35,ee0=6 GJ/m3。
1.3 模型驗證
為了模擬實際爆炸沖擊頭部場景,參考王智等[20] 的空氣域模型,構建了一個320 mm×320 mm×1 500 mm的空氣域爆炸模型,如圖2(a) 所示。該模型中,對空氣和炸藥網格單元采用ALE (arbitrary Lagrange-Euler) 算法進行計算,網格尺寸設置為5 mm。在起爆點的yz 平面設置了對稱邊界,以提高計算效率;空氣域的邊界則設定為無反射邊界,并將邊界壓力保持在大氣壓,以防止出現負壓現象。
根據模型相似律理論,建立了炸藥在空氣中爆炸的經驗公式,并通過試驗確定了相關系數[21],從而得到了高爆炸藥沖擊波峰值超壓的表達式:
式中:Δp+為峰值超壓,單位為 MPa; rˉ 為比例距離;m 為炸藥當量,單位為kg;d 為爆炸中心與頭部的距離(簡稱爆心距),單位為m。
根據式(4),利用所建立的模型模擬100 g TNT 炸藥在空氣域內的爆炸,獲取不同爆心距處的氣壓變化曲線及峰值超壓。對比經驗公式[21] 預測的超壓峰值與模擬結果,檢驗所建立的爆炸模型是否具有可行性,以及是否適用模擬爆炸場景。
在基于頭部模型進行的爆炸損傷研究中,首先需要驗證頭部模型的有效性。本文中,參考Sharma[17]的激波管實驗與仿真,將頭部模型置于空氣域內,模擬100 g TNT 炸藥爆炸對人體頭部的沖擊,以確保頭部所受載荷與文獻中的一致,本文仿真模型如圖2(b) 所示。相較于Sharma[17] 的模型,本文的空氣域模型更貼近實際爆炸環境。Sharma[17] 利用變直徑激波管,通過驅動室(內有惰性高壓氣體)產生的沖擊波,模擬爆炸所產生的高壓沖擊波,作用于激波管尾端固定的頭部模型。激波管尸體實驗示意如圖2(c) 所示,在激波管的A 和B 處裝有壓力傳感器,并在靠近尸體頭部的位置附加了壓力傳感器C,以便于測量激波發生過程中激波管內部氣體壓力的變化。
Sharma[17] 開展了71、76 和104 kPa 等3 種沖擊強度的激波管模擬爆炸實驗。本文中采用空氣域模型,模擬激波管產生的沖擊波,通過控制炸藥與頭部模型的距離,以確保作用于頭部的沖擊波壓力與實驗一致。這種方法能夠有效地再現Sharma[17] 實驗中所測得的壓力特征,從而為后續的模型驗證提供可靠的基礎。由于71 和76 kPa 強度近似,本文模型驗證是在低強度(75 kPa)和高強度(102 kPa)2 種強度下進行,比較顱內壓的變化及顱內壓峰值。顱內壓力測量點設置在頭部的額部、腦室、頂部和枕部,測量點的位置在圖2(b) 中進行了標注。這種設置能夠全面評估不同強度下顱內壓力的響應特征,為模型的有效性驗證提供了重要依據。
2 結 果
爆炸沖擊波在顱內傳播規律極其復雜,受到多種因素影響。沖擊波可以通過顱骨的骨縫傳播,直接作用于顱腦。此外,頭顱加速運動也會導致顱內出現應力和應變,從而進一步影響顱內壓力的分布。沖擊波直接作用于頭部時,可能引起顱骨變形,使得沖擊波以更快的速度通過顱骨并作用于腦組織[22]。Sharma[17] 進行了5 組實驗,但由于實驗的偶然性和多種因素的影響,最終僅有尸體4 和5 的實驗數據可用于模型驗證。文獻中僅對正面沖擊下顱內壓的時間歷程曲線進行了比較,未詳細分析側面和背面沖擊。本文中將通過建立的有限元模型進行仿真預測,分析顱內壓-時間歷程曲線及顱內壓峰值,以驗證所構建的頭部有限元模型在頭部的爆炸損傷研究中的適用性。研究發現,在爆炸載荷作用下,骨縫處會出現明顯的應力集中,導致顱骨更易發生骨折,同時顱腦也可能遭受更嚴重的損傷。
2.1 空氣域爆炸模型驗證
通過建立的爆炸模型進行模擬仿真,分別測量在爆心距為0.75、0.80、0.85、0.90 和0.95 m 時的壓力變化。所得到的壓力變化曲線如圖3 所示。根據數值模擬分析所獲得的超壓峰值,與高爆炸藥沖擊波峰值超壓公式[21] 進行對比,驗證結果如表3 所示。根據結果可知,超壓峰值數值模擬結果與經驗公式計算結果基本一致,相對誤差控制在10% 以內,最小誤差為0.18%。這表明所建立的空氣域爆炸模型適用于爆炸相關的科學研究。
2.2 正面爆炸
關于生物方面的驗證,由于頭部組織結構復雜,仿真和實驗之間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中引入了Sharma[17] 的仿真數據以達到驗證的目的。在爆炸正面加載條件下,顱內壓的數值模擬結果與實驗結果[17]的對比如圖4~7 所示,可以看出,低強度沖擊波正面加載頭部時,本文腦室和頂部顱內壓力模擬結果與Sharma[17] 的實驗結果和仿真數據吻合良好。盡管實驗存在一定的不可預測誤差和偶然性,同時由于頭部模型的差異及測量點的偏差,枕部的預測結果與實驗結果存在一定差距,但與Sharma[17] 的仿真數據擬合度較好。額部的預測結果與Sharma[17] 的實驗結果和仿真數據均存在差距,但依據康越等[23] 的近期研究,前額附近的顱內壓會出現一個極高的峰值,而不是先有一個較小峰值后再攀升至較大峰值。在高強度沖擊載荷下,額部的顱內壓預測與在低強度沖擊分析類似,與康越等[23] 的近期研究相符合。腦室和枕部的顱內壓預測結果與Sharma[17] 的實驗結果吻合度較高。盡管枕部區域的顱內壓預測結果與Sharma[17]的實驗結果存在較大差距,但與Sharma[17] 的仿真數據吻合較好。而其他位置的測量點均位于額部之后,沖擊波在頭部發生了復雜的反射,減小了外部因素的影響。綜合分析顱內壓變化曲線,可以看出,模型仿真所得的顱內壓力變化曲線與Sharma[17] 實驗和仿真擬合度較好。
表4 展示了不同強度沖擊波正面沖擊下,本文模型預測的顱內壓峰值與Sharma[17] 的實驗數據(cad4、cad5、cad4 與cad5 平均值)和仿真數據的對比情況。由于實驗的不確定性,Sharma[17]的一組尸體實驗數據缺乏參考價值,這也導致后文關于側面和背面爆炸關于cad 與cad5 部分數據缺少。由表4 可以看出,在低強度和高強度沖擊波沖擊下,數值模擬預測的顱內壓峰值均為額部顱內壓峰值>頂部顱內壓峰值>腦室顱內壓峰值,其中枕部的顱內壓峰值為負壓。在低強度沖擊下,實驗cad4 與cad5[17] 的額部顱內壓峰值平均值為132 kPa,本文模型預測的額部顱內壓峰值為155 kPa,略高于實驗平均值,但介于實驗cad4 的額部顱內壓峰值與實驗cad5 的額部顱內壓峰值之間。本文模型預測的腦室顱內壓峰值為52 kPa,高于相應的實驗cad4 的結果和實驗cad5 的結果及其兩者的平均值,但低于Sharma[17]的仿真預測值。本文模型預測的頂部顱內壓峰值為62 kPa,高于Sharma[17] 的實驗結果和仿真預測值,但誤差在20% 以內。在高強度沖擊波沖擊下,額部顱內壓峰值的預測結果與Sharma[17] 的數據存在較大偏差,但腦室、頂部和枕部位置的顱內壓峰值預測結果與Sharma[17] 的數據接近。其中,本文模型預測的腦室顱內壓峰值為84 kPa,高于Sharma[17] 的實驗平均值55 kPa,但低于Sharma[17] 的仿真數據91 kPa。綜上所述,在低強度和高強度沖擊波作用下,利用本文中建立的模型預測得到的顱內壓峰值與Sharma[17] 的實驗結果和仿真數據相吻合。
2.3 側面爆炸
表5 展示了側面沖擊下,本文模型預測的顱內壓峰值與Sharma[17] 的實驗數據(cad4、cad5、cad4 與cad5 的平均值)和仿真結果的對比情況。在低強度沖擊波沖擊下,額部顱內壓的模型預測值與實驗結果[17] 存在較大誤差,但與仿真結果[17] 相近。模型預測值為76 kPa, Sharma[ 1 7 ] 的仿真數據為69 kPa,兩者的誤差為9.21%。腦室顱內壓的模型預測值為40 kPa,Sharma[17] 的實驗平均值為30 kPa, cad5 的實驗值為39 kPa,仿真結果為42 kPa,最小誤差為1.25%。雖然模型預測的頂部與枕部顱內壓峰值與Sharma[17] 的實驗數據存在較大差距,但和Sharma[ 1 7 ] 仿真的預測值接近。在高強度沖擊下,模型預測的額部顱內壓峰值高于Sharma[17] 的實驗和仿真數據,腦室的預測值與Sharma[17] 的仿真結果接近,枕部預測值介于Sharma[17] 的實驗結果與仿真結果之間。
2.4 背面爆炸
表6 展示了背面爆炸沖擊下,本文模型預測的顱內壓峰值與Sharma[17] 的實驗數據( cad4、cad5、cad4 與cad5 平均值)和仿真的對比情況。在低強度沖擊下,額部預測的顱內壓峰值介于cad4 與cad5 之間。腦室的預測結果雖然高于Sharma[17] 的實驗結果,但與Sharma[17] 的仿真結果接近,誤差為4.76%。模型預測的頂部結果與cad5 相近,誤差為9.28%。枕部的模型預測值與Sharma[17] 的仿真相近。在高強度沖擊載荷下,腦室和頂部的預測結果介于Sharma[17] 的實驗與仿真之間,而額部預測結果在cad4 與cad5之間。枕部預測結果為149 kPa,介于Sharma[17]的實驗與仿真之間, Sharma[ 1 7 ] 的仿真數據為138kPa,誤差為7.38%。通過顱內壓峰值的對比,模型預測的結果與Sharma[17] 的實驗和仿真吻合較好。
2.5 力學響應與損傷分析
在模型驗證過程中,發現高強度和低強度爆炸沖擊波作用于頭部時,顱骨骨縫處出現明顯的應力集中。圖8 展示了低沖擊強度下頭部顱骨的應力云圖,可以明顯看出,3 個沖擊方向均會在骨縫處產生應力集中。沖擊波在經過骨縫時,由于骨縫相對于顱骨存在凹陷且截面厚度較小,應力通過骨縫作用于顱腦,從而導致更嚴重的腦損傷。這表明,在爆炸載荷作用下,由于顱骨骨縫的存在,爆炸沖擊波更容易造成嚴重的腦損傷。
圖9 展示了正面、側面和背面爆炸沖擊對顱內4 個位置的壓力峰值的對比。其中,正面爆炸對枕部區域和背面爆炸對額部區域的顱內壓峰值表現為負壓。根據黃星源[21] 的研究,正面或背面沖擊下,沖擊波在經過整個頭部后,會在沖擊側的背面匯聚,導致沖擊波從背面擠壓頭部,從而使顱內出現負壓。依據文獻[24] 中的損傷評估標準,發現在低強度沖擊(圖9(a))與高強度沖擊(圖9(b))下,腦室區域的顱內壓強度最低,造成輕度腦損傷。在低強度沖擊下,爆炸對頭部造成輕度損傷;而在高強度沖擊下,正面沖擊對額骨區域的顱內壓峰值達292 kPa,造成中重度損傷。在顱內4 個位置中,正面沖擊下的顱內壓均大于側面沖擊,僅在低強度沖擊時,頂部與枕部的壓力小于側面沖擊。而在高強度沖擊下,背面沖擊造成的腦室損傷小于側面沖擊。綜合比較壓力峰值,正面沖擊和背面沖擊對頭部的綜合損傷情況明顯高于側面沖擊。
3 結 論
本研究建立了具有骨縫的精細解剖結構的頭部有限元模型,基于Sharma[17] 的激波管尸體實驗,開展了不同爆炸方向和沖擊強度的數值模擬,對比了正面沖擊下顱內壓變化以及不同沖擊方向的顱內壓峰值,得到了以下結論:
(1) 模型數值模擬結果與Sharma[17] 的實驗和仿真數據吻合較好,表明建立的模型能夠有效模擬頭部在爆炸載荷下的生物力學響應,如顱內壓變化等。
(2) 骨縫區域出現明顯的應力集中,顯示在爆炸載荷作用下,該區域相較于其他部位具有更大的損傷風險。由于應力集中,沖擊波的傳遞路徑會發生改變,進而通過骨縫進入顱內,使得爆炸損傷機制更加復雜,對此問題仍需進一步研究。
(3) 在相同的爆炸沖擊強度下,正面和背面沖擊對頭部的損傷程度顯著高于側面沖擊。
本文中所建立的具有骨縫的頭部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可為未來的頭部爆炸損傷研究提供支撐,可用于分析具有骨縫的人體頭部在不同載荷下的響應。
參考文獻:
[1]CONNELLY C, MARTIN K, ELTERMAN J, et al. Early traumatic brain injury screen in 6594 inpatient combat casualties [J].Injury, 2017, 48(1): 64–69. DOI: 10.1016/j.injury.2016.08.025.
[2]GALARNEAU M R, WOODRUFF S I, DYE J L, et al. Traumatic brain injury during Operation Iraqi Freedom: findings fromthe United States Navy-Marine Corps Combat Trauma Registry [J]. Journal of Neurosurgery, 2008, 108(5): 950–957. DOI:10.3171/JNS/2008/108/5/0950.
[3]BHATTACHARJEE Y. Shell shock revisited: solving the puzzle of blast trauma [J]. Science, 2008, 319(5862): 406–408.DOI: 10.1126/science.319.5862.406.
[4]YU X C, AZOR A, SHARP D J, et al. Mechanisms of tensile failure of cerebrospinal fluid in blast traumatic brain injury [J].Extreme Mechanics Letters, 2020, 38: 100739. DOI: 10.1016/j.eml.2020.100739.
[5]KULKARNI S G, GAO X L, HORNER S E, et al. Ballistic helmets: their design, materials, and performance against traumaticbrain injury [J]. Composite Structures, 2013, 101: 313–331. DOI: 10.1016/j.compstruct.2013.02.014.
[6]MOSS W C, KING M J, BLACKMAN E G. Skull flexure from blast waves: a mechanism for brain injury with implicationsfor helmet design [J].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09, 103(10): 108702. DOI: 10.1103/PhysRevLett.103.108702.
[7]GOELLER J, WARDLAW A, TREICHLER D, et al. Investigation of cavitation as a possible damage mechanism in blastinducedtraumatic brain injury [J]. Journal of Neurotrauma, 2012, 29(10): 1970–1981. DOI: 10.1089/neu.2011.2224.
[8]康越, 張仕忠, 張遠平, 等. 基于激波管評價的單兵頭面部裝備沖擊波防護性能研究 [J]. 爆炸與沖擊, 2021, 41(8): 085901.DOI: 10.11883/bzycj-2020-0395.
KANG Y, ZHANG S Z, ZHANG Y P, et al. Research on anti-shockwave performance of the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thehead of a soldier based on shock tube evaluation [J]. Explosion and Shock Waves, 2021, 41(8): 085901. DOI: 10.11883/bzycj-2020-0395.
[9]MAO H J, ZHANG L Y, JIANG B H, et al. Development of a finite element human head model partially validated with thirtyfive experimental cases [J]. Journal of Biomechanical Engineering, 2013, 135(11): 111002. DOI: 10.1115/1.4025101.
[10]COTTON R T, PEARCE C W, YOUNG P G, et al. Development of a geometrically accurate and adaptable finite elementhead model for impact simulation: the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Simpleware Head Model [J]. Computer Methods inBiomechanic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16, 19(1): 101–113. DOI: 10.1080/10255842.2014.994118.
[11]GHAJARI M, HELLYER P J, SHARP D J. Computational modelling of traumatic brain injury predicts the location of chronictraumatic encephalopathy pathology [J]. Brain, 2017, 140(2): 333–343. DOI: 10.1093/brain/aww317.
[12]CARMO G P, DYMEK M, PTAK M, et al. Development, validation and a case study: the female finite element head model(FeFEHM) [J].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 2023, 231: 107430. DOI: 10.1016/j.cmpb.2023.107430.
[13]聶偉曉, 溫垚珂, 董方棟, 等. 破片侵徹戴防彈頭盔頭部靶標鈍擊效應數值模擬 [J]. 兵工學報, 2022, 43(9): 2075–2085.DOI: 10.12382/bgxb.2022.0428.
NIE W X, WEN Y K, DONG F D,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ludgeoning effect of fragments penetrating head targetwearing bulletproof helmet [J]. Acta Armamentarii, 2022, 43(9): 2075–2085. DOI: 10.12382/bgxb.2022.0428.
[14]栗志杰, 由小川, 柳占立, 等. 基于三維頭部數值模型的顱腦碰撞損傷機理研究 [J]. 工程力學, 2019, 36(5): 246-56. DOI:10.6052/j.issn.1000-4750.2018.04.0254.
LI Z J, YOU X C, LIU Z L, et al.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brain injury during head impact based on the three-dimensionalnumerical head model [J]. Engineering Mechanics, 2019, 36(5): 246-256. DOI: 10.6052/j.issn.1000-4750.2018.04.0254.
[15]張文超, 王舒, 梁增友, 等. 爆炸沖擊波致顱腦沖擊傷數值模擬研究 [J]. 北京理工大學學報, 2022, 42(9): 881-90. DOI:10.15918/j.tbit1001-0645.2021.191.
ZHANG W C, WANG S, LIANG Z Y,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traumatic brain injury induced by blast waves [J].Transactions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22, 42(9): 881-890. DOI: 10.15918/j.tbit1001-0645.2021.191.
[16]毛征宇, 李澤民, 牛文鑫, 等. 不同載荷作用下頭部生物力學響應仿真分析 [J]. 醫用生物力學, 2016, 31(6): 532–539,547.DOI: 10.3871/j.1004-7220.2016.06.532.
MAO Z Y, LI Z M, NIU W X, et al.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on biomechanical responses of human head under differentloading conditions [J]. Journal of Medical Biomechanics, 2016, 31(6): 532–539,547. DOI: 10.3871/j.1004-7220.2016.06.532.
[17]SHARMA S. Biomechanical analysis of blast 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a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and validation study ofblast effects on human brain [M].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2011.
[18]李澤民. 子彈沖擊防彈頭盔動力學響應及防護性能仿真研究 [D]. 湘潭: 湖南科技大學, 2016.
LI Z M. The bullet impact ballistic helmets simulation research on dynamic response and protective performance [D].Xiangta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19]PAVAN P G, NASIM M, BRASCO V, et al. Development of detailed finite element models for in silico analyses of brainimpact dynamics [J].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 2022, 227: 107225. DOI: 10.1016/j.cmpb.2022.107225.
[20]王智, 常利軍, 黃星源, 等. 爆炸沖擊波與破片聯合作用下防彈衣復合結構防護效果的數值模擬 [J]. 爆炸與沖擊, 2023,43(6): 063202. DOI: 10.11883/bzycj-2022-0515.
WANG Z, CHANG L J, HUANG X Y, et al. Simulation on the defending effect of composite structure of body armor underthe combined action of blast wave and fragments [J]. Explosion and Shock Waves, 2023, 43(6): 063202. DOI: 10.11883/bzycj-2022-0515.
[21]黃星源. 爆炸沖擊波作用下顱腦損傷力學機制與頭盔防護性能研究 [D]. 湘潭: 湖南科技大學, 2023. DOI: 10.27738/d.cnki.ghnkd.2023.000012.
HUANG X Y. Research on mechanical mechanism of craniocerebral injury and protective performance of helmet under theblast wave [D]. Xiangta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3. DOI: 10.27738/d.cnki.ghnkd.2023.000012.
[22]趙輝, 朱峰. 原發性顱腦沖擊傷的生物力學機制 [J]. 創傷外科雜志, 2016, 18(6): 375–378. DOI: 10.3969/j.issn.1009-4237.2016.06.017.
ZHAO H, ZHU F. The biomechanical mechanism of primary blast brain injury [J]. Journal of Traumatic Surgery, 2016, 18(6):375–378. DOI: 10.3969/j.issn.1009-4237.2016.06.017.
[23]康越, 馬天, 黃獻聰, 等. 顱腦爆炸傷數值模擬研究進展: 建模、力學機制及防護 [J]. 爆炸與沖擊, 2023, 43(6): 061101.DOI: 10.11883/bzycj-2022-0521.
KANG Y, MA T, HUANG X C, et al. Advances in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blast-induced traumatic brain injury: modeling,mechanical mechanism and protection [J]. Explosion and Shock Waves, 2023, 43(6): 061101. DOI: 10.11883/bzycj-2022-0521.
[24]SAUNDERS R N, TAN X G, QIDWAI S M, et al. Towards identification of correspondence rules to relate traumatic braininjury in different species [J]. Annals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2019, 47(9): 2005–2018. DOI: 10.1007/s10439-018-02.
(責任編輯 張凌云)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12372356,11972158);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CX2022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