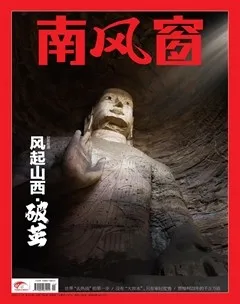文獻
1中國經濟高質量增長與新質生產力
趙波 北大國發院經濟學長聘副教授
本文為趙波在北大國發院MBA講壇第75講
先談談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性。從1978年開始,我們的經濟增速雖然有所波動,但平均增速非常高,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前40年里,年均增速在9% 左右。然而近些年來,尤其是從2012 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速不斷下降。這既由于全球次貸危機的沖擊波,也有新冠疫情和全球新一輪衰退的影響。經濟潛在增速從2012年左右的近10% 降至現在的約5%。

面對這樣的數據,很多人感到悲觀,擔心中國經濟是否出了問題,是否還能按照過去的高增長進一步改革下去。因此,我們急切需要搞清楚如何才能提升經濟增速,或者避免它進一步的下降。我們需要總結過去的成功經驗。以前為什么做得很好?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但絕大多數人會認同的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頭40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市場化的改革、投資驅動的發展戰略、擴大開放與國際貿易、經濟上財政分權等。為什么那些成功經驗在當前遭遇了挑戰,無法維持過去的高增長呢?部分原因是經濟內在規律的作用。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再增加資本投入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會逐漸降低。例如,美國、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都經歷過快速增長階段,但在后期都出現了增速逐漸下降的現象。
此外,我們面臨一些特殊的國內國際環境,包括產能過剩、內需不足、外部不確定性增加等。例如,房地產業過去是我國經濟的支柱,但由于2019年之后國家推行“三條紅線”政策,旨在遏制房地產企業過高的債務增長,這導致房地產企業融資困難,投資大幅下降,進而影響了土地市場的拍賣,加劇了地方政府本就嚴峻的債務危機。同時,由于過去的房地產投資在我國整體投資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也導致經濟中的投資需求下降得非常快,經濟開始出現大幅度的增速放緩。
我認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應對上述挑戰的重要手段,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生產率可以簡單理解為一種生產效率,它衡量了企業在相同要素投入下的產出能力。體現在宏觀層面,就是一個國家整體的生產效率。為了衡量一個國家的生產效率,經濟學家們采用了一系列的生產計量方法在宏觀層面進行估算。生產效率的變化不僅反映了技術進步,還體現了創新能力和要素資源配置的效率。
2為什么硅谷精英希望特朗普成為“美國的CEO”?
本文節選自《文化縱橫》,編譯原文為Capital&Main
《為什么硅谷精英希望特朗普成為“美國CEO”》
科技精英的倒戈也與拜登在退選前提出的征稅計劃有關,他希望對未實現收益的資本部分征稅,而這是壓垮風投a16z創始人馬克·安德森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主黨)太瘋狂了,他們顯然想借此謀求巨額利益,”Palantir 聯合創始人喬·朗斯代爾表示,“99% 的投資者都明白這將造成多大的破壞——它將摧毀我們的創新世界。”
特朗普承諾將放松監管,是吸引科技精英的另一個關鍵要素,這將帶來寬松的反壟斷執法環境,為“不受約束的企業增長”鋪平道路。盡管這保障了巨頭的利益,但長遠看將會抑制公平競爭和創新。ITIF(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創始人阿特金森表示:“特朗普更像是一位‘CEO’總統,他傾向于利用自己的經驗和人脈來做決定,而不是通過繁瑣的政府流程,譬如19次會議或四級備忘錄來進行跨部門活動。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硅谷精英)會覺得,‘如果我們能與特朗普開一些閉門會議,我們的議程便可以落地’,這與哈里斯政府不同。”

特朗普對加密貨幣領域的示好也點燃了一些科技精英的熱情,他承諾任命一位“建設未來、而不是阻礙未來”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暗示加密貨幣的監管將得到放松。盡管這會使加密貨幣投資者和企業家獲得收益,卻會讓散戶在已經十分動蕩的市場上承受更大的風險。
硅谷里反對特朗普的力量也已集結起來,即一批覺得自己被“污名化”的科技精英們。“外界傳言硅谷和科技行業正轉向‘讓美國再次偉大’,這甚至不只是右翼,而是右翼的分支,這讓人感到沮喪。”他們擔心,減稅和放松管制帶來的短期利益,可能會以犧牲長期經濟健康和社會穩定為代價。正如庫班所形容的,“科技精英已經到了想要自己控制世界的地步”。
3數字時代的就業風險分配:制度主義的視角
張順 呂風光 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
本文節選自《社會學研究》2024年第5期
當代中國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遷,風險社會特征進一步凸顯,甚至已經進入“高風險社會”。21世紀以來的數字經濟發展,使我們尤其深刻地感受到數字經濟帶來的巨大沖擊和不安全感。
勞動力市場風險不斷深化。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1999 年至2019 年,自雇勞動者群體占比由8.74% 上升至22.84% ;同時,2021 年個人經營、非全日制以及新就業形態等靈活就業規模達到2 億人,勞動力市場的不穩定性與風險性不斷凸顯。從理論維度看,風險社會學理論深刻分析了當代社會的不確定性演化趨勢。布迪厄認為“不確定、不穩定是21 世紀社會問題的根基”;貝克提出風險社會的概念,認為現代社會正從工業社會轉向風險社會。本文從風險社會學的基本視角出發,從失業風險和收入風險兩個維度,衡量勞動者就業風險并進行實證研究。
本文主要結論如下:第一,數字經濟通過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進而降低失業風險,但勞動者收入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性則快速上升。這一發現可以解釋為何近年經濟發展增速放緩,而整體失業率并未發生明顯上升,還有大量勞動者進入互聯網新業態、非正規就業數量增加,勞動者職業流動速度加快、收入波動加大等現象。第二,人力資本、政治資本和社會資本對就業風險的不同維度具有相異的作用效果。人力資本能夠顯著降低勞動者失業風險,但顯著提高勞動者收入風險,呈現高收入高風險特征;社會資本與政治資本均能顯著降低失業風險與收入風險。第三,隨著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三類個體資本對就業風險的制度性作用大體上呈下降趨勢,或者說化險性功能有所削弱。這一結論能夠很好地解釋“讀研、讀博熱”及大學生入黨積極性上升等現象。為應對數字時代不斷加劇的就業風險,勞動者需要更為豐富的個體資本以有效規避就業風險。
綜合上述發現,數字經濟發展不但通過技術系統路徑直接影響就業風險,也通過影響制度作用空間進而影響就業風險的分化程度,并對就業風險的不同維度具有不同的影響,促使失業風險整體降低且呈收斂之勢,但收入風險整體加大且分化程度有擴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