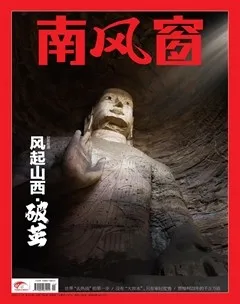“關稅人”歸來,系好安全帶

“除了愛情和宗教,最美的詞就是關稅。”這是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10月21日在北卡羅來納州競選集會上說的話。不用懷疑,特朗普對關稅是真愛。
在美國總統競選史上,關稅很少成為競選的重要話題,僅有的幾次例外,幾乎都是因為有自稱“關稅人”的特朗普參選。當然,僅憑特朗普的“愛”,肯定不足以使關稅話題在競選活動中“大賣”。更為關鍵的原因在于,美國的政治思潮進入了保守主義時代,為貿易保護主義提供了沃土。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表示,一旦當選他將對所有美國進口的商品加征10%至20%的關稅,對中國商品加征幅度可達60%的關稅。這意味著什么呢?
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計算:以2023年美國進口數據為基準,如果特朗普所稱的稅率落實,那么美國進口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將升至約27%。這27%是什么概念呢?1990年代至2017年,美國關稅稅率大多數年份保持在2%左右。2018年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戰后,當年美國關稅稅率是3%,此后的拜登政府基本維持在這個水平。
也就是說,即便特朗普的關稅威脅打個對折,美國關稅稅率也會翻上好幾倍。這是否會引發升級版的貿易戰?
2017年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宮時,對于他競選期間的關稅威脅,美國的貿易伙伴還在猜測其是否會兌現。今年大選塵埃落定后,這些猜測肯定不復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如何應對的兵棋推演。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在對外經濟政策上的巨變,可預料的結果是世界經濟的前路將更加顛簸。
不只是威脅
在10月15日一次關于經濟政策的電視訪談中,特朗普再次提到了他對關稅的愛和關稅倍增計劃。他說“對我來說,字典里最美麗的詞匯是關稅”,稱將對進口商品征收“歷史上最高的關稅”。
特朗普的語言風格內嵌夸張,但在言語所表達的行為方向上卻毫不含糊。這是不能懷疑特朗普會把對關稅的愛轉化為政策行為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關稅立場背后有著在美國政治思潮中日漸強勢的“理念”支撐。
這個“理念”背后的關鍵人物,就是貫穿特朗普第一任總統任期的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2021年1月卸任后的萊特希澤一直比較活躍,積極推銷他的貿易政策理念。這個理念集中體現在他2023年出版的《沒有貿易是自由的》一書中。在這本書中,萊特希澤主要論述的是為何美國應該放棄自由貿易,并稱“特朗普將被銘記為一位偉大的總統,真正的偉大總統之一”。他的重要衡量標準是,特朗普任內開啟了美國貿易政策的根本性轉變。
萊特希澤認定“根本性轉變”正在發生的主要論據,是拜登也在走特朗普的路。萊特希澤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特朗普離開白宮后)接下來的幾年里,除了幾個重要的例外,拜登政府繼續在沿著特朗普總統和我所制定的道路前進。”
萊特希澤的繼任者、拜登政府的美國貿易代表戴琪,今年6月出席大西洋理事會的活動時的表態印證了這一點。戴琪表示,她和萊特希澤一致認為美國必須改變貿易模式,兩人的差異只是在言辭上。
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明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后,主張更多的貿易保護、更高的關稅的聲音將在華盛頓變得更加主流。那么接下來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就任總統后,特朗普是否有不受約束地大幅加征關稅的權力呢?
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征7.5%至25%的關稅,大多數都是援引“301條款”。而且,至少從該條款的授權上看,特朗普是有權加征60%關稅稅率的。
今年9月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競選活動上,特朗普親自回應了這個問題:“首先,我不需要他們(國會議員),我不需要國會,但他們會批準的。”“如果他們不批準,我有權親自實施。”特朗普是在放嘴炮嗎?簡單的回答:不是。
在美國“三權鼎立”的政治架構中,憲法把與貿易相關的權力(比如征收關稅、締結貿易協議)賦予了國會。但歷史上國會議員的胡亂作為釀成嚴重后果后,國會通過立法,事實上把這部分權力讓渡給了白宮。這里面的關鍵事件,就是由共和黨議員推動的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該法案把美國的關稅提高到了40%至60%,導致美國的進出口萎縮超過60%,加劇了美國經濟大蕭條,也引發了更大范圍的貿易戰。
通過梳理193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的相關立法,不難發現美國總統在加征關稅方面,有著很大的權力和政策操作空間。比如,1962年的《貿易擴展法案》第232條,賦予總統這樣的權力,即可以以進口商品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通過加征關稅來調整進口商品。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鋼鋁加征關稅,就是援引這一法案。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任何法條都沒有給何為“威脅國家安全”下明確的定義,這意味著總統有著近乎隨意的裁量權。
1974年的 《貿易法案》第301條(即所謂的“301條款”)規定,如果發現外國政府的行為、政策“不公平、不合理或有歧視性”,那么總統有權采取包括征收報復性關稅在內的行動。2018年,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商品加征7.5%至25%的關稅,大多數都是援引“301條款”。而且,至少從該條款的授權上看,特朗普是有權加征60%關稅稅率的。此外,《貿易法案》的“國際收支權力條款”,1977年的《國際經濟緊急權力法案》等,都給美國總統預留了關稅權力。
把與貿易相關的權力讓渡給白宮,美國立法者們的本意,是避免激進的國會議員再次造成破壞性,但卻忽略了這一點:白宮的主人也可能激進。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學者斯科特·林西科姆在最近的文章中,指出了貿易權力被濫用的危險:“(1930年代以后的)貿易政策在80多年里一直運行有效,但特朗普暴露出了這些政策的一個關鍵缺陷,即其所涉及的法律過于寬泛和模糊,以至于總統可以基于可疑的理由單方面征收或維持破壞性關稅。”
反常識登場
在11月6日的勝選演說中,特朗普提到了“常識”:“這是一次歷史性的重新調整,將各種背景的公民團結在一個共同的常識核心周圍。你知道,我們(共和黨)是常識政黨。”然后,他列出了一串“常識”,希望“有國家邊界”“有安全”“有良好的教育”“有強大的軍隊”。這些“希望”的確都是常識。特朗普的這次演說對關稅只字未提,但恰恰是他的關稅理念,有很多違背常識的地方。
在關稅問題上,特朗普最反常識的地方,莫過于他堅稱美國的關稅是由對美出口的外國公司支付的。
一般來說,關稅增加后,對商品價格的影響會導致以下幾種結果,即出口商降價、進口商承擔漲價成本、進口商轉嫁給消費者,或者三者兼而有之。但在特朗普今年10月與彭博社總編約翰·米克利思韋一次關于經濟政策的對話中,當后者多次追問商品漲價的問題,特朗普除了以開啟“復讀”模式做回應,反復稱“外國公司會付錢”外,還表達了一個中心思想——關稅大棒并非是給美國人增加所謂消費稅的雙刃劍,而是迫使各國企業到美國建廠的政策杠桿;一旦外國公司迫于高關稅而在美國境內生產產品,美國消費者購買的這部分產品自然就不需要付高額關稅了。
然而,美國智庫“稅務基金會”2021年12月的一項研究發現,特朗普政府時期加征的關稅,大部分成本由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承擔了。具體來說,有進口商把成本做了部分轉嫁,導致商品價格微漲;有的進口商幾乎是完全轉嫁,商品價格漲幅等同于關稅漲幅;還有少數進口商趁機大幅漲價,商品價格漲幅超過關稅漲幅。而且,這項研究發現,沒有證據證明外國進口商通過降低價格(這里不考慮匯率調整因素)來吸收關稅上漲的經濟負擔。
不過,反常識并不影響特朗普沿著自己的邏輯思考政策。他更大膽的想法是,降低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用關稅的收入來填補上述虧空,維持聯邦政府的支出。在這個問題上,特朗普曾提及對威廉·麥金萊總統(1897年至1901年任美國總統)的欽佩,因為那時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主要來源于關稅。通過向外國企業收錢來維持本國政府的支出,目前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把美國拉回到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模式。
反常識并不影響特朗普沿著自己的邏輯思考政策。他更大膽的想法是,降低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用關稅的收入來填補上述虧空,維持聯邦政府的支出。
1914年美國稅制改革前,關稅長期是聯邦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但后來尤其是二戰結束后,這個占比逐步下降(2023年僅為1.8%)。2023年,聯邦政府的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收入是2萬億美元,進口商品總額約為3.1萬億美元。簡單計算就不難發現,如果要實現特朗普所說的“取代”,那么必須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高達65%的關稅。而且,還要確保在這個稅率下外國企業愿意對美出口,并且承擔關稅成本。
相比較而言,特朗普提及的另外兩個意圖或許稍顯嚴肅一點,即通過加征關稅保護美國企業免受外國同行壓迫式競爭,以及吸引外國企業赴美投資。
先說“保護”。根據美國普查局的數據,如今美國的進口商品中,超過一半是中間產品。特朗普全面加征關稅的做法,無疑會增加美國企業的采購成本,推高終端產品價格。如果這些美國企業的市場在海外,那么就會面臨海外市場的競爭壓力。如果考慮其他國家幾乎可以肯定的關稅報復,那么特朗普的關稅大錘會讓美國企業被錘兩次。
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經證明了,他的政策更突出的特點是“不確定性”而非吸引力。美聯儲經濟學家卡爾達拉等,2020年發表過一篇題為《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經濟影響》的學術文章。這些學者發現,特朗普政府時期的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達到歷史高點—僅在2018年(即挑起貿易戰的那一年)就使美國的投資減少了230億至470億美元。
斯科特·林西科姆寫道:“大量研究已經證實了這些影響,但它們實際上只是常識,誰愿意把數百萬美元押注在一個可能很快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或由于可能的關稅,而無法在國外銷售產品的美國新工廠上?”
系好安全帶
斷言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完全不可能達到效果,顯然過于武斷。但可以肯定的是,比效果先到的,肯定是混亂。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溫迪·埃德爾伯格和莫里斯·奧布斯特費爾德,在今年10月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可能的混亂前景:“每一個進口商和每一個所進口中間產品的購買者,都會將注意力從日常業務需求轉移到重新談判合同、重新配置供應鏈和游說關稅豁免上,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不確定、高度政治化的貿易環境中。”

上述學者描述的是美國國內的前景,更大的混亂是在國際層面。特朗普雖然多次贊揚關稅的“美”,但幾乎不提貿易戰,似乎他不提這事就不會發生,或者其他國家對美國加征關稅會無動于衷。美國加州大學經濟學者莫里斯·奧布斯費爾德,把特朗普全面加征關稅的想法比喻為“扔進貿易體系的手榴彈”,認為這“可能造成各國不再遵守貿易規范和規則的混戰,從而阻礙國際投資和貿易,導致世界變得非常貧窮”。
作為世界第一、第二經濟大國,美中兩國的貿易將受到多大沖擊,無疑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但同樣具有世界級影響的,還有歐盟與美國之間的貿易。高盛公司今年7月的報告預測,10%的關稅增幅將使歐元區的GDP下降1%。其中,受沖擊最大的是歐盟經濟的火車頭德國。法國一家投行預測,在最壞的情況下,10%的關稅增幅將使德國的GDP損失1.6%。這對于近年來一直在低位徘徊的歐盟經濟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如果不是致命一擊的話。
很有可能,特朗普也是這么想的:對歐盟的第一波關稅打擊,就以造成巨大損失為目的。
歐盟會如何回應?美國政治新聞網今年10月的報道透露了蛛絲馬跡。這篇通過采訪數位歐盟官員而撰寫的報道認為,歐盟正在為與特朗普進行一場高風險的大規模貿易戰做準備。根據該報道,在美國大選結果出爐前,歐盟就成立了一支快速反應小組,設在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秘書處。其中一位受訪官員表示,“我們將迅速反擊,而且是大力反擊”,“目的是給特朗普造成巨大損失,迫使他立即與歐盟談判,且以歐盟處于更有利地位的形勢(進行談判)”。
很有可能,特朗普也是這么想的:對歐盟的第一波關稅打擊,就以造成巨大損失為目的。政治新聞網的上述報道,提到了歐洲美國商會副總裁馬喬里·喬林斯對歐盟“以反擊逼談判”方式的擔憂:“問題是,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是否還有空間通過談判,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
美國大選塵埃落定,世界經濟繃緊神經,這也是特朗普在創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