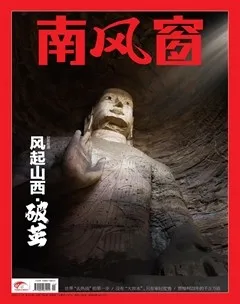哈里斯敗選,拜登被埋怨

11月6日,美國總統選舉塵埃落定后,眾議院前議長佩洛西在受訪時,被拍到忍不住滿眼淚水。次日,身在白宮的拜登在面對媒體談及政府交接時,卻顯得輕松,甚至露出笑臉。加上在投票當天,拜登夫人穿一件紅裙子前往投票站(紅色是共和黨象征色),拜登及身邊人的種種表現,給人在背后給哈里斯“挖坑”的印象。
在熱烈的選戰中,拜登和副手哈里斯各自所屬的陣營,還能勉強掩蓋一下裂痕。而在哈里斯敗選后,民主黨內部相互指責之聲高漲。競選階段拜登的一系列迷之操作,乃至對自己總統任期的定位偏差,導致了他成為哈里斯敗選后,黨內拿來鞭撻祭旗的對象。哈里斯的前公關總監甚至在CNN上呼吁拜登辭職,以便讓哈里斯短暫成為第一個美國女總統。
作為縱橫政壇50多年的老將,拜登的離去,意味著美國政壇一個時代的結束。民主黨在選舉中打出的“翻頁”口號,竟然一語中的,成為了拜登時代落幕的真正標記。
過于戀棧之嫌
指責的聲音,除了來自民主黨內部,還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對特朗普不滿并且公開給哈里斯站臺的共和黨建制派要員。
參加了2024年共和黨總統初選的新澤西州前州長克里斯·克里斯蒂,在選舉結束后的采訪中表示,拜登對自己總統任期的根本性定位出了偏差。“四年前當他坐在我這個位置(直播間)的時候,他就說自己是個過渡式人物。也就是說他只會做一任。因為他的年紀,他到時候會讓步。”
的確,從很多角度看,自2020年贏得大選到中期選舉,再到2024年大選,這四年里,拜登并沒有朝著競選期間許諾的那個方向前行。拜登贏得大選時已是78歲高齡,他是當時美國歷史上年紀最大的總統;假設還能連任,拜登在白宮干滿8年退休時也已超過86歲。用拜登自己的說法,他年紀太大,就是物色下一代民主黨領袖的“橋梁”。
拜登一直以來說話結巴,走路姿勢不乏顫抖,而且到了任期后期,被白宮內部人員曝出開會講話時老是思維跳脫。年齡和身體條件如此讓人“不安心”,拜登卻繼續苦撐。正如克里斯蒂所言,拜登一反選前作為“過渡式人物”的承諾,并沒有成為連接下一代民主黨人的“橋梁”,最終在選民心目中,不自覺地樹立起了“老朽”“脫節”“羸弱”的形象。
2024年6月27日,拜登跟特朗普舉行大選前兩人間唯一一次電視辯論,拜登聲音嘶啞,對于特朗普的攻擊幾無還手之力。此后,民主黨陣營內部以佩洛西為代表的逼宮和換帥的聲音浮現(哈里斯的好友也在事后被發現參與其中)。雙方又擾攘了許久,最終在7月21日,拜登被迫在一份公開信中宣布退選。至此,留給副手哈里斯替補沖刺總統寶座的時間,只剩下106天。
政治能量不能傳遞
也就在這106天里,拜登陣營一直低調地在向外界傳遞一種觀點:他本來可以再次擊敗特朗普。有論者稱,要是拜登依然參選的話,民主黨也不至于會丟失賓夕法尼亞州這樣的搖擺州。由于拜登和哈里斯的輩分和所屬流派的差異,可以想象兩人能贏得的支持者群體不會一樣。
有分析人士指出,8月民主黨大會上拜登受“明贊暗冷落”,9月總統級辯論中哈里斯試圖與拜登政策有所區隔,之后哈里斯越發享受聚光燈,較少照顧拜登的感受,甚至在競選團隊中排斥拜登的人馬。這些都給了拜登深深的打擊。
所以不奇怪,拜登屢次在哈里斯競選的關鍵時刻,發表與她立場有異甚至是添堵的觀點。更有一次,拜登還在鏡頭面前,瞬間戴上了繡有“特朗普2024”字樣的紅色帽子,甚至帶它上了飛機。這些舉動,被網民解讀為他對自己被哈里斯替代的不滿。
拜登在黨內積累了深厚的政治資源,卻一再被“加州幫”為代表的民主黨精英層輕視。拜登從1970年代開始經營政治地盤,和黑人組織乃至工會組織的關系匪淺。早在2019年拜登開始投入黨內總統初選之際,他的年紀和“低能量場”形象,一直讓他在候選人當中不算突出。論口才和智商,諸如奧巴馬和希拉里·克林頓這樣的精英,對拜登這種出身于非知識分子家庭又跟商界有過多來往的“老白男”,有意無意中總是透露出某種優越感。
在后全球化年代,隨著美國選民對全球化年代崛起的大城市精英感到厭倦,哈里斯這種試圖步奧巴馬后塵的進步派,也就未必有多大號召力。
但是,拜登在底層美國人面前的親和力,卻非希拉里、哈里斯或者奧巴馬等人可及。記者佩吉·諾努南這樣評價拜登:“有些人從政是因為熱愛政策。有些人從政是因為熱愛跟人打交道。‘跟人合得來’是個很老套的俗話,但拜登就是這么開始自己的政治生涯的,而且他得到了回報。”
在四年前初選中數度于黨內落后,拜登被認為是個對年輕和精英選民毫無吸引力的“過氣角色”。但是拜登的王牌,在于他深耕多年的基層黨組織,以及他跟工會的悠久淵源。就在拜登于初選中快要被淘汰的關口,跟他有多年至交的南卡羅來納州黑人國會議員詹姆斯·克萊本高調現身,號召黑人選民把票投給拜登,一舉帶動了基層對拜登的熱情。
而請動這些能扭轉選戰戰局的關鍵人物背書,往往需要沉淀多年的積累。相比之下,成長于加州的哈里斯,成長道路跟拜登截然不同,背后的政治資源也很不一樣。如果說拜登的成長和壯大之路,一直都是在東北“藍墻”州,那么作為西部海岸大城市的精英,哈里斯在民主黨內的政治光譜則完全不同。
盡管總統選舉很多時候是選政策,但是候選人的人設、外貌、種族乃至性別,也對選民產生不小的影響。同樣一個政黨,換了個總統候選人,支持者的態度就很不一樣。正如這次總統大選反映出的,相當一部分藍領工人和鄉村底層美國人,也包括駐扎海外的軍人,并不希望一個少數族裔女性成為美國的三軍統帥。
跟佩洛西可算是“老鄉”的哈里斯,屬于民主黨內的進步派,這類西海岸大城市的進步精英在墮胎權、性別多元化和種族多元化議題上具有優勢,但是面對美國廣袤的農村和北部鐵銹帶地區,未必有吸引力。在奧巴馬光芒依然強烈的日子里,好像哈里斯這樣擁有印度和非洲血統的候選人,也許能夠有強大的吸引力。然而,在后全球化年代,隨著美國選民對全球化然而,在后全球化年代,隨著美國選民對全球化年代崛起的大城市精英感到厭倦,哈里斯這種試圖步奧巴馬后塵的進步派,也就未必有多大號召力。
早在2019年,哈里斯就作為奧巴馬派系的代表,在民主黨黨內初選中吃了敗仗。在當年的初選中,長期在加州活躍的哈里斯,幾乎難以贏得北卡羅來納州和艾奧瓦州這些保守州的民主黨選民的代表票。四年之后,還沒真正接受紅州淬煉的哈里斯,面對特朗普的時候再次敗走東南部。
也是四年之后,哈里斯始終難以爭取到以下兩個群體的支持:男性選民和工會成員。美國最大的工會Teamster,在拜登退選前有44%的會員支持民主黨,相比之下特朗普獲得的成員支持率只有36%。到了哈里斯取代拜登后,她在Teamster所獲得的支持率只有34%,特朗普則反超民主黨人獲得了六成的支持。2020年大選中宣布支持拜登的全國消防員工會,也在這次選舉中拒絕表態。可以說,拜登多年來塑造的“工會之友”形象,哈里斯在一時半刻之間是難以復制的,這種資源也是難以直接“傳遞”給副手哈里斯的。
副手的詛咒
在1988年老布什作為在任副總統贏得大選后,美國再沒有在任副總統能夠贏得大選。事實上,老布什之前,上一個贏得大選的在任副總統,是1836年的范布倫,他當時是擔任安德魯·杰克遜的副手。
除了繼承上一屆政府的包袱之外,副總統“轉正”參選,還得面臨如何在過去四年中樹立自身政治形象的問題。根據美國相關法律,除了作為總統職位的“備胎”之外,副總統的作用在政府運作中形同“雞肋”。在任總統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治遺產,極少把重要的事項交給副總統處理。長期活在總統的陰影下,副總統在任期內一般難以交出讓人眼前一亮的成績單。
哈里斯在拜登的四年制約后,匆忙地被民主黨大佬們趕上了對陣特朗普的位子。相比之下,特朗普在2020年敗選后,就處心積慮再次沖刺白宮寶座。
在拜登當奧巴馬的副總統的前期,年輕的總統率領的年輕幕僚們,一直把拜登當作老朽過氣的“老伯伯”,作用更像是一個吉祥物。奧巴馬也是直到跟國會打交道受挫后,才開始重視拜登在參眾兩院經營多年的人脈,讓副總統成為了白宮和國會之間溝通協調的橋梁。

作為拜登的副總統,哈里斯長期坐冷板凳,可以說有著政策和個人形象兩方面的雙重不利條件。在美國選民普遍感覺到物價上漲壓力的不利因素下,哈里斯直接成為了拜登政府過去四年的經濟政策的替罪羊。在早間電視節目“View”的訪談中,哈里斯被問及自己的內閣和拜登內閣將會有什么不同的時候,多次閃爍其詞,最終的回答是“將會任命一名共和黨人到內閣”。
她的答案,激起了選民的反響:“如果給哈里斯投票為的是讓共和黨人入閣的話,那么干脆投給特朗普算了。”
四年以來活在拜登的陰影下,哈里斯不僅沒能好像在當參議員時那樣,能夠有一個輸出自己政治觀點和政策展望的平臺,甚至連曝光率也被白宮嚴格限制。拜登在就任初期為了宣示團結,還在多個場合中讓哈里斯一起亮相,但是到了后期,拜登幕僚基本上在重要場合中故意讓哈里斯缺席。
既繼承了拜登的包袱,又沒有四年的自由度去打造自己的個人政治形象,哈里斯在拜登的四年制約后,匆忙地被民主黨大佬們趕上了對陣特朗普的位子。相比之下,特朗普在2020年敗選后,就處心積慮再次沖刺白宮寶座。在被民主黨正式提名后,哈里斯難以挽回自己的政策走弱,個人形象也不強。到了9月底,她的選情就開始走向崩盤。“她就是被選出來承受敗局的替罪羊”,成為了民主黨內不滿者的說辭。
“出身貧寒,心比天高”的拜登,在政壇上摸爬打滾了50多年,終于坐上了總統的寶座。他作為建制派的最后一道光芒,最終還是難以為下一代民主黨精英找到新的道路。輸了白宮還輸掉了國會,面對下一個四年,一敗涂地的民主黨還是要經歷陣痛才能站穩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