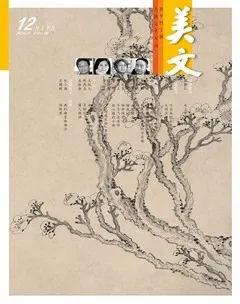尋南姜記【尋樹記】
一
潮州赤鳳鎮葵山村的村民李軍民曾經是村里的“南姜大戶”,他有幾年常種南姜。說到南姜的時候,他的感情相當復雜。
像很多潮州人一樣,從有記憶開始他就對南姜很熟悉。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他,小時候還是集體化的年代,村里每家每戶都會在自留地里再種一株南姜。南姜每年都會挖出來食用,只要留下一小株,還會繼續生長,就這樣生生不息,每一年家里不會缺了南姜。
赤鳳鎮的葵山村屬于山地,土壤很適合種植南姜。南姜喜愛山坡黃土,遠勝平原或者田地里的黑土,種出來的味道截然不同。
今天的潮州鄉村,多數人也會在屋前屋外種幾株南姜。如果從鄉村走到鎮上或者市區,你會發現,每個菜市場,南姜都不會缺席。因為,這是一種靈魂香料,是潮州人難以被代替的味覺坐標。
鹵鵝如果沒有南姜,就失去了最有標志性的味道,可以說是南姜成就了鹵鵝,它們的關系,是孟不離焦,焦不離孟。所以才有鄉諺:“擇塊南姜,去掉只鵝。”
粿條湯里的那點南姜末,也是這碗湯的點睛之作,雖然它在湯汁中浮泛四散,但形散神不散,一碗湯料有沒有它,可能就是籍貫的區別。
年底腌咸菜也離不開南姜。著名的橄欖糝就需要大量的南姜末提香。“個錢橄欖個錢姜”,這句鄉諺所描述的場景是橄欖糝制作的過程。這兩種本來就具備獨特香氣的食材,以1+1大于2的效果,成為潮汕美食的一個經典。
除了橄欖和烏欖,其他的小吃比如芥菜(潮州話謂之“貢菜”)、蘿卜(潮州話謂之菜脯)也都需要南姜末來配味。沫,微沫之意,量雖少而意至深,這點南姜末,是吾鄉泡菜在四川泡菜東北泡菜韓國泡菜面前驕人的理由。
街頭的“甘草水果”也離不開南姜末。桃李、酸芒果、楊桃、番石榴、油柑……甘草先熬制成汁,同時加入大量的糖、鹽、南姜,這道小吃,與其說叫甘草水果,其實不如叫南姜水果,畢竟甘草到處都有而南姜并不是。
其實南姜還不僅僅有吃的作用。
李軍民說到,小時候,他爺爺身上長了牛皮癬,那時候根本買不到治皮膚病的藥,于是他爺爺就經常挖南姜,搗爛之后再泡上米醋,止癢效果極佳。
二
但李軍民對南姜的感情不僅只有懷念。
幾年前,他曾經親自種植過幾畝南姜,大概一千株的量,并不算多。那次經歷讓他難忘。
那年的谷雨之前,他花兩千元買了一千株南姜苗開始種植。
剛開始種植的時候他是樂觀的,因為當年的南姜在市場上賣得很好,一斤可以售到四五塊錢。這一千株的苗如果管理得好,每株能產五六十斤的南姜。
但南姜與其他姜不同,很難在當年收成,從種植到成熟要經過兩三年,這時間差,足以讓價格出現難以預估的跌宕。
一般來說都是這樣的規律:某年南姜在市場上能賣出一個好價錢,于是就有一批人加入種植,那必然可以想象兩三年后南姜的出產量很大,供大于求,于是價格又跌得很低。所以本來抱著大賺一筆的希望,兩三年后卻賠得很慘,這樣的事經常發生。
李軍民說他當時種的一千株南姜苗,粗略計算每一年需要花費的費用如下:除草的人工費用一千元,肥料一千元,種植看護的人工費一千元,三年就是九千元,挖的時候,每人每天挖兩百斤,如果工錢以每人每天一百五十元算,兩萬斤的工錢就是一萬五千元。
那一年因為南姜產量巨大,每斤南姜的價錢低至一斤一塊多錢,所以李軍民種植南姜那幾年,扣除相關費用,算下來就等于是白忙活了幾年。
后來李軍民就很少大規模種植南姜了。但葵山村的其他村民還是時不時有人種植。最近幾年,南姜出現了一種病害,經常整片枯萎,農戶們暫時沒有找到辦法。
三
南姜英文名為Galangal。植物界;被子植物門;單子葉植物綱;芭蕉目;姜科;姜族;山姜屬;紅豆蔻種。
和其他姜科植物一樣,葉片上有橫出平行脈,葉柄基部下延,互生。它有著匍匐、塊狀的根狀莖,看起來像一塊老樹根,農戶經常嫌棄它挖起來特別麻煩,比一般姜更深,更多的溝壑,還要出動鐮刀來切割根部。挖出來后的南姜也要費更多工夫把藏污納垢或者腐爛部分做些雕削。
每年五六月份是開花季節,南姜開花非常美,是白色的穗狀花序,花香不濃但很清新。成片的南姜花,是它作為一個經濟作物之外,被人忽視的審美價值。
《農桑輯要》一書中,在姜這個條目上做如下介紹:
姜宜白沙地,少與糞和。熟耕如麻地,不厭熟,縱橫七遍尤善。三月種之。先重耬耩,尋壟下姜。……芽出后,有草即耘。漸漸加土;已后壟中卻高,壟外即深。不得并上土。鋤不厭頻。
從這一大段介紹,我們大致可以總結出姜科植物的一些特點:適宜白沙地,山地肥沃疏松、排水良好的砂質土壤最為合適。土壤應經常保持濕潤或靠近水源。黃河流域不適宜種姜。
這些特點,基本也是南姜的特點,只不過南姜仿佛是姜的升級版,形象比姜更桀驁,味道比姜更辛辣,成熟的時間也比姜更久。
四
南姜,帶有濃濃潮籍色彩的食物,以氣味強化自己的存在。它的氣味來源是在根莖含有的蘆葦姜素(Galangin)、山柰素(Kaempferide)、擗皮素(Quercetin)及揮發油。
人類從嗅覺得到的資訊,豐富得我們自己都難以解釋。
這也許是某種動物本能,動物借氣味判斷和掌握著它們的生存環境,樹木、植被、石頭、沙土、花、草、河流、海水……動物本能讓我們記得這些事物的氣味,以及與之伴隨的情境,以及與之鏈接在一起的回憶和情緒。
法國作家聚斯金德的代表作《香水》描述了一名嗅覺過人的天才格雷諾耶,小說里有過一段關于幼年的他的描述:
在三月的陽光下,他坐在一堆山毛櫸木柴上,木柴受熱發出噼啪聲。這時,他第一次說出“木頭”這個詞。在此之前,他看見過木頭不下一百次,也上百次聽到過這個詞,他也了解它的詞義……可是木頭這東西并未引起他足夠的興趣,促使他花點力氣說出它的名稱。在三月的那天,他坐在柴堆上才說了出來。當時那堆木柴……最上面的木柴散發出燒焦的甜味,木柴堆深處散發出苔蘚的氣味,而倉庫的云杉板墻遇熱則散發出樹脂碎屑的香味。
格雷諾耶是根據氣味來說出事物的名稱的。他極端化地形容出氣味對于人類的特殊吸引力。
據說農耕發展之后,膳食也跟著徹底簡化,于是我們的祖生也想盡辦法為我們的味蕾和鼻子重新帶來更多的體驗,其中一種做法就是使用風味特別強烈的植物部位。香草和香料的產生就是基于這個原理。
五
遺憾的是,在所有的香料香草中,南姜并沒有更多地為人所知。
對于潮州人來說如此重要的一種靈魂食物,它的名聲卻是封閉的。對于外地人來說,很難領略這種食物的微妙魅力。他們甚至很難將它和普通的姜區分開。但對于潮州人來說,姜和南姜,卻是完全不可互相替代的東西。
這幾年潮州粿條店比較有名,不少粿條店開到外地。比如廣州就有不少“潮州粿條店”,如前文所說,正宗的粿條湯會放南姜末,但很多外地人表示受不了這種特殊食材的特殊口感,南姜末干燥細碎,有點類似極細微的木屑,所以不少外地人吃“潮州粿條湯”的時候會特意要求不要放南姜末。
美國生態人類學家尤金·安德森寫了不少有關食物之生產與消費的論著,探討人類如何利用、分類和認識他們的資源,其中有一本著作叫《中國食物》。在其中,他提出,中國食物的烹調比亞洲大部分地方更少使用香草和調味品,但調味品的目錄并不少。
之后,他說到八角、花椒、桂皮,還有幾種香草。并說道:“作為調料,沒有一種比大豆的發酵物和蒜更重要。”“調味品份量小,通常由幾種味道濃烈的東西組成,其中最多的是發酵的大豆制品、生姜,以及蒜和蔥。”
我注意到,書中提及到的調料品,在蔥蒜的名下細談到了冬蔥、紅蔥、韭蔥、細香蔥,甚至還有蕌頭,但是,南姜卻沒有在此書中出現。而在百度百科上,關于南姜一項也寫道:古埃及時代,南姜被用作為煙熏材料。中古世紀時在歐洲,被作為藥材與辛香料使用。直至今日,南姜僅潮汕地區及東南亞地區仍在使用,其他各地已經極少得見。
(責任編輯:龐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