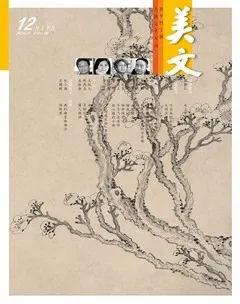它們比人更喜歡在山在野
一
深林里,于一個(gè)漫漫走山的人,行止由心,也各有妙處。行到水窮處、云起時(shí),可止;行到想止處、思止時(shí),亦自可止。
走得累了,想歇口氣。就歇歇吧。住了腳,拄著杖,就站在林間小徑上,喝幾口水,抹一把汗,聽(tīng)聽(tīng)鳥(niǎo)鳴——不聽(tīng),也就浪費(fèi)了。聽(tīng)了心里喜歡,也不必四處作揖道謝,那鳥(niǎo),也不是唱給行者聽(tīng)的。
路邊有草。看季節(jié),也看天氣,草上有時(shí)會(huì)飛來(lái)兩只蝴蝶,白的,或灰的;有時(shí)會(huì)巴著一只蟬蛻,赭褐色,半透明的,蟬已羽化升仙,剩了個(gè)空房子在曦光里顫顫悠悠;有時(shí)慢慢走來(lái)一只蝸牛、一只蛞蝓,蝸牛和蛞蝓是山里最從容的行者,但蛞蝓好像更貪吃一些,走山時(shí)會(huì)看見(jiàn)它們伏在蘑菇上大快朵頤;更多的時(shí)候,會(huì)有一朵幽幽的花,含苞的,半開(kāi)的,怒放的,或者干枯的。有時(shí)候草上啥也沒(méi)有,除了一顆露水,一縷風(fēng)。
再小的風(fēng),都能讓草伏向大地。那些卑微的草,每每望見(jiàn)它們?cè)陲L(fēng)里顫巍巍地鞠躬,就禁不住嘆一聲:好像一株小草,欠下了全天下的什么什么似的。它們的心中盛滿了疚意,總是想讓自己低下去,再低下去。
嗨,你用不著這樣的,想勸一勸它們放過(guò)自己,可是沒(méi)有一株小草肯聽(tīng)。隨其去吧。只是草的這種姿態(tài),弄得過(guò)路的風(fēng)有些忐忑,不太敢瘋開(kāi)了,撒丫子跑。風(fēng)實(shí)在是不忍心看著一株草,被自己虐成這個(gè)模樣。
樹(shù)和山泉就好一些。除非是大風(fēng)狂風(fēng)驟風(fēng),一般來(lái)說(shuō),一棵樹(shù)向來(lái)是不怎么把風(fēng)放在心上的。它們只管忙自己的事情。萌芽,分蘗,抽枝,吐綠,展開(kāi)小手一樣的葉片,開(kāi)花,或者悶著頭長(zhǎng)個(gè)子,把自己長(zhǎng)成木頭木腦的傻大個(gè)兒。
泉更沒(méi)心沒(méi)肺一些。它才不在乎世界上的風(fēng)風(fēng)雨雨風(fēng)言風(fēng)語(yǔ)呢。相反,它覺(jué)得山里太靜了,靜得有些憋屈,所以,總愛(ài)弄出點(diǎn)兒動(dòng)靜。
泉喜歡跟石頭拌一拌嘴,山中的每一塊石頭都是悶葫蘆,你不惹它,一萬(wàn)年都不吱聲。給泉惹著了,聽(tīng)起來(lái)籟聲籟氣的,好像倆人在逗哏捧哏,其實(shí),那也都是泉一個(gè)人的聲音。
山中小路,隨處即可小憩。若是想坐下來(lái)待一陣子,那可得好好選一選地兒。
夏天,晴日,無(wú)風(fēng),那么一泓清泉,一片林蔭,是很適宜的選擇。嶗山的每一條褶皺,每一道山谷里,都藏著無(wú)數(shù)個(gè)這樣的所在。溯九水,翠微之間,林崖之下,一條條水溪隨著山勢(shì),蜿蜒而下,因石賦形,漱玉成聲。近得水來(lái),人便進(jìn)入神仙境地清涼界了。
在水邊坐了,四下是泉籟,是風(fēng)聲,是草色和天光,是木蔭下的清涼,是千崖萬(wàn)壑間的靜謐。溪谷里大石光潔沁涼,午后的日光,又將樹(shù)蔭之外的石面曬到恰好的溫?zé)帷H希勺膳P,可偃,可掬泉,可聽(tīng)風(fēng),可折枝而撩魚(yú),可仰天而觀云,可照水而發(fā)呆,可倚松而忘求。此時(shí)此境,很自然地會(huì)想到一些泉水一樣的文字,一些林山一樣的古人。
先想到的,是太白和他的《夏日山中》:“懶搖白羽扇,裸袒青林中。脫巾掛石壁,露頂灑松風(fēng)。”呵呵,率意得很,又“脫”又“灑”的,這才是真正的灑脫呢。
又想到了東坡先生的《書(shū)臨皋亭》:“白云左繚,清江右洄,重門(mén)洞開(kāi),林巒坌入。當(dāng)是時(shí),若有思而無(wú)所思,以受萬(wàn)物之備。慚愧!慚愧!”
是的,有些時(shí)候,在山里,在林間,在溪邊,在一路嵐雨中,在白云青穹昊日之下,行走,佇立,沉默,出神,然后油然就是這種感覺(jué),“慚愧”;而且這慚愧,往往連著些感恩、知足、珍惜,還有些淡淡的,莫知由來(lái)的蒼憫、寥廓和悵然。
二
該寫(xiě)到蛇了。幾年前,深秋的一個(gè)午后,我從巨峰往山下走,過(guò)子英庵口之后,在半山的一塊凸起的崖石邊停下,小佇休息,抬頭一望,覺(jué)得高處的嶗頂襯著藍(lán)天白云,景色不錯(cuò),就想走到前面的草叢中,稍微平整的一塊空地上,取景拍照。
走了兩步,覺(jué)得空地上好像扔著一攤繩子,臟兮兮的,灰突突的顏色,覺(jué)得不大對(duì)勁,再一瞅,是一條蛇,蝮蛇,就是被稱作“土虺”的蝮蛇。
幾乎每年,都會(huì)在媒體上看到有人不小心被“土虺”咬傷后送往八醫(yī)治療的報(bào)道。差一點(diǎn),自己就要踩上這條正在曬太陽(yáng)的“土虺”。這是幾年來(lái)與“土虺”最近的一次。通常來(lái)說(shuō),每當(dāng)感覺(jué)到人走近,“土虺”就會(huì)很快地游走。但這條“土虺”大概在秋日午后的太陽(yáng)下曬得過(guò)于舒服,所以就懶得動(dòng)彈了。
常在山中走,怎能不遇上幾回蛇呢?遇上是正常的,不遇反倒是小概率。遇上是必然,不遇則是偶然。
蝮蛇是大山的一個(gè)提醒,提醒走山者,這個(gè)世界上,并非只有他自己一個(gè)在行走。
在通往嶗頂?shù)能娪霉飞希灿鲆?jiàn)過(guò)一回蝮蛇。它就臥在路中,見(jiàn)有人來(lái),并不驚惶,沒(méi)有要走的意思,也不想讓路。它是山中土著,且有著一般蛇類沒(méi)有的毒牙,自然有底氣和資本這樣做。
有個(gè)秋天,從嶗頂往明道觀去。那時(shí)天氣已經(jīng)涼了。是個(gè)晴天,太陽(yáng)當(dāng)頭照著,山坳里,樹(shù)木循著海拔,開(kāi)始漸次換上秋裝。光瀑瀉下來(lái),將一些率先變黃的烏桕樹(shù)葉打得明晃晃的,猶如金箔。風(fēng)一忽兒涼,一忽兒又有些煦暖。
在斑駁的樹(shù)影里走,人有時(shí)會(huì)有些微微恍惚眩暈的感覺(jué),好在小路是熟諳的,無(wú)數(shù)驢友的行走,讓小路盡管瘠瘦單薄,倒還不至湮沒(méi)于荒草落葉中。
在驢友小徑上行走著,四下幽寂、靜謐,偌大的山中,只有自己的腳步聲、鳥(niǎo)鳴,還有葉子落地和登山杖叩石的聲音。人的神經(jīng),很容易就松懈下來(lái)。然而,蝮蛇的出現(xiàn),一瞬間就會(huì)讓人激靈、警醒。前面是個(gè)小下坡,正走著,忽然聽(tīng)到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是鳥(niǎo)?不像,這聲音是貼著地的;是獾或野狗?不像,它們的動(dòng)靜要大得多,腳步也重;是風(fēng)吹落葉?也不像,風(fēng)葉之聲,要更空靈一些。當(dāng)然這些念頭只是一閃,還來(lái)不及做出判斷,就看見(jiàn)了一條土灰疾疾滑行的影子,只瞥見(jiàn)了它的脊背和尾巴。如果它伏著不動(dòng),我是很難發(fā)現(xiàn)它的,因?yàn)橥粱业捏w色與林中的石頭、泥土,以及落葉的顏色差不多。要不怎么叫土灰呢。蛇有著靈敏而精確的感覺(jué),它可以據(jù)此判斷向自己走來(lái)的,是一只鳥(niǎo)、鼠、蛙,還是一頭獾、狗,還是一個(gè)人,隨之作出獵食抑或逃走的選擇。轉(zhuǎn)眼間,它隱進(jìn)草叢中不見(jiàn)了。
吃這一驚,我的注意力不再只是散漫在林子中的光、風(fēng)和落葉上了,而是拉回到腳下,留神那不知隱藏在何處的土灰。同時(shí),手中的登山杖,也增加了叩擊路邊巖石和灌草的頻率和力度。打草驚蛇么,其實(shí)目的不是在打,而是提醒,提醒大家離得遠(yuǎn)一點(diǎn)兒。在這里,與一條土灰之間,距離不僅產(chǎn)生美,還是保證安全的必須。敬而遠(yuǎn)之,彼此安好。
還有一回,從嶗頂下小石橋到九水,又遇見(jiàn)了一回土灰。那是個(gè)燠熱的午后。在小路上走著,恰是向陽(yáng)的南坡,那個(gè)夏天又干旱少雨,草卻依舊生得荒蕤,那一段路走得很是不愜。忽然記起,這樣的天氣,很容易遇見(jiàn)出來(lái)尋水源的蛇。就更加警醒,一邊走,一邊不斷用登山杖敲打路邊。果然就驚動(dòng)了一條土灰。這條土灰在草叢中飛快地滑過(guò)。與我的不期而遇,肯定也讓它吃了一驚,原來(lái)在這悶熱的山中午后趕路的,不止它自己。
有時(shí)我納悶,一條蛇,沒(méi)有獾那樣的利爪,冬天來(lái)臨之間,它們是怎樣鉆進(jìn)泥土里巖石下,開(kāi)始漫長(zhǎng)的冬眠呢?不止蛇,還有青蛙和蛤蟆。比起獾和蛇,青蛙和蛤蟆不僅沒(méi)有利爪,也沒(méi)有尖牙。不過(guò)轉(zhuǎn)念一想,這用不著我來(lái)操心,且只管走我的山看我的山去。
蛇愛(ài)待在山里,只要腹中無(wú)虞,一條蛇可以把自己的一個(gè)下午撂在一塊巖石上,一動(dòng)不動(dòng),老僧入定一般。我知道有一些人也喜歡這樣,在林山之間,覓一處寂靜的所在,擲浮生半日于斯,一待就是老半天。我也愿意并且這樣做過(guò)。回頭想想,彼時(shí)彼境的那些知覺(jué)、情緒,那些空寂又沖平、索淡又寧?kù)o的感觸,一瞬間又復(fù)蘇重回,令人禁不住生出無(wú)端的歡欣與惆悵。
說(shuō)到底,人最終還是要回頭與自己相處,或早或晚。林山,不過(guò)是在自己與自己之間立起了一面鏡子,或者說(shuō),推開(kāi)了一道旋轉(zhuǎn)門(mén)。
不是有個(gè)詞叫造化弄人么,造化閑著無(wú)聊,就愛(ài)捉弄人來(lái)逗樂(lè)子、解悶兒。在山中走著,有時(shí)想:造化樂(lè)不樂(lè)意,高踞于群山之巔,俯視蒼黎,將天下蕓蕓眾生的來(lái)路與去處,都了然于胸呢?如果是我,我是想作出否定的回答的。
即便每一條隱沒(méi)在林中的小路,都被繪制在清晰的地圖上,我仍然相信,沒(méi)有一條線段,會(huì)自作聰明地認(rèn)為,自己洞察并掌控了它所標(biāo)注的那條小路的心脈與遠(yuǎn)方……
三
較之晴山,雨山里的行走,讓行者的注意力更多地收回在腳下。
林中滴水,很容易讓人的情緒和意氣清寂下來(lái)。滴水聲在山下不太容易聽(tīng)見(jiàn)。走山者剛剛從山外來(lái),耳朵里充滿的市聲不是一下子就能排空的,還有余音,還需要過(guò)渡和稀釋。再者就是山下的泉聲所致。越是在山下,泉聲越大越激切。天下之聲,人道是居高自遠(yuǎn),就泉來(lái)看,居高則聲自希矣。不急,走著走著,市聲遠(yuǎn)去,泉聲也隨著山勢(shì)的高起,由湍鳴漸次歸于杳渺,然后,林中的滴水聲就從一爿清境中凸顯出來(lái)了。
天籟是大自然的無(wú)心之作。雖是無(wú)心,有時(shí)卻勝于人間最工巧的樂(lè)師搔短華發(fā)拈斷莖須。當(dāng)一片雨做的云,際會(huì)一棵樹(shù)、一株草、山中的一條小路,一些事物便誕生了。比如這林中滴水之聲,比如滿山的綠和清寂,再比如,路上遇見(jiàn)的那些,蘑菇、枯樹(shù)、蝸牛、蛞蝓、蟬蛻、蛤蟆,還有靈芝。
不是所有的下雨天,也不是雨中的每一處所在,都適合撐著傘慢慢地走。遠(yuǎn)方暴雨如注,洪水肆虐,良田墟鎮(zhèn)成澤國(guó),多少人不得果腹安眠,千里之外的行者,這時(shí)撐著傘走進(jìn)一場(chǎng)災(zāi)患無(wú)虞的雨里,難免有些心生歉疚。“誰(shuí)都不是一座孤島”,可在這個(gè)世界上,如果沒(méi)有一樣的身受,哪里會(huì)有徹抵心腑的感同。冷暖炎涼,最是自知。
在山中,林間小路,景區(qū)石階,多雨的夏天,常常會(huì)看見(jiàn)蝸牛。蝸牛的殼,不比海螺殼,很脆弱的。行走中,會(huì)看見(jiàn)有些蝸牛被踩成一灘,殼是碎的,而軟體還在蠕動(dòng);還有的,被雨后太陽(yáng)曝曬成干癟的一條、一片,像蚯蚓、枯葉一樣,甚至只是貼在地面上模糊的一道淺痕。這些蝸牛不是舶來(lái)的那種大蝸牛,是土著,也不比山雀、兔子和蛤蟆,面對(duì)行者的腳步,它們行動(dòng)遲緩而又毫無(wú)防御之力。當(dāng)然絕大多數(shù)行者的踐踏,應(yīng)該是無(wú)意的,但這無(wú)意,其實(shí)也飽含著漠視甚至蔑視。鬧市中,人們的車(chē)會(huì)努力避開(kāi)或鳴笛示意路上的一條狗一只貓離開(kāi),可在山中,能有多少腳步,會(huì)對(duì)一只蝸牛或蛞蝓,保留一份生命的敬畏和等待其慢慢爬去的耐心?
有毒,無(wú)毒,是我們通常用以判斷臧否一株蘑菇的價(jià)值標(biāo)尺。嶗山今年雨下得較以往要勤,雨量也多。原本秋天才旺發(fā)的蕈子,暑季里卻也成了汛,蘑菇汛。覺(jué)得山里的好多果樹(shù),比如櫻桃,是有“大小年”的。今年,大約是逢上了蘑菇的“大年”也未可知,而不僅僅是雨水多的緣故。
在巨峰,暑天里,有次雨中走山,一杖徐行,無(wú)意間的一瞥,發(fā)現(xiàn)路邊樹(shù)樁上有些什么。近前一看,是兩朵靈芝,紅色的靈芝。枯朽多年的老樹(shù),年輪已不清晰,平常它是皸裂的,雨水讓它的顏色更加黧黑;然而造化總是給我們以想象不到的神奇,就在這腐朽之上,靈動(dòng)的生命萌發(fā)了。
雨下著,水珠滴答滴答落在樹(shù)樁上,落在靈芝撐開(kāi)的傘冠上。我拍了幾張照片,然后離開(kāi)。遇見(jiàn)即是緣分,看看就好,何必非得將其采下來(lái),據(jù)為己有?
靈芝么,其靈氣、靈秀、靈性,是這座嶗山,是山中的草木云嵐溪泉,是這場(chǎng)泠泠的雨,它們一起給它的,離開(kāi)這些,它可能成為一些人心目中的靈丹妙藥仙草,然而其山水嵐光之靈,卻將不復(fù)存在,或者,至少是消去大半。況且,一株草,真的能擁有使人祛除疾病延年益壽的特異功效么?就繼續(xù)往山上去。
雨天,人不多,從嶗頂回來(lái)的時(shí)候,留心看看那靈芝,還在。就讓它們?cè)谀莾喊桑谟昀铮舶察o靜地長(zhǎng)它們的去。盡管我知道,它們終將被人再次發(fā)現(xiàn),并采摘而去;而事實(shí)也印證了我的判斷,等下一次我再度走嶗頂?shù)臅r(shí)候,樹(shù)樁還在,靈芝卻已不見(jiàn)了。
雨山里,還遇見(jiàn)過(guò)山蛤蟆。這種蛤蟆比起印象里的癩蛤蟆,鄉(xiāng)村田野池塘邊的,小巧得多,膚色也深一些。在水窠里,它們通常浮在水面上,跟樹(shù)葉子一樣,老半天一動(dòng)不動(dòng)。林下的泉水,如果不是被陽(yáng)光照著,通常是幽幽暗暗的,山蛤蟆就浮在水上,又常常保持著靜默,所以并不容易分辨。
早先當(dāng)兵的時(shí)候,在外駐訓(xùn),在山中拉練,深夜里,行走,奔跑,天上有時(shí)下著雪,有時(shí)是雨,小雨,大雨,回想起來(lái),那蒼莽山中的一聲一聲,腳步聲,口令聲,吶喊聲,風(fēng)雨聲,磕打聲,仿佛從來(lái)沒(méi)有遠(yuǎn)去。當(dāng)下的大暑之夜,預(yù)報(bào)中的大雨正落在島城。夜雨敲窗,聲聲入耳,風(fēng)也在呼嘯,這樣的雨夜里,嶗山是怎么度過(guò)的呢?山中的落葉松、萱草、榿木、貓、蕈子、鳥(niǎo)、蝸牛、泉、獼猴桃、蛇、仙胎魚(yú),它們又將怎樣面對(duì)這彌天的風(fēng)雨呢?
四
嶗山一向是沉默的,但山中卻會(huì)集了好多愛(ài)說(shuō)話的,而且它們一說(shuō)起來(lái)就沒(méi)有停的時(shí)候。比如,風(fēng),不管松風(fēng)還是竹風(fēng),巽風(fēng)還是離風(fēng);比如,鳥(niǎo)、布谷、繡眼、白頭翁、山雉;比如,夏天的蟬,草叢里的蟋蟀,還有雨后的蛤蟆,以及蛙。可是這些,都比不上泉,山泉。
山泉有多能說(shuō)啊,誰(shuí)也不知道它是從何時(shí)開(kāi)始說(shuō)起的,大概自打嶗山從萬(wàn)古洪荒里站起來(lái)那一刻起。泉怕它寂寞,就把話頭兒扯開(kāi)了,越扯越長(zhǎng),越扯越長(zhǎng),再也收不回來(lái)了。
清晨說(shuō),傍晚也說(shuō);跟星星說(shuō),跟月亮和石頭也說(shuō)。在明亮的日光里說(shuō),在云里霧里霜里雪里也說(shuō)。跟毛毛雨輕輕地說(shuō)細(xì)細(xì)地說(shuō),跟微雨泠泠地說(shuō);跟春雨潺潺地說(shuō),跟夏天里的雷雨暴雨豪雨口無(wú)遮攔狷狂恣肆地說(shuō)。繞著落葉松、楓楊和山櫻桃的影子說(shuō),與憨厚的大石頭促著膝貼著臉說(shuō),也跟大腦瓜的小蝌蚪嘟著嘴喁喁喁喁地說(shuō)。
有時(shí),山泉說(shuō)著說(shuō)著,心中悠悠生出一支曲子,它就有了哼一哼的念頭。于是,泉就開(kāi)始了它的歌唱。大山里有無(wú)窮無(wú)盡的耳朵,無(wú)窮無(wú)盡的耳朵都喜歡傾聽(tīng)泉音。聽(tīng)泉的笑聲、歌聲,聽(tīng)泉的低語(yǔ)、吟誦,也聽(tīng)泉的怨尤、哀愁。不不,大家都知道泉是沒(méi)有哀傷和憂愁的,即使有,泉也將其深深地深深地藏在自己的心和影子里,澄澈的心和透明的影子里。從泉的心里流出的,永遠(yuǎn)是清澈的明亮的,光,還有那些讓聆聽(tīng)者感到開(kāi)闊、澄靜、欣悅的什么。
泉聲悅耳,泉聲更走心。魚(yú)樂(lè)意聽(tīng),布谷、蜈蚣和蕈子也喜歡聽(tīng),山中的一草一木,如果哪一刻耳邊突然沒(méi)了泉的聲氣,那么那一刻所有的草木,它們的心都是空的,都是焦灼不安的。
最樂(lè)意聽(tīng)泉說(shuō)話,也最愛(ài)跟泉聊天的,是魚(yú)。
嶗山是仙山,泉是仙液、神泉、圣水、靈泉,聽(tīng)泉的魚(yú),也自非池中之物,而是可以從大海一直溯向深山高澗里的仙魚(yú),有個(gè)好聽(tīng)的名字,叫仙胎。
在嶗山里走,有一次,走得累了,在一道水壩上小憩。仲夏時(shí)候,草木已到盛時(shí),高大的野山櫻、榿樹(shù)和落葉松枝葉婆娑,塘壩水上有風(fēng)來(lái),樹(shù)蔭和水上的光影明明暗暗。壩里的水很清澈,天氣晴好,山氣清和,一只藍(lán)蜻蜓,一只紅蜻蜓,倏然闖入這片澄明之境,振翼,懸停,又倏然飛去。就在不經(jīng)意間,在空明的水中,我發(fā)覺(jué)有什么輕盈地掠過(guò),像孑孓,或者像水晶的柳葉。定睛去看,呵,原是它們,嶗山山泉里的精靈,仙胎魚(yú)。
被泉水漱得很干凈的沙子,或者,在水中被折射的一道光,這,其實(shí)就是仙胎魚(yú)的影子,難怪它們不容易被發(fā)現(xiàn),也難怪它們擁有這樣一個(gè)仙氣靈動(dòng)的名字。仙胎魚(yú)很靈動(dòng)的,也很靈敏和警覺(jué),一點(diǎn)兒動(dòng)靜,它們就伶俐地急轉(zhuǎn)、擺尾、滑弋,倏然就不見(jiàn)了影子。其實(shí)并沒(méi)有游走,只是澄明的水,天然就是同樣通明剔透的仙胎魚(yú)的保護(hù)色,漣漪顫曳,波光閃閃,眩了目,晃了眼,所以無(wú)須遠(yuǎn)遁,無(wú)須隱匿,卻也難覓其蹤。
讓我奇怪的是,塘壩是塊石壘砌的,并沒(méi)有水道連通壩內(nèi)的塘水和壩下的小溪,那么,塘壩中的仙胎魚(yú),是怎么來(lái)的呢?深山老林,這么偏遠(yuǎn)的地方,不大可能有人捉了來(lái)放養(yǎng)。是下雨的時(shí)候,仙胎魚(yú)乘著雨逆著水飛進(jìn)塘壩的么?覺(jué)得是有這個(gè)可能的。小時(shí)候,在院子里的水缸中養(yǎng)過(guò)鯽魚(yú),原本這種魚(yú)是底棲的,很少浮到水面上來(lái),有一次下大雨,水缸并沒(méi)漫溢,雨后卻發(fā)現(xiàn)鯽魚(yú)不見(jiàn)了。水缸里的鯽魚(yú)可以乘雨而飛,山溪里的仙胎魚(yú),要越過(guò)這道石砌的壩墻,想來(lái)也是可以的。
山泉,仙胎魚(yú),這嶗山中最靈動(dòng)的兩樣,總是形影不離的。水中的魚(yú)影,對(duì)于心存善念的走山人來(lái)說(shuō),是眼中的秀色和心中的美意,而非口腹之欲。臨淵,但僅限于賞魚(yú)之悠逸,感受魚(yú)之閑樂(lè),而不饞羨魚(yú)之美味。這是一個(gè)樸素的走山人之基本素養(yǎng)。事實(shí)上,我所知道的許多走山者,他們也正是這樣做的,發(fā)乎于愛(ài),止乎于觀。
不唯走山者,那些歲歲年年朝朝暮暮待在嶗山里,臥于清澗澄泉邊的嶗山貓們,守著水中的美味生鮮,也從來(lái)不見(jiàn)其動(dòng)過(guò)捉魚(yú)撈魚(yú)的念頭。在北九水,橋頭,潭邊,竹下,石上,大貓小貓、黃貓花貓,有好多的。
尋常所見(jiàn),它們總是與游人的平靜對(duì)望中,得到后者投食的火腿腸、貓糧或者餅干什么的。看其中一些小貓,閃轉(zhuǎn)騰挪,翻筋斗,撲躍,身手甚是了得,按說(shuō)跳入清且淺的溪泉中,逮一條魚(yú)上來(lái),應(yīng)該不難。然而,這卻是人的想法了。嶗山貓和仙胎魚(yú),一個(gè)在岸上,一個(gè)在水中,不往來(lái),不越界,至多,不過(guò)是在這普羅共適的光風(fēng)霽月云嵐林泉里,偶爾相望一下,各守其靜,彼此無(wú)擾,也不念。于是這九水,自是流光澹沖,煙水寥邈,歲月靜好。
山中的貓有些佛系,泉呢,淡,素樸,清靜虛空,這不過(guò)是泉之一種。而天下之泉,性靈當(dāng)如天下之人,何止于千種萬(wàn)種。覺(jué)得泉有時(shí)道家,有時(shí)佛系,有時(shí)卻又很儒的。因石賦形,隨遇而變,入潭則空靜,出罅則激湍,也平順,也跌宕,也澄澈,也渾濁,不拘于定式,不羈于窠臼,不涸于壅滯,不踞于高上,善下而不爭(zhēng),自清亦能容,善變又抱一,是謂之自然之道。
泉心么,本來(lái)非一物,本來(lái)也無(wú)一物,所以不貪、不嗔、不癡、不慢,也不疑。然而,以人的心量來(lái)揣度泉,泉心又是很執(zhí)的。不是么?你看,大地上所有的泉,無(wú)論身在何處,十萬(wàn)大山,百丈高崖,萬(wàn)古寒川,莽莽森林,皚皚雪原,炎炎沙海,心心念念的,還是遠(yuǎn)方的海。
十年前寫(xiě)過(guò)一篇《嶗山賦》,其中寫(xiě)到北九水的泉,“觀夫北之九水兮,承天泉,出巖罅,攏草露,滲木脈,納瘦澗,匯細(xì)流,然后沿逶迤,順蜿蜒,側(cè)磐崖,穿參差,繞堅(jiān)頑,漫泥淤,一路回環(huán)跌宕,幾度曲迤蹣跚,歷盡輾轉(zhuǎn),方出乎萬(wàn)重、脫乎浮華、融乎浩淼”,并感念“然素以其之軟之弱之柔,無(wú)陷乎潭,無(wú)耽乎礁,無(wú)嘻乎塘,無(wú)餒乎壩,無(wú)滿乎庫(kù),無(wú)泯乎市,所以九九歸一,終得奔流入海”。所以從彼時(shí)的視角看,九水之泉,約略是個(gè)踽踽獨(dú)行煢煢孑立上下求索初心不改的書(shū)生了。
然而,有什么架得住時(shí)間。在歲月的群山中,光陰幾曾見(jiàn)老,泉的聲色、形容和味道也不老,老去的總是行者的腳步,那么泉心呢?那么曾于一剎回眸間照見(jiàn)泉心的行者之心呢?
(責(zé)任編輯:孫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