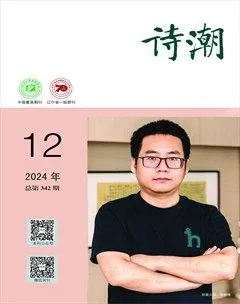回歸 [組詩]

趕時間的人
得抓緊,急著趕去現場
鉆進兩棟老式居民樓之間
盡頭只能右拐,僅限
一輛車的距離,必須減速
樓房和行人瞬時進入后視鏡
失去認識和寓意——門
和墻壁的距離,和真實
完全重疊。得抓緊
一腳油門,明顯卡頓了一下
我們并沒在意,必須減速
拱形門兩側的剮痕留有
三種顏色的車漆,紅磚
露出粉碎的骨頭
穿過一段橡樹林,左轉——
哦,我們見到要找的這個
充滿虛無主義的地方
我不得不承認,那個晚上
躺在救護車里痙攣的兒子
才是事實
語言與回音
雙手握著木棒轉動
或用石塊撞擊石塊
語言帶來光
野狼之詞
在燃燒
遠古,被回音吞噬
它的回音消失
重復——
無意識的絮叨
來自黑暗內部的旋渦又把
這一切卷進去(喪失
主體性),漂浮的
巖石撞擊我,我撞擊我自己
彼何人也
此時你來到鏡前,彼何人也
長臉頰抓著眼睛升起船帆
額頭凸起,石頭的表面用它撞擊
濃厚眉毛的弧度向上攀巖
嘴唇略顯寬大像神秘的旋渦
抖動肩膀,那細微的神態
是他坐在院子搖著蒲扇
蟲鳴的咆哮是大地已突圍
你一定會說他來了,我們閱讀
他人的故事,不必再去分別
哦,我想起那個夜晚坐在床沿看著
熟睡的孩子,說到這些
也說到他們,也意識到世事到此即止
一個一個的我,這不安的游蕩
在那里,又作什么生——
秋 日
樹長在手掌里
流水撥動石頭
在那兒有張嘴巴用力啜飲
一動不動地注視著自己
紅石榴沒有名字
我把它陳列燭臺
漏斗落下沙子
又逐漸倒回去
它們的月光寫在紙上
一切都在視線所及之內:
沒有他物
沒有移動
光的誕生,在森林深處
用木棍取火,所有事物
都與它們吻合:樹,水
以及石頭
兩只老虎
從一棵巨杉右拐,陽光
照在它斑斕的身體
趟水,觀察四周,低下頭
喝了一口,察覺到不同
敏捷地奔跑,咬住
鱷魚的脖頸上躥下跳,直到
它不再動,繞著走了幾圈
我發現老虎與老虎分離
像是在非洲草原追逐野牛
我們成為它丟失的影子
現在它在玻璃墻里閑逛
意志昏睡,高貴的四肢下榻
在原始森林神秘的事物
互相纏繞,將要合攏
我感覺它們臣服于你的右眼:
追逐,爭斗。左眼里的我
騎著金色老虎馳入玻璃的
是一眾的面癱,疲倦和虛妄——
不被定義的光
光從窗子找到她的鼻梁
找到她的黑發挺著的胸脯
找到身后的影子抵達廢棄的墻壁
一只蜥蜴回頭望著我
發現光在實驗它自己的形象
比如:田野,縹緲的青紗,縮在
拳頭的森林,窗玻璃或海洋……
看,光照在鵝卵石
——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生活于此的我必須把它精準地描述
看,墻壁的陰暗緊挨著坐下
一頓猛敲。那只蜥蜴猶疑地爬進
它的身體——
哦,這并沒有光
蛇爬至路面
空洞而又柔軟的水泥路
一眼就望到頭
躥出一條水蛇,看起來
比細長的水泥路更是慌亂
加大擺動幅度,往左滑
使前行變得緩慢
如果放下捕獵就去到豢養的莊園
如果放下詛咒和仇恨
就像一個母親疼愛打結的腫瘤
到底是沒有放下
在石階前沒有猶豫
返回潮濕的泥土
空洞而又柔軟的水泥路
時間把它拉長
我在昨夜的路面不能發力
致W.S.默溫
豎起一棵桉樹,蛇沿著樹干
蛻皮,劈開,倒向兩邊
海水從中間涌來,赤金色沙灘
寫下的詞語:棕櫚樹,紅色蝎尾蕉
木槿和那些瀕臨滅絕的植物
六角網眼鐵絲柵欄……生長出來
海浪淹沒,又去抹平痕跡
一只海象咬著滴血的肉
在爐火煎烤,他撒上孜然
是詩的詞語:棕櫚樹,紅色蝎尾蕉
木槿和那些瀕臨滅絕的植物
六角網眼鐵絲柵欄……滑動玻璃
從門前的塑料盆里長出
(哦,我的塑料盆就讓它
這么空在那兒吧)
玻璃制品
島嶼也是藍色的。海水時刻
在扎染,仿佛跳到一面鏡子里
沒有風,也沒有浪花
盯著鏡像的自己,沒有意識
也沒有思想。海鷗在玻璃飛翔
許多海鷗在藍色玻璃飛翔
它是虛無,也可能是一只飛到
另一只的位置,使所有事物動起來
風在動,水在動,浪花朝我撲來
它們并沒有動,只是自我重復
海鷗飛來,許多海鷗飛來
就這樣被纏繞而不能返回,凝視
某條魚被肢解的肉體,沒有人記得
只有藍色玻璃里無序移動的白色
由這唯一的困獸高舉,沒有人發現
臭 鼬
對于臭鼬的形象應是站在
橫著的樹枝咬著什么
現在它在白色教堂搜索食物
面對路燈拉長的黑影
遲疑地抬腳同時放下另一只
撞擊——隱秘的聲響
塵埃跳躍,劃開凝固的夜晚
像發現了什么,急速奔逃
忽地又停下,圍繞雕塑轉悠
被一束汽車的光照亮
驚惶地躲進灌木里
很長一段時間也沒有出來
但我知道灌木叢中有只臭鼬
弓著身體,鮮明的白色背對我
向時間和空間的深處延展
直至喪失臭鼬的屬性
短暫性失明,是我離得更遠?
意味一切已閉合,臭鼬的巢穴
野果和蟲卵懸掛舌尖兒
讓我在我的外面吹動它們
不朽地種植
灰雀在啄食一只青番茄
沾上農藥的蟲子蜷縮,打滾
而你什么都不是,在這植物覆蓋的
田野,我能對自己說些什么呢?
又看到那個身影,我仍與他
同在:除草,挖溝,噴灑農藥……
突然聚集的形象,是許多灰雀
我們都在認真地種植,不茍言笑
泡湯簡史
木耳泡在盆中冥想,它在虛構:
淫欲的肌肉躲進人間背后
坐在溫熱的池子,流動的血液
在加速,聽見心跳,那般清脆
似乎成為泉水的曲調,水霧
營造的氛圍增添神秘的色彩——
皮膚——關節——血壓——神經
唯一的皇冠屬于微量元素和礦物質
而松冠和瓷盆左下角的殘雪
仿古亭,以及喝水的野貓不在
虛構的事物中,包括:德仲寺下
赤身裸體的她把嬰兒舉高
木耳打開,仍在樹影籠罩的昏暗
被遮蔽著。懸掛——形態各異
——鐘乳石——這幽居的小屋
——仿佛是在集市上售賣的山貨
顏色重組計劃
那個女人走過來,穿著白色裙子
草坪青翠,在她走來時
那白色裙子綴滿的小雛菊
飄起,又卷在一起,自然垂下
讓男孩子們羞澀地看向它
盡管貼近土地我們卷成指環的
殘枝敗葉和根莖,像是終曲
巖石和玻璃之間,治學的警句
閃閃發亮。松樹底下盛開的小雛菊
根莖晃動,白色花瓣捧著它的
太陽,根莖擎著孤立的太陽
夾雜其中,即使變換自己的式樣
與我,仍不奉獻飛鳥和舊松,于是
三種色彩在鏡子里拒絕任何其他事物
草叢中的鏡子
將自己消耗在漣漪的形狀
使得藍色天空的鏡子破裂
而船只起伏,類似飛去的鳥雀
這僅僅是三種不同方式的語言
所有的一切都很平靜。嫩草
微顫,像新生兒展示著它的
哭聲和四肢的力量——貼合生命
一小撮的祝福(那移動的主體)
甚至瞧見它們的邊界,跟隨
草叢中亮起的光,盡管隱沒
聲音和形狀。使得開出白色的花
往年的根莖坦然處著……
無法照見自己,它不屬于我們
被它們武裝,而使之困惑疑慮:
相反飛行的鳥啾啾啼
不同屬科的兩只灰雀
“時間和黑暗卷走發光的物體。”
我瞧見它:右眼,半根樹枝
以及暗了又暗的天空,跳出來
——我跳出我:哦,你會向哪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