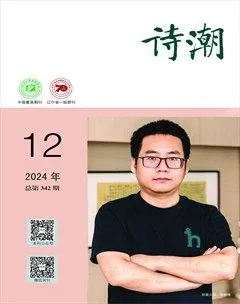雷平陽詩歌代表作品選
存文學講的故事
張天壽,一個鄉下放映員
他養了只八哥。在夜晚人聲鼎沸的
哈尼族山寨,只要影片一停
八哥就會對著擴音器
喊上一聲:“莫亂,換片啦!”
張天壽和他的八哥
走遍了莽莽蒼蒼的哀牢山
八哥總在前面飛,碰到人,就說
“今晚放電影,張天壽來啦!”
有時,山上霧大,八哥撞到樹上
“邊邊,”張天壽就會在后面
喊著八哥的名字說,“霧大,慢點飛。”
八哥對影片的名字倒背如流
邊飛邊喊《地道戰》《紅燈記》
《沙家浜》……似人非人的口音
順著山脊,傳得很遠。主仆倆
也借此在陰冷的山中,為自己壯膽
有一天,走在八哥后面的張天壽
一腳踏空,與放映機一起
落入了萬丈深淵,他在空中
大叫邊邊,可八哥一聲也沒聽見
先期到達哈尼寨的八哥
在村口等了很久,一直沒見到張天壽
只好往回飛。大霧縫合了窟窿
山谷嚴密得大風也難橫穿……
之后的很多年,哈尼山的小道上
一直有一只八哥在飛去飛來
它總是逢人就問:“你可見到張天壽?”
問一個死人的下落,一些人
不寒而栗,一些人向它翻白眼兒
光 輝
天上掉下飛鳥,在空中時
已經死了。它們死于飛翔?林中
有很多樹,沒有長高長直,也死了
它們死于生長?地下有一些田鼠
悄悄地死了,不須埋葬
它們死于無光?人世間
有很多人,死得不明不白
像它們一樣
清明節,在殷墟
野草和莊稼讓出了一塊空地
先挖出城墻和鼎,然后挖出
腐爛的朝廷……我第一眼看見甲骨文
就像看見我死去多年的父親
在墓室中,笨拙地往自己的骨頭上刻字
密密麻麻,筆筆天機
——誰都知道,那是他在給人間寫信
池 塘
我繼承了一筆只能描述的
遺產:池塘的四周
長著各安天命的蒿草、大麻、紫藤
水面有浮萍,但讓死水
更加靜默的,是虛空之上一層層堆積
一層層腐爛的樸樹和櫸樹的落葉
水面和穹蒼之間,斜掛著幾束
叢林間透射過來的陽光
成群結隊的蝴蝶,閃爍著,從那兒升入天國
它們沒有代替我,我仍然坐在一棵樹底
一身漆黑,卻內心柔和
仿佛有一頭大象在我的血管里穿行
天空里喝酒
我常常一人在天空里喝酒
地面上的親朋們
他們一直想不明白,我為什么要一個人
在天空里喝酒:“為什么?”
他們忍不住問我的時候,我往往
酩酊大醉了。舌頭腫大,思想混亂
根本回答不了他們的提問
只會像頭獅子,在天空中
發出一聲聲空洞的怒吼
我去霧里小住幾天
去梵凈山,我沒什么特別的目的
聽說那兒一峰獨立
天天都是大霧籠罩
我去霧里小住幾天
如果你們上山來找我
請對著大霧喊我的名字
致月亮
月亮,今生我想至少與你相聚一次
地點由你選定:天心、海面、曠野、寺院后
的山頭
當然也可以就在你的體內
或者我的屋頂上
只要能接到你的邀請,一個唯心主義者
他想聽見你凌空的腳步聲,想看見你
因一場酒席而停頓,關鍵是他想
與你為徒,扛一棵桂花樹走在你的前面
為你打掃滿天黑暗的灰塵
彈 奏
在老虎背上放了一張琴
老虎也樂意聽我為它彈奏一曲
但我,頓時失去了常態,不知道
彈奏什么曲子為好
最終什么也沒有彈奏
就在老虎背上放了一張琴
制 燭
在燭盞內的蜂蠟里插入麻繩燈芯
點燃之后,微黃的光亮中
他們繼續制作蜂蠟和細麻繩
割蜂巢,火熬,剔麻絲——每一道工序
博伽梵說過,在蠟燭形成之前都需要
苦心研修,且沒有哪一道工序
可以單獨完成功果。在此期間
還得有一個人,按時往燭盞添加
或新或舊的蜂蠟,不時用竹針挑直燈芯
如果黑夜延伸了長度,夜風一再
吹滅燭火,研修遇到了不可視為業障的
魔障,他們就會轉移到存藏蠟燭的地下室
一家人圍著豆粒大的火苗,低頭
干一些用塑料封蠟、裝箱之類的活計
悲觀,但又保持了光明的沉默
今 夜
今夜,世界在我身上
提燈外出找人
今夜:一頭白老虎。唯美,驕傲
出現在昭通府一位僧侶的書中
始終與作者保持幾公里的距離。但它后來
還是被饑餓的人士所屠
作者說:“我在昭通,彎著腰化緣
沒有看到過,沒有被虎血染黑的石頭。”
今夜,我學會了屠虎的辦法:從幾個方向
圍堵它,讓它逃進一個天坑
然后再用箭或槍射殺它
瀾滄縣的落日
江水流向落日,群山朝著落日低頭
天空,也為落日傾斜……
萬物統一感恩于
偉大而疲憊的發光體。在惠民鄉
一條半明半暗的山梁上,站著一群
合十仰望的僧侶。白鶴振翅飛向落日的一幕
他們認為,那是幾個寨子里的白衣人
從大金塔的尖頂上緩緩升空
黃 昏
黃昏時,近距離觀看白鷺
悠然打開翅膀
從身前低飛而去,身體一浮
一疼,一空:分明是自己白天的靈魂
飛走了。同時,在白鷺飛走的那兒
突然出現一個迎面走來的人
落日的光照著他,看不清面孔
像一團光有了人形,越走越近
兩個人影碰頭時
身體一震,一沉,一收
分明是自己夜晚的靈魂回來了
孤兒的泥塑
用馬車,一個孤兒
將泥塑的佛像
運往山頂供奉
走在坑洞與巨石的路上,馬車顛簸
泥塑的各個部位不停地往下掉
——到達終點,佛像只剩下幾根
綁著稻草的人形松木支架
他抱住馬頭
傷心地抽泣
四下蒼茫,無人給他安慰
馬伸出舌頭舔他的手背和眼睛
浮生如夢之五
暮春,我只對一件事情
感興趣:半夜起床,不點燈
坐在黑暗中吃櫻桃
——綠絲綢的風吹拂著白絲綢、紅絲綢
黑絲綢。像一條條綠色大蟒
拱動著脊背在浮世翻找它們細如槍管時蛻下的皮
順勢抽掉了我故鄉的屋梁。鄉愁變成使命
返鄉就是立場——但我困倦如那座不被認可的
童年游戲中的燈塔,不滅之燈已滅,徒然站在
船毀人亡的航線上。什么樣的火焰也不能
再將我點燃。什么樣的光也不能
再賦予我新的意義和樂趣
此刻,沒有人住在燈塔里替我說話
風壓彎了櫻桃樹的枝條,我只想提著一筐櫻桃
前往夢境。半夜起床
不點燈,坐在黑暗中吃櫻桃
一邊吃,一邊聽我的哭聲從另外的地方傳來
我:人物之一
寫詩時我總想抹掉以前的風格,
但抹不干凈。我努力地去成為另一個人,
但還是虛弱的這一個,并且無法還原。
我:虛構了自己所有故事的思想溫度,
把真實分切成無法縫合的碎片,把假象凝固
為白銀。
為天空種上茶樹,給星斗澆水。
無視烈火在馬廄和墓園中點燃、失控,以及
退隱于
宗教之后用燭火與柏香自焚的獵手。
——沒有陷阱可以困住誕生于陷阱中的人。
偉大的文字也并非世界最終的善。
我:每天坐在家門口,
觀看巨石和巨浪從街道上轟隆轟隆地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