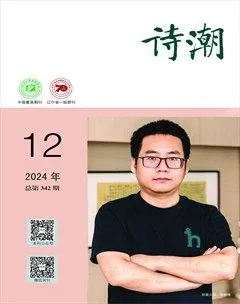“只是輕輕戰栗”:日常詩性感人的可能及限度
日常生活貧乏、簡陋,一成不變的流水時間,既冗長,又單調。有本事、會生活的人卻能制造波瀾,創生意義,活出滋味。寫作也是如此,有眼光、有功力、善經營的人,往往能從日常生活找到富礦,并發掘生活,開采情趣,提煉詩意。這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取向,詩人陸岸加入這一隊列。先來讀一讀陸岸由沙漠“窗框”攝取的一瞬。
遠處的春日正墜落在沙漠上。
而沙漠外的一個窗框內,
我的那個鐵制水壺又在悲鳴。
除了煮水,水壺還能干些什么。
除了煮水,火焰還能干些什么。
除了給她們裝水點火,我又能干些什么。
春日落下來了,整個黑夜慢慢豎起。
我周而復始地傾聽,一種越來越響的噪聲。
……
這是《煮水的黃昏》一詩前半闋,詩人用以命名其首部詩集,足見其重要性。“鐵制水壺”“煮水的噪聲”“落日”“黑夜”“星空”經由一個“煮”字,“整個黑夜慢慢豎起”,荒漠天地被勾連成一個生命體。架鍋生火,燒水做飯,這些凡夫俗子最普泛、家常、塵世的事項被摳凸出來,指向生命流逝過程的溫情與悲憫。“煮水的黃昏”,關鍵在詩眼之“煮”,“煮”,是司空見慣的家務事,卻“煮”出一番喃喃私語的詩意神奇。看似匱乏、虛空的現實,卻被“煮”出豐盈、充實、智慧的樂音。詩,往往就是這樣,當普泛、局促、有限的表象之門簾被揭開,語言指向一個非凡、廣闊、無限的世界,敞開了紛繁多樣的可能。
如果說《煮水的黃昏》還帶有傳奇色彩,那么《暮色》就更具波瀾不驚的生命日常屬性。一個春天的傍晚,走在黃昏的李樹林,白晝碎如細蕊,過往漸趨模糊、消逝,隱入無法捕捉的時間之中。晨光與暮色、生長和消逝、過往與曾經、芳烈和沉寂、短暫與永恒,在常人熟視無睹的自然物象深處,埋藏著一個寬恕與和解的海洋,以及比海洋更廣闊的人類學胸襟。“還有什么誓言能被記住,還有多少光陰不能被原諒”,箴言式的警句如通天之梯,引領著泥淖之人引體向上,徐徐攀升。“永恒的女性引領我們上升”,在非古典時期的今天,日常生活的女神就是詩人的自我詩意賦能。類似的還有《西廬寺》,文字樸實無華,敘述全無機巧,天地人間被構建成一個詩意容器,承接了天地人神共情釀造的玄妙與機趣。
西廬寺跟別的寺院并無兩樣
也愛在山中修行
那天我去的時候
滿山都是路人
滿山都是落葉
秋深了,這些離人之心
仿佛通天塔高聳
而塔下的一個掃地老僧
他慈眉善目
動作單一
不緊不慢
正是這颯颯秋風
那時天空分外寥廓
地面的金色收容了所有
除了西廬寺、通天塔和掃地僧等充滿文化粘連能指之外,詩所敘的落葉與離人在秋風中的情景,與通常所見的自然紀行“并無兩樣”,初讀似乎太過平白,既無生僻殊異構思之巧,也無驚悚穿越旨趣之邃,這樣的詩常常會被粗率略過。然而,當我們安靜下來,讓心沉潛到詩的意境和能量中,將欲望減持到“慈眉善目動作單一”修行狀態,一種自拯之力仿佛醍醐灌頂,人心趨于明亮、澄澈,“分外寥廓”,像“地面的金色收容了所有”。這樣的書寫“洗凈了視覺的復雜性,只留下一個充滿意義聯系的簡單形式和要素世界”(宇文所安語)。
沒錯,當我們說到日常生活之詩時,大約都要提到王小妮、韓東、于堅等人的開創修為。王小妮是“朦朦詩”一代詩人,從不參與社交,孤獨是其詩思不竭的源泉,她的詩注目個人的家長里短、油鹽柴米,能夠從一地雞毛中提煉鉆石閃亮的詩思。韓東則更加決絕,從反詩、反文化出發,用日常生活的瞬間感覺來敘呈生活物象的具體性,人物盡皆灰色之人,景象都是灰暗環境,卻清晰地洞察生活本相。于堅集搖滾歌手、混世魔王、酒鬼俗人于一身,寫夾著酒瓶回家的生活失敗者,滿紙大白話,卻能凸現底層的天真、淳樸和粗獷、野逸。總之,這一路詩拒絕隱喻,反對思想,放棄技術主義修辭,屬于晦澀、艱深、充滿學術詞藻詩風的另一面。這在當代詩壇,是一個豐富、立體、多棱的側面,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陸岸大致上可劃歸這一象限。《參觀屠宰場》短短六句,近乎伊沙式的口語,冷峻、平實、客觀的對峙和緊張,接通的是人類盲目、無知、悲苦的命運觀照。殺豬,吃殺豬飯,辦屠宰場,這是鄉村生活的日常人事,卻因整體喻寓而引爆了一場精神震撼。《方向》一詩,更是當下眾多無根之人感慨唏噓之作。林間即人間,“舊路”即天路,喜鵲即他者,垂柳即路友。鄉下和低處是生命來路與歸處。在新綠和荒蕪的輪回、消長之中,韭菜和歸人年復一年地邂逅、交匯。詩,并未動用多少豐饒的技術修辭,卻提供了意味盎然的境界分享。類似的還有《還鄉路上》《山行》《給薔薇》等,人間盛大,小徑幽邃,修行者引領我們在時間中回望自身。
引發我聯系韓東來解讀陸岸,直接原因是其《一握之感》一詩,“夜讀《買鹽路上的隨想》,讀到韓東‘生命常給我一握之感’”(《一握之感》);客觀上,則是陸岸的寫作形態樣貌與韓東、于堅等人相近,而且因“一見之地”,他們也有諸多聯系。從韓東“生命常給我一握之感”,到陸岸“緊緊一把握住”,二者之間既有藕斷絲連的靈感勾連,更具程門立雪的師承差異。比起“詩到語言為止”,陸岸不敢像韓東寫《大雁塔》那樣,以形式實驗對歷史文化的大雁塔實施顛覆重構;相較于堅法國新小說式的去個人化零度呈現,陸岸也不敢放棄對意義、旨趣的追求,以及意味、德性的承載。換句話說,陸岸的日常生活寫作,是從韓東、于堅的口語出發,汲取意象詩和意境詩的要素,雜糅了西部日常詩一些元素,走出一條兼容多家、混凝前人的個人化之路,寫法更接近晚近的張執浩。
“我傾向于使用那些與生活平起平坐的詞語來傳導我的情感,這些詞語因為與生活相齟齬、摩擦而產生適度的熱量,可以讓我筆下的文字具有正常的人性體溫,可以見證我曾經這樣活過,曾經來過這里。”
這是張執浩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語言觀。在日常生活之中,取萬事萬物平等的倫理立場,善待身外一切他者,友愛身邊諸多外在,向樸實無華的生活斟酌智慧和熱情,耐心琢磨飲食男女的活色生香,精準梳理生老病死的現實律動,不走調,不喧囂,不絕對拒絕隱喻,也不一味沉溺文化,通過個人化幽徑上的輕言細語來彰顯對人世和生命的洞見,這是張執浩的態度與立場。當年魯迅文學獎頒給張執浩時,我想,這也許是一種導向,一種引領。陸岸近年來扎實、系統、持續的寫作,就是響應這一引領的案例之一。他的詩,總體呈現為取材日常經驗,講究視角和構思,注重情緒釀造、言詞淳厚,照顧到公眾的廣泛接受。《踏空》《白鷺》《口器賦》三首小詩,以日常小動物、小生命來鏡鑒人的卑微存在,是對日常生活獨有發現,較好體現個人特色之詩。
《踏空》觸發于“黃雀”在枝頭跳躍這一日常事象,寫出人間的兇險關懷和他者悲憫。“黃雀”非凡鳥,集獵者、被獵、施暴、受害、天道、獻祭、叢林法則等多重屬性于一身,在漢語譜系中粘連著豐富的文化含義。詩由鳥而人,由枝頭而社會,落筆于“每天做著黃雀一樣動作”,為可能的“踏空”者給出充滿善意的提醒與自警。《白鷺》所敘也屬日常物象,將湖上白鷺、水邊人、蘆葦的倒影,錯落有致地勾勒在一個畫面之中,寄托了高飛與棲落、追逐與放下、自由與羈絆的人生哲理。《口器賦》,細節來自生活幽暗之處,洞幽燭微的能量令人震顫。
……
我在天目書院小住時
室內為蚊子的口器所困擾
這些柔軟的嗜血工具
隱蔽、渺小卻異常鋒利
而室外的蟬聲,與之呼應
日夜不停歇地掠食、歡鳴
十萬棵沉默的櫟樹、油松、水杉和八角楓
在烈日下和月光里跟我一樣輕輕戰栗
這土地上有多少苦楚和忍耐,一言不發
被這些明晃晃冠冕堂皇的宣告
被底下伸出的口器
暗暗折磨、榨取
而我仍舊跟它們一樣
只是輕輕戰栗
人生在世,觸覺受蚊叮,聽覺被蟬噪,視覺遭困厄,味覺挨苦楚,連同櫟樹、油松、水杉和八角楓,萬物同構于一場生命的苦旅。雙翅目纖小飛蟲口器是蟲子的天道工具,卻是人類身心整體必須承受的疼痛;小戰栗,大痛楚,小刺殺,大板蕩,世界萬物共振于一個感同身受的肉身整體。
必須申明,以如此標尺述評日常感覺一路寫作,并不意味著對學院現代主義、地域混血、女性主義、生態主義等寫作的矮化和排斥。詩,是多元、斑斕、繁復的,如同世界和存在,絕對不能定于一尊。日常寫作也好,學院寫作也罷,都只是詩的不同路數,并無高低、卑賤之分,更不能厚此薄彼、妄自獨尊。回首百年新詩,從胡適、廢名和魯迅、馮至以來,就有“口語敘述”與“化歐化古”、“懂”與“反懂”兩條路徑齊頭并進,以致后來發展成“大眾化”和“化大眾”意識形態寫作的對峙——當然這是后話,不說也罷。西方現代詩歌引入以來,也是如此,菲利普·拉金、謝默斯·希尼、辛波斯卡和托馬斯·艾略特、埃茲拉·龐德,法國超現實主義及后現代主義浩如煙海的詩人都在各自的專業路上探索發展,形成各自的傳統,相互激蕩,互為主體,構成現代詩豐富繁復的傳統。

由此看來,日常生活詩寫并不先天性地擁有話語優勢。當我們說日常生活詩是一種有難度的寫作時,恰恰是指,此類詩歌具有先天的寫作風險。在處理詞與物、語言與現實、歷史與未來、思想與情緒的關系時,日常生活詩歌隱含著諸多非詩元素,預埋著寫成大白話或口水詩的倫理風險,因而一般詩人不敢輕易入門。胡適雖為開山者,卻并未留下成功的遺產。即使韓東、于堅等,也在日常生活和瞬間感覺推進中,存在著一種類似歐陽江河智力游戲式言詞平滑那樣表象空轉的瑕疵。因此,無論技術經驗寫作,還是日常口語寫作,要寫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的好詩,都是一場艱苦卓絕的勞役,是“樹枝上兩只烏鴉,一只正努力把另一只染黑”(《賽里木湖》)的過程,需要耐心、智慧和誠實地勞作,需要像韓東那樣,“如今我只向匠人脫帽致敬”。
世上還有什么風景
比得上你年輕時遇見的一場大雪
大雪上只有兩個人的腳印
年輕時,當我們愛上詩,其實就等于陷入了一場終身談情說愛耳鬢廝磨,能否在時間的大雪中留下“兩個人的腳印”,誰也無法說準。詩,一門古老的手藝,也許終其一生難成一二,竹籃打水一場空。陸岸自湖州師院讀大學期間開始寫詩,我不知他最初的詩歌路數樣態,至少從目前狀態看來,他已從理念和寫法上找到一個適合的自我,并在這一向度上寫出一批足以成為個人標志的作品。但這一切只能代表過去。能否繼續以一定數量的優秀作品加固這一肖像,并在今后轉益多師,從多個向度上豐滿多樣的自我,寫出風格多元、言辭多姿、形態多變、辨識度鮮明的詩歌,這既是陸岸個人面臨的壓力,也是新詩本身面臨的壓力。好在陸岸的努力是扎實嚴謹的,在經營著知名度日益擴大的詩歌公眾號“一見之地”同時,他像一個藝人在現實生活的村巷街頭不斷穿梭,啜飲人間煙火,寫新作,找新人,組織新活動,在粗糙的物質化生活之石上磨亮個人感覺之鏃,激活感受力,創生意義,活出滋味。這是一種值得經歷、符合倫理的生活和人事。
今天,整個世界都陷入動蕩不安。面對資本、技術和金錢效率對人的欲望反復誘惑、不斷挑逗,個人如何保持心性和定力,以敏銳、細膩、精確、旺盛的感受活力進入日常,已經成為所有生命反抗異化的個人擔當。過好日常生活,安妥個人靈肉,愛身邊的人,愛卑微的事,寫出好詩的同時做好一個人,是陸岸與我們的共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