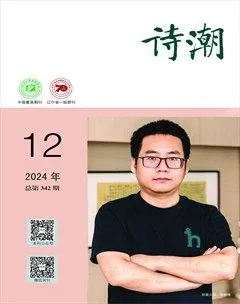河流之上[組詩]

小火苗
那時我還沒有近視。
兩百米外河對面山腳的
小火苗
確定地被我看見了
我沒有告訴誰。
八九歲的小姑娘能發(fā)現(xiàn)什么
驚天動地的新聞呢
我沒有太激動
只是遠遠地看著它
慢慢地變得更明亮和清晰
——其間我進了趟屋
抓了把瓜子和葡萄干吃
火在那時候仍舊什么也不算
我不知道我在期待什么
冬天,夜里,過年
大人們在屋里
歡樂又大聲地吃喝聊天
孩子們也沒誰會對寒冷的屋外
遙遠的小火苗感興趣的所以
我沒有告訴誰。
我也沒料到小火苗
會在一小時后變那么大
在兩小時后,徹底失控
三小時后成為鄰近三個村近百名男士
集體奮力要撲滅的東西。
三十年間我都沉默著
沒有告訴誰。
我不知道要告訴誰
火花原本是那么小
我也那么小。
遙 遠
選一門遙遠的外語
比如荷蘭語?
學習它,精通它
去說它的城市
阿姆斯特丹
或者萊頓
該找一座天橋嗎
或者地下通道
希望足夠幸運
找到一個乞討的人
在他身旁盤腿坐下吧
用靈巧的荷蘭語
與他打招呼
當過往的人少時
就拿誠懇的東方眼神
請求他
讓他將他的故事
全說出來
我要認真傾聽他
病中微悟
生病了才終于
離它們近了,那些
幾乎不值一提的事物
不明朗的陽光
凋殘的樹枝
偶爾才起的風以及
幾只閑散鳥雀
世界原來這么慢
這么安靜
每一個聲響
都能找到源頭
而只要我稍不注意
它們就又會
不知去向
好運氣
街道上車子太多了
空氣里飄著粉塵、噪聲
天氣也熱
要打的電話一個也沒接通
車子好不容易動了一點兒又到
紅綠燈了。30秒的紅燈啊
真晦氣,他說。說的時候
他看了眼后視鏡
后面車上一對年輕人
正爭分奪秒,熱情擁吻
歸來記
是否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先于朋友們半天,到達了5月9日下午
他們都還在田納西的凌晨無辜地沉睡
全然不知,廣州的天空正烏云密布。
幽暗的下午
也被稱為下午。下午的人們
——我盯著他們每個人的臉
絲毫沒有贏了誰大半天的喜悅。
沮喪就突然勾住了我。
夜晚遲遲不來
沒有華燈初上沒有歸心似箭
我手拿戰(zhàn)利品,不知要如何揮霍。
河流之上
小木船只剩下一半了。
魚兒,白肚皮朝上。塑料瓶
不遠還有另一個。
水草反復,被拖拽著
仍留在原地。
巖石屹立。樹木。房屋。村莊
村莊后綿延的山脈,它指向了
更遠處。遠處的事物
河流能拿它們有什么辦法
不像魚兒,除非它活著
不像小木船,如果有繩索系著
路
總想去路邊幫忙打撈些什么。
這么多輛車過去了
會有多少憂傷和困苦在里頭
它們?nèi)卦谲嚴铮P押在
路上,絲毫也不被
路旁的你看到可你知道
你還知道,它們不但此刻在
車子停下終點到來時它們可能依舊在
路上。有的路沒有終點。
求陰影部分面積
清晨的陽光將我的前院
切割成兩份:斜線正好
落在蔬菜壇的對角線上
突然慶幸,說不好
是因他給我做了個
規(guī)則的長方形蔬菜壇
還是在我大學一畢業(yè)
就娶了我
困 局
這么居高臨下,盯著
一只臨死的蜱蟲
是不仁道的,它這么小只
正沿著我的指紋爬行
它找不到出路。
我也找不到。
它當初選擇爬上我的身體
打算寄居在我溫暖的后腦勺
初衷一定不是傷害我我是知道的。
我也不是不能選擇原諒。
靜夜思
摁滅屋里的最后一盞燈
世界開始沉睡。
我走出房子,走向后院
不消進入更深處的叢林了
世界已經(jīng)是我的。
我停下腳步,環(huán)顧四周
黑暗里萬物都很清晰
林子里偶爾傳來細碎的聲音
很安靜,像是回到了最初——
蟲鳥是我的
動植物是我的
土壤,石頭,濕冷的空氣
如果此刻你在
你也一定是我的
我們可以一起待上一會兒
就一小會兒。然后我就要回去
要走向房子,要打開房門,要進去
我會摁亮屋里的燈
門會在我身后自己輕輕關上
為陌生的你寫一封情書
寫一首詩是容易的
相比較寫一封信。
詩可以寫著寫著就大膽起來
而信只能遮遮掩掩越寫越小心翼翼
這卻是一封信。你看
我的緊張正催逼著我
硬生生地,停頓
終止一個想法是難的
遠甚于結(jié)束一種行為所以你
千萬,不要回應我的心意。
就當它是一首劣質(zhì)詩:
奇怪的布局,不明朗的主旨
想要隱喻還找不著合適的詞——
讀著讀著就請你告訴自己你感受到的
一切可疑之物,都是錯覺
它只是詩人寫給另一人的請你
一定,這樣說服自己吧
一定,要繼續(xù)保持我們的陌生。
我們此刻距離是多少呢
以它為半徑如何?
我可以沿著你畫一個完美的圈
絲毫也不更近或更遠。
你什么都不要做。請你
什么都不要做。一點兒也不要
破壞,我們之間可能的
長長久久,心照不宣。
懷 念
剛睡醒時總?cè)菀纂x過去很近
特別是,夏日午后
院里的一棵大樹下
陽光細碎地灑你身上
有一點兒微風最好
躺椅或者木床不能太舒服
要有些嘈雜音:
知了,蒼蠅,母雞剛下完蛋
小孩子在奔跑或者哭鬧
門這時總是敞著的
一個男人走近了
手里拿著什么
屋里的女人迎上去
接過東西
他們輕聲交談著
你聽不清
你不愿意醒過來
日 常
日常有很多
想到了
就說出來
接一瓢雨水
看看它
然后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