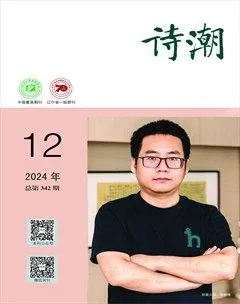旁觀者 [組詩]
過 敏
車子在疾馳,我已忘了
自己是駕駛者。沿途的路人
和來往車輛的阻滯,使我心生怨恨
——這些時間的幫兇
母親臉色慘白,紙片般走出房門
痛苦使本就深重的法令紋
深深勒進面頰——
兩道溝壑,盛裝著無形的苦水
以最快的速度抵達診所——
心慌、乏力,不斷冒出的紅疹
過敏原是母親日夜照看的一箱蜜蜂
(生活從不肯輕易給她一點兒甜)
在藥水的作用下,母親才逐漸立體起來
——“真要有什么事,等你趕來也晚了”
此時的我,陷入同樣的心慌、乏力
仿佛經歷著一種更深的無力診治的過敏
親情闡釋
還是無法打通自己的兩面
去得到一種關于親情的矛盾闡釋
記憶追溯到三十多年前的一個下午
母親手中的鋤頭,不小心砸向了自己的腳
一旁玩耍的我,看著母親
鮮血直流的腳趾,沒有絲毫心疼
甚至幸災樂禍般笑起來
母親的怒斥使我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這種無意識表現出的冷漠與薄情
與親人的疏離,以及
對他們的笨拙與假意懷揣的鄙夷
是我與生俱來對抗愛的喪失的一種途徑
如此刻,年近七十的老父親
把自己喝得滿臉通紅,對于他
敬酒途中的踉蹌,我只看客般投以一瞥
而他在坐回自己座位后,執意要給我夾菜
面容慈祥,已經干癟的嘴唇囁嚅著
仿佛說出什么驚天的秘密——
“因為你是我的女兒呀!”那一刻,始終站在
渴望逃離的高墻頂端的我,開始渾身發顫
不確定的雨
出門前特意看了天氣預報
它給了我錯誤而篤定的信息
就這樣,我走進了雨中
——沒有帶傘。細雨舔舐著我
從發絲、額頭、臉頰到全身
我因抵擋而蜷縮。像一個
潮濕而醒目的傷口——
在一場不確定的雨中
我反省欲望生成的瞬息
在它無意或是蓄謀已久的侵襲中
艱難地分泌熱度。而敞開
意味著身處險境,我還尚不知曉
虛無精確的指向和要義
安慰顯然已是多余。剩下的路
已經給不了我太多的想象
只是無從折返
——在泥濘洇開的崎嶇里
我的身體是一只容器
給身體做保養的時候,她的手
在我胸部的結塊處停下:
“你是不是很能忍?”
(這從皮肉直抵內心的關懷
來自一個陌生的手藝人)
我開始思考這具作為
行走的容器的身體都忍下過什么
——無數尋常日子里的平庸與乏味
愛意消失后詆毀謾罵的猙獰的嘴臉
繁重負荷下的嚴苛指責與無止盡的沮喪
四角的生活突然冒出的鋒利的刀尖
虛偽與謊言累積下的密而不發的雪崩——
許多個夜里,淚水與積壓的疼痛交疊
提醒我,活著是個巨大的命題
需要用更多隱忍而堅硬的骨頭作答
委屈,怨恨,頹喪,這些與生活持續
對峙的產物,在身體的某處日漸顯形
她繼續按揉撫摩,為我驅散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