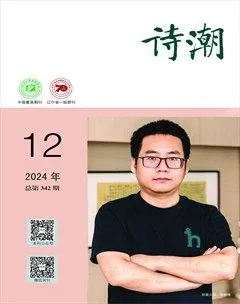當花瓣松開花蕾 [組詩]
2024-12-07 00:00:00董燕
詩潮 2024年12期
當花瓣松開花蕾
我是在太陽把自己變成一個紅彤彤的火球
悍然闖入重癥監護室的門窗時
才意識到房梁的晃動。母親
你把吶喊給了空氣
沒有回音壁的墻隔開了世界
風用冷涼的速度提醒
輸送到你體內的液體沒有了
母親。警報被酣眠吞噬
一個又一個病兆被誤讀
喉頭發緊。被暴雨淋打的葉子
轉眼就脫離了樹體
花瓣帶著不忍,松開了花蕾
一個人的戰斗
走廊里喊叫的人沒有了
她端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搬不動自己
也搬不動別人
她把手邊的衛生紙挪來挪去
像移動一個星球
她受損的肺葉,紫紺的指甲
骨肉分離的細瘦的腿和胳膊
塌陷的臉頰,干枯的手
她只是一個人在戰斗
不,她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不不,她真的只是一個人在戰斗
醫院的西側有一片萬壽菊
每天夕陽下墜時
醫院的門口總會坐著幾個人
住院的病人和陪護
偶爾也有探視者
和晚霞一樣平和
仿佛病痛不在
死亡也不在
時間追攆著時間
雨,排斥雨
從十六層病房外持續下墜
仿佛雨中奔跑的人是我
出租車里的人是我
被雨淋洗的東西路南北街是我
空中傾倒的雨是我
堤岸邊溺斃的人也是我
而病床上的母親
仿佛被暴雨拍打的枯葉
仿佛空中傾倒的雨是我
母親身體里所有的苦和疼
是雨中的一切
給母親洗腳
一雙沒有溫度的腳
在熱水里依然沒有溫度
穿鞋和不穿都是一樣的
沒有感覺
我一邊揉搓一邊想
這是母親的腳
一邊否定這不是母親的腳
腳往上的小腿
松松垮垮的皮和肉掛在骨頭上
像秋天的蘆葦
母親無處安放的痛
都在窗外的暴雨里翻涌
清 早
母親粗重的喘息像海浪
一定有一萬匹野馬在體內奔跑
說夢到自己割下大腿上的肉給父親吃
說不想吃飯一聞菜味兒就惡心
母親費力地挪動身體
到病床邊的座便椅上
暴雨拍打的菜地
大風、冰雹、霜凍、強降雨
全都提前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