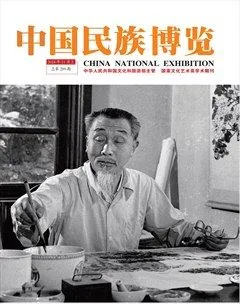《雨王亨德森》中敘事時間的倫理表現
【摘 要】在小說的敘事情境中,敘述者會對故事時間進行調整和控制以表達題旨和凸顯創作主體的倫理觀念。本文以敘事時間為理論基礎,從時距與頻率兩個角度分析主人公亨德森在敘事過程中通過實踐世界主義倫理以構建倫理身份,進而重塑人格的歷程。
【關鍵詞】《雨王亨德森》;時距;頻率;倫理身份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198(2024)21—023—03
《雨王亨德森》是美國作家索爾·貝婁的經典之作,描繪了主人公亨德森在非洲大陸的冒險之旅。作者特殊的身份經驗和美國經驗的雙重文化背景使作品蘊含了深刻的倫理意味,再加上作者荒誕夸張的寫作手法使作品在敘事時間上具備了豐富的可言說性。法國學者路易·加迪(Louis Gardet)指出:時間不是中性的,而是充滿強烈的感情色彩的(加迪,1986:168)。故事時間在敘事過程中被敘述者延展、壓縮而發生扭曲、變形,時間“具有了事件的意義”(伍茂國,2008:202),即時間在小說中具有了倫理性。本文以《雨王亨德森》為研究對象,根據敘事時間的時距與頻率兩個角度來解讀小說主人公亨德森在故事時間與話語時間不一致的節奏中憑借世界主義倫理實踐,不斷拓展倫理視閾以應對人性異化危機,進而構建倫理身份。
一、時距的倫理意味
時距,即故事時長與文本長度之間的關系(Genette,1980:87-88)。作者通過人為性改變敘事話語的長度實現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的互動,使敘述主體的倫理觀念得以凸顯。
(一)時間加速:違背倫理秩序
在《雨王亨德森》中,敘述者在敘述主人公從出生到婚后的生活時,事件在文本中被加速敘述。
“我生下地就有十四磅重,而且是個難產兒。長大后,身高六英尺四,體重二百三十磅;偌大一顆頭顱,凹凸不平……舉止粗野……到了結婚的年齡,為了討父親歡喜,我娶了個門當戶對的女人”(貝婁,2016:4)。
作品中的寥寥幾句概括了亨德森從出生到成年的早期生活,從這些敘述可以顯示出亨德森雖家財萬貫,學識淵博,卻舉止怪異,酗酒成癮,劃向空虛的深淵。再加上文本其他敘述,如:“我呢?也被認為是個瘋子……喜怒無常、脾氣暴躁、獨斷專橫,真有些瘋瘋癲癲的”“對人動輒又罵又叫,兇相畢露,搖頭晃腦”等(貝婁,2016:4-5),主人公顯然生活在一個混亂的倫理語境中。社會倫理語境是作品中無法規避的要素,但作者在敘事過程中調整與控制了敘事話語的長度,并沒有還原社會倫理語境的詳情,而是妙用有限的敘事話語對此語境進行概述,敘事文本把事件所對應的故事時間縮短、擠壓,通過個體生活歷程的物理時間在敘事文本中以加速行進的方式展現出來,蘊含著深刻的倫理內涵。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發展迅速,衣豐食足,利己主義與物質主義盛行,步入了充裕社會。但亨德森的精神不僅沒有因為物質財富的增長得到提升,信念的契約反而被瓦解,使他逐漸出現了異化。亨德森過度的物質享受衍生為一種導致他脫離本性的異己力量,他逐漸被物質上的富足異化成一架內里空洞的機器,淪為受物欲驅動的“獸”,最終違背傳統倫理秩序,深陷倫理困境。個體倫理的壓抑與混亂,家庭倫理的疏離與扭曲,社會倫理的異化與失序,揭示了當代社會趨于崩潰的倫理秩序,而主人公不過是在現代文明壓制下無數個體的縮影。在此,敘事時間對故事時間進行的加速處理有其深刻的倫理意圖。其一,個體在文本中的敘事時間縮短更加突顯了當代美國社會的倫理失序影響之深、持續時間之長,為后文主人公逃離美國倫理荒原前往非洲作了充分的鋪墊,同時也表明作者對主人公所作出的倫理選擇持堅定的贊成態度。其二,敘事時間的加速也表明敘述者對個體背離傳統倫理秩序行為地果斷批判,進一步批判了西方現代文明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道德沉淪的物質主義。亨德森正是在這樣的豐裕社會中倍受人性異化和精神崩潰的折磨,做出相悖的倫理選擇,最終違背了傳統倫理秩序。
(二)時間延緩:實踐倫理職責
在亨德森到達非洲的第二個部落時, 他部落首領達甫國王帶到獅子居住的巢穴, 讓他近距離觀摩并模仿獅子的吼叫和動作,從而吸收獅性。在這段敘事過程中,敘事時間被延緩、放大,讀者對文本中的人物與故事情節產生迥然不同的感悟。
“我站在原地絲毫不敢動彈,連盔帽蓋住了眉頭也不敢伸手去扶一下;我神情緊張,盔帽沿著皺額直往下滑。”(貝婁,2016:209)
這是亨德森第一次進入地下獅穴與獅子近距離接觸,他成為瓦里里雨王之后仍然對自己的倫理處境感到困惑并試圖向達甫尋求答案。在希伯來文化中,獅子是威猛、勇敢、力量和權威的象征,代表著生命和活力。在此場景中,敘述者以意識流動的方式展現亨德森恐懼的真實心理,心理時間成為敘事的主體。細節的描寫呈現出亨德森復雜的內心世界,文本中使用較多話語對事件進行敘述,而事件持續的物理時間又較短,敘事時間對故事時間進行的拉長與延緩意味著敘述者對事件進行主觀性地有意擴張,不禁影響了讀者的倫理判斷。亨德森第一次面對獅子的恐懼,實則是他本能欲望與道德倫理的沖突令其備受煎熬。面對如此煎熬,他想逃避回到之前養豬的生活,貪圖享樂,百無聊賴,為所欲為,又想克服困境,履行對他人的倫理職責,實踐世界主義倫理。阿皮亞的世界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實踐,通過與他人建立良好的倫理的關系以履行對他人的職責,阿皮亞“倫理世界主義”的核心是在倫理實踐中重視個體間關系的維系。亨德森以客人的身份來到瓦里里部落,成為雨王后他將幫助部落視為一種義務,履行好雨王的職責以更好地服務于整個部落,但這于他而言并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接受獅子恐懼等于接受歷史使命,敘述時間被拉得越長,就越突出歷史使命的艱巨,反映出亨德森的掙扎與畏懼,亨德森對部落的責任心正是世界主義對于倫理實踐的道德規范的表征。另一方面,時間在他接觸獅子的那一刻靜止了,被延緩的時間與長期艱難的流浪歷程相得益彰,強調個體進行倫理身份的選擇的前提是回歸種族身份,重視個體間關系的維系。獅子對于此刻的亨德森來說就是巨大的倫理困境,無論如何他必須勇敢的直面困難。敘述者主觀上對事件的放大同時也使讀者對人物的倫理職責有更深層次的感悟,這個場景以詳細描述的形式構建,通過事件,讀者可以看到亨德森無形之中從貪圖享樂到融入社會的直接轉變,他決心模仿獅子的各種勇猛姿態以汲取并內化獅性。因為亨德森渴望具有獅性是基于他的外在行動也像獅子,唯有如此,他才會有沖破精神牢籠、擺脫豬性的內驅力,抵抗異化,而這一切都在對部落人民倫理職責的實踐中得以實現。
二、頻率的倫理內涵
除了時距,頻率對展示倫理價值同樣具有重要作用。依照里蒙——凱南的解釋,敘述頻率是指“一個事件出現在故事中的次數與該事件出現在文本中的敘述(或提及)次數之間的關系。”(Rimmon-kenan,1986:56)
(一)概括敘述:深陷倫理困境
概括敘述是指講述一次發生了數次的事件。在《雨王亨德森》中,敘述者在提到亨德森的第二任妻子莉莉時,是這樣敘述的。
“莉莉自始至終不離開那個道德話題……莉莉講話聲音總不清楚……我知道她還在嘮叨那個話題。她那張神采奕奕的臉孔,那雙充滿喜悅的眼睛,不斷折磨著我……這話她說了足有一百遍”(貝婁,2016:17)。
敘述者這里采用概括敘述,將主人公與妻子重復發生的爭吵進行了籠統敘述,“自始至終”“總”“還在”“不斷”等這些詞淋漓盡致地表明亨德森對妻子深深的不滿與厭惡,同時也揭示了亨德森與妻子之間不可調和的倫理沖突。在傳統倫理秩序中,父親象征著智力和理性,而母親代表著無條件的愛和溫暖。這種男女性角色自然成為亨德森衡量莉莉的標準,在他眼里,這位嘮叨的妻子與他心目中理想的伴侶標準相差甚遠,因此造成了夫妻之間的道德隔閡。在當時的美國文化中,莉莉代表“沖動”的“濁者”,她過于情感化和不切實際。在面對巨大而復雜的社會, 亨德森同樣是貝婁所說的“濁者”類人物。“雖然為了討好父親,我取得了碩士學位,但是我的所作所為卻完全像個無知的二流子。”(貝婁,2016:32)亨德森受當時美國社會兩種極端文化的共同夾擊,對妻子的厭惡也就是對同屬于“濁者”的自身的厭惡,他們都是極度感性的受害者,同時也是施虐者,都處于一個混亂且疏離的倫理關系中。在這種關系中,亨德森無法有效地與妻子和睦相處,導致了家庭倫理關系逐漸僵化,對此他熟視無睹,并變得易怒、急躁,內心充滿著迷茫與無助。這一切合力作用于他身心之上,使他無所適從,又被狂暴、混亂的力量所驅使,不斷與妻子發生沖突,因此他極力渴望得到釋放,而莉莉就是被亨德森視為這一切負面情感的釋放對象。以至于“情況在不斷地惡化、惡化、惡化……終至錯綜復雜,不可收拾”(貝婁,2016:7),他這些荒謬行為與傳統倫理中智力和理性的標準背道而馳。在此情境下,敘述者此次對故事時間做出重新安排是根據表達題旨需要的有意處理,旨在表明亨德森沒有履行好傳統倫理的職責,導致倫理身份的缺失,深陷家庭倫理的困境。
(二)重復敘述:構建倫理身份
在文中有許多只發生一次卻被重復敘述了好幾次的事件。如亨德森哥哥狄克的死在作品中被重復敘述。
“狄克卻連大皮靴都沒脫就縱身跳去,靴子灌滿水后,他便淹死了”(貝婁,2016:35)。
“我們常去阿底隆代克鄉鎮度假,我的哥哥狄克就是在那兒淹死的”(貝婁,2016:96)。
“狄克同我們家其余的男人一樣,有一頭卷發,寬闊厚實的肩膀。然而,他卻在荒山里淹死了”(貝婁,2016:312)。
按照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觀點,“人的(倫理)身份是一個人在社會中存在的標識,人需要承擔身份所賦予的責任與義務”(聶珍釗,2014:263),亨德森對哥哥的關愛符合文學倫理學對于倫理身份的要求。狄克在一場事故中淹死了,這對亨德森及他的家人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對這件事的敘述貫穿于小說的始終,體現了對它的高度重視。起初,因為家庭原因他與哥哥的關系與外界其他人一樣及其冷漠與扭曲,甚至“舉行狄克葬禮的那天,我也堅持去干活”(貝婁,2016:313),而后在他的冒險之旅中的多次回想表示他深深地愛著狄克,他回憶道:“我很喜歡我的大哥狄克,他是我們兄弟姊妹中最有頭腦的人,是一頭不倦的雄獅,他在大戰中戰功卓著”(貝婁,2016:35)。對狄克死亡的重復敘述表達了他對哥哥深切的悼念。敘述者在不同敘事進程對狄克死亡進行重復敘述,說明這個事件對他打擊程度之深,每一次的敘述都表達了他對哥哥深切的懷念。阿皮亞賦予友愛以倫理觀念,自古希臘時期,“友愛”就是倫理學的一個重要概念。故此,亨德森與狄克之間的友愛關系已從普通意義的兄弟關系轉化成了一種倫理關照。亨德森獲的情感得以寄托,他的精神也從家庭倫理困境的束縛中成功逃離,都得益于這種倫理關照,“獸性因子”向“人性因子”轉變完成,逐漸擺脫了空虛的精神世界,構建了倫理身份。
三、結語
通過對《雨王亨德森》中敘事時間的分析,一方面證實了敘事時間與倫理表達之間的互動作用;另一方面,主人公從深陷倫理困境到倫理身份的構建,指明貝婁在小說創作中超越了種族狹隘偏見,通過履行對他人的倫理職責來探索抵制倫理荒原的途徑,建構了一種以人性為基礎,以 “愛”為核心的世界性倫理品質,表達了貝婁積極的人文關懷和肯定的倫理觀,也給人們在倫理道德出現缺位的當下提供了倫理指引,從而為構建多元社會、構建和諧的人文世界的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
參考文獻:
[1]Genette,Gerard.Narative Discourse[M]. Ith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
[2]Rimmon-kenan.Narrative Fiction : Contemporary Poetics[M].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1986.
[3](法)路易·加迪.文化與時間[M].鄭樂平,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4](美)索爾·貝婁.雨王亨德森[M].藍仁哲,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5]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6]伍茂國.現代小說敘事倫理[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
作者簡介:莫露(1995—),女,布依族,貴州獨山人,碩士,黔南民族師范學院,預科教育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