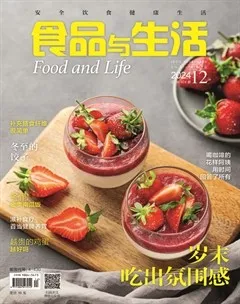霞飛路與羅宋湯
喬志遠上海通志館助理館員,中國科普作家協會會員,以筆描食,以文述史。
上海的飲食文化受西方影響頗深。開埠后,以美、英、法為首的西方列強在上海建立租界,為滿足在滬外籍與華籍買辦的需要,“禮查飯店”“匯中飯店”“德大飯店”等各具地方飲食特色的旅館、餐館在租界內相繼出現,為食客提供菲力牛排、奶油濃湯、華爾道夫沙拉等地道的西式菜肴,口味絕佳,價格不菲,很快受到上流階層的熱捧。不過,有一種西餐品類卻未走上這條“高雅”之路,而是憑借低廉的價格與扎實的用料在平民階層扎下根來,時至今日依然是上海人民餐桌上的常客,這便是來自俄羅斯的羅宋湯。
羅宋湯與上海的因緣要追溯到1917年。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不僅給中國帶來了馬列主義,也將數以萬計的沙俄貴族與軍官送到了上海。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亞歷山德羅維奇退位后,自知在祖國已無立錐之地的沙俄權貴紛紛出逃,其中一部分經西伯利亞進入我國東三省,一路向南,最終在上海停下了腳步。彼時的“上海王”盧永祥與美英租界當局對新勢力的涌入心懷憂懼,不愿意接收這些初來乍到的沙俄難民與兵士,只有法租界當局對他們關照有加,不僅定期安排救濟與診療,還允許他們在法租界工作和生活。在法租界當局的幫助下,落魄的沙俄人在法租界抱團定居,并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一帶活躍起來。這條街本是因紀念一戰時期法國著名將軍霞飛親臨上海而得名,但由于沙俄人多了,這條街便有了兩個別名,一個是沙俄人的稱呼,叫作“涅瓦大街”,涅瓦大街是圣彼得堡最繁華美麗的街道,沙俄人便借此表達對故土的思念;另一個則是中國人的稱呼,叫作“羅宋大馬路”,其中“羅宋”就是洋涇浜英語中的“俄羅斯”的諧音,“羅宋湯”也是由此得名的。
由于人生地不熟,沙俄人討生活的方法其實并不多,其中開餐廳算是海人得以感受到俄式紅菜湯、肉排、牛肉餅與炸雞的別樣滋味。也是在這一時期,許多曾在闖關東時期定居沙俄,擁有一定俄餐功底的山東籍廚師也因戰亂返回祖國,其中一部分流落至上海,看俄餐生意頗為紅火,他們也有樣學樣開起了中式俄餐廳,雖然菜品不及沙俄廚師講究,但口味更貼近上海人喜好,價格也更為低廉,反而在市場中占據了一席之地。“羅宋湯”就是其中的代表,作為俄式紅菜湯的改良版,按正宗俄餐的做法需用到高寒地區特有的產物紅菜頭,煮出的湯才能鮮紅艷麗。在上海買不到紅菜頭,山東廚師就用卷心菜與番茄醬做替代,不僅顏色相近,滋味也酸甜可口,且更合上海人的口味,后來甚至比原版的俄式紅菜湯更受歡迎。
就這樣,正宗俄餐廳與中式俄餐廳都在霞飛路一帶開枝散葉,短短數年內,霞飛路上的俄餐廳數量就達到40余家。為了招徠顧客,各家也推出各式套餐,其中最常見的便是以羅宋湯為中心的“羅宋大菜”,只需2角錢就可以 吃到羅宋湯配面包黃油,價廉物美,成為不少上海人的日常用餐選擇。1936年10月,有人在《申報》上談起羅宋大菜,對其贊賞有加:“(羅宋大菜)其中最有味道者,允推‘羅宋湯’,量又多,卷心菜同一塊大牛肉,實惠之至。”1939年12月,有人在《申報》上介紹上海生活雅趣時,也推薦讀者嘗試羅宋大菜:“(上海)現又新開俄國菜館數家,一小鍋羅宋湯,略佐面包,所費不多,即可果腹,所以人多趨之。”到了1940年,羅宋湯已然脫離了俄餐范疇,連市區的部分咖啡館也開始制作、販售羅宋湯,足可見彼時羅宋湯在上海灘的風靡程度。
1945年9月,二戰結束,沙俄難民的命運隨之轉折。1947年8月,蘇聯政府決意恢復難民國籍,并派出船只接收流落各地的俄僑。就這樣,在霞飛路一帶生活30余載的沙俄人與人生中的第二故鄉告別,再次踏上未知的旅程。無論是回到故土,抑或是再次流浪,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與霞飛路的故事徹底畫上了句點。時至今日,在繁華的淮海中路上,屬于昔日沙俄社群的有形印記早已消失殆盡,唯有羅宋湯依然深深鐫刻在每一位上海人的生活片段之中,默默傾訴著那段屬于過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