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風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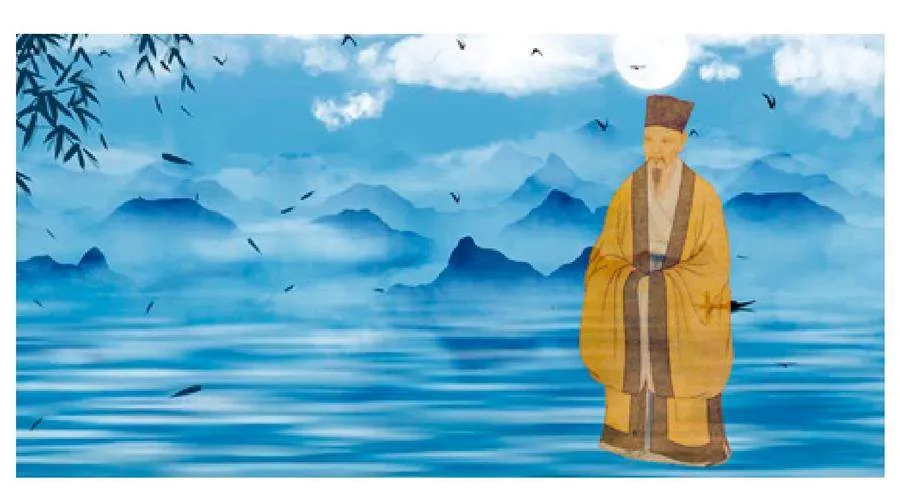
文人的風骨,之所以譽滿古今,有口皆碑,主要是因為其政治氣節,即我們常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政治氣節的產生,源自符合國家和民族大義的人格操守: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縱觀歷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風亮節,就像魯迅先生所說的:“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作為古代文人的杰出代表,蘇軾終生踐行愛國愛民的政治思想,恤民護民、直擊權勢、革新弊政、鞭撻丑惡的氣節浩然于天地間,萬世功名豈詩文。
蘇軾不僅文采流芳百世,其獨特的政治見解更令人刮目相看。1057年,蘇軾如愿以償考中進士,關于治國理政,他認為當時的國家形勢是“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因為“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主張“補偏救弊”“吐故納新”,并提出一系列改革舉措。1061年,蘇軾到鳳翔(今陜西寶雞鳳翔區)府任判官,這個官可以看作一個閑職。不過,蘇軾卻閑不住,他深入了解民間疾苦和地方實情后,寫下了《思治論》,指出“常患無財”“常患無兵”“常患無吏”,這“三患”是關系國家生死存亡的要害問題,進而提出“豐財”“強兵”“擇吏”的改革措施,并認為治理國家要“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向最難之處攻堅,追求最遠大的目標。
懷揣民本思想的蘇軾認為,法律得靠人去實施,為此任職期間始終堅持司法為民、德法相濟。然而,再好的法律,遇庸官、貪官則不能推行,只會流于紙上空談。一句“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讓曠達豪放的蘇軾敢于為民請命,敢于言辭激烈地譴責弊政。蘇軾抨擊大大小小缺乏才能、行為輕率、貪圖私利且品行卑劣的官吏是“不才茍簡貪鄙”之人。
蘇軾所處的那個時代,官場趨炎附勢的風氣盛行:在王安石(荊公)當權時,“唯荊是師”;當司馬光(溫公)主政時,則“唯溫是隨”,投機鉆營的官風官品,使得政治腐化之風盛行。1079年,北宋的朝廷大臣怕皇帝重新任用蘇軾,于是曲解詩文、斷章取義,將蘇軾逮進監獄,這樁著名的文字獄,史稱“烏臺詩案”。蘇軾那些曾經被人贊美的詩句,如今卻是指控他的證詞,卓絕才華在這一刻成了毀掉自己的利器。但是,蘇軾無所畏懼,對那些“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的人毫不懼怕,同時認為自己的文學作品是在特定的情境下產生的,不能簡單地將其等同于政治立場。在蘇軾自己和友朋的努力下,宋神宗權衡利弊后,決定網開一面,蘇軾總算保全了性命。一樁跌宕起伏的“烏臺詩案”,展現了蘇軾在逆境中堅韌不屈的風骨。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蘇軾的豁達與灑脫讓他善于發現平淡生活中的哲理,用樂觀笑對苦難,道出了“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人生態度。蘇軾一生,浮沉官場四十余載,既在朝堂身居過高位,也被貶至蠻荒之地擔任過小官,從黃州到惠州再到儋州,隨遇而安,所到之處都是“此心安處是吾鄉”。然而,無論多么窘困的環境,蘇軾都能泰然處之,始終秉持為民請命、心濟蒼生的情懷,追尋苦樂年華中的文人風骨:無事以當貴,早寢以當富,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
如果說李白代表了中國式的浪漫,那么蘇軾則塑造了中國人的風骨。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在不同的經典詩詞中與蘇軾相遇,傳承先賢風骨,凝聚前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