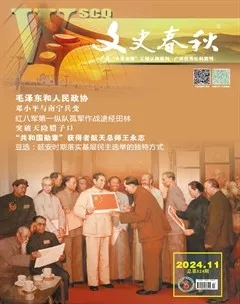突破天險臘子口
熟悉紅軍長征史的人都知道,紅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途中以少勝多,僅用5個多小時的英勇激戰(zhàn)就突破了天險臘子口,從此奠定了紅軍破局北上延安奪取全國勝利的基礎(chǔ)。天險臘子口位于甘肅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縣東北部,屬岷山支脈迭山系,為甘肅南部一道門戶屏障,是由川入甘的重要通道,素有“天險門戶”之稱。這里為深度切割下的中高山地貌,白龍江支流臘子河穿切侵蝕于峽谷間,最高海拔4515米,最低海拔1600米,平均坡度較大,多處山頂常年積雪,兩壁峰巒對峙。懸崖峭壁間的臘子河水深湍急,抬頭只見青天一線,地勢十分險峻,當?shù)孛裰V有“人過臘子口,像過老虎口”之說。1935年9月,長征中的紅軍抵達由國民黨軍魯大昌率部防守的天險絕隘臘口子,北上挺進面臨重阻,紅軍英勇奮起突襲與血戰(zhàn),出奇制勝攻關(guān)破隘,順利進入隴東臺塬區(qū),為北上陜甘腹地打開了通途。
為何進發(fā)天險臘子口
1934年,由于受王明等人的“左”傾路線影響,中央蘇區(q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即紅一方面軍)被迫放棄經(jīng)營多年的中央蘇區(qū),踏上艱苦卓絕的長征之路。1935年1月,為解除“左”傾錯誤思想把全黨全軍帶入險境的危急情況,中共中央召開了遵義會議,恢復(fù)毛澤東的軍事領(lǐng)導(dǎo)權(quán),否定了長征最初把湘鄂西作為落腳點而制定的“北去湘西”計劃,決定繼續(xù)西進,與活躍在川西北地區(qū)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創(chuàng)建新的革命根據(jù)地。
為實現(xiàn)這一戰(zhàn)略目標,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的卓越指揮下,先后取得了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一系列關(guān)鍵性戰(zhàn)役的勝利,最后又翻越山高雪厚的夾金山,成功和張國燾領(lǐng)導(dǎo)的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地區(qū)完成會師。但此時,蔣介石領(lǐng)導(dǎo)的國民黨看出了紅軍的戰(zhàn)略意圖,開始調(diào)兵遣將,準備將紅軍“圍剿”于川西北地區(qū)。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在兩河口地區(qū)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兩河口會議),幾經(jīng)討論后,最終決定繼續(xù)北上,創(chuàng)建川陜甘革命根據(jù)地的正確的戰(zhàn)略決策。
兩河口會議之后,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混編分成左右兩路大軍北上。其中,右路軍由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帶領(lǐng),計劃從毛兒蓋出發(fā),穿過松潘草地向班佑前進。左路軍由張國燾等人帶領(lǐng),計劃從卓克基出發(fā),先過草地去阿壩,再前往班佑同右路軍會合。行軍路線確定后,毛澤東等率領(lǐng)右路軍立即啟程,一路攻堅克難,用了6天時間,走出荒無人煙的松潘草地,順利到達班佑。但是,當毛澤東發(fā)電讓張國燾盡快率領(lǐng)左路軍前來會合時,張國燾未執(zhí)行黨中央北上的戰(zhàn)略方針,反而向黨中央拋出他制定的“南下川康邊”計劃,要求改變長征路線,轉(zhuǎn)為南下。在遭到黨中央的拒絕后,張國燾竟電令右路軍中紅四方面軍的某些干部,要求他們以武力脅迫黨中央南返,所幸電報被葉劍英看到,及時告知毛澤東。
當時擺在紅軍面前有三條路:一是被迫掉頭南下,重走雪山和草地;二是改道西進,繞道青海,前路漫漫,吉兇未卜;三是改道東進隴南武都,取道漢中,掉入國民黨軍重兵把守的勢力范圍,成為其“囊中之物”,有全軍覆沒的危險。而往北是甘南平原,人口稠密,物產(chǎn)豐富,也便于補給,且敵人的兵力相對薄弱。毛澤東從戰(zhàn)略大局出發(fā),堅定執(zhí)行兩河口會議黨中央制定的長征路線方針,帶領(lǐng)右路軍北上甘肅。繼續(xù)北進甘南,紅軍要面對必經(jīng)之途迭部縣強大的“攔路虎”——天險臘子口,只有通過天險臘子口,才能北上抵達甘南。
擇道天險臘子口遇強敵
1935年8月下旬,毛澤東、周恩來率領(lǐng)的右路軍進入甘肅省南部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縣達拉鄉(xiāng)俄界村。9月12日,黨中央在俄界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即俄界會議),確定紅軍長征北上入甘的戰(zhàn)略方針,指出張國燾分裂的性質(zhì)是破壞黨和紅軍,這次會議是長征途中的偉大轉(zhuǎn)折。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秦邦憲)、王稼祥、彭德懷、凱豐、鄧發(fā)、李富春、葉劍英、聶榮臻等人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關(guān)于與四方面軍領(lǐng)導(dǎo)者的爭論及今后戰(zhàn)略方針的報告》,明確指出紅軍北上的戰(zhàn)略方針:“北上紅軍經(jīng)過甘東北和陜北,以游擊戰(zhàn)爭去打通共產(chǎn)國際的聯(lián)系,以便取得共產(chǎn)國際的幫助。首先在接近蘇聯(lián)的地區(qū)創(chuàng)造一個根據(jù)地,休整隊伍,壯大紅軍,然后再以更大規(guī)模、更大力量進去陜甘寧大區(qū)域。”會議討論了長征北上的任務(wù)與到達甘南后的方針,通過了《關(guān)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發(fā)出了《為執(zhí)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會議討論制定了長征行軍路線,即突破天險臘子口,繼續(xù)向北進軍以獲得生存空間,打開全國革命的新局面。會后的第二天,毛澤東就率領(lǐng)紅軍隊伍離開俄界村向天險臘子口進軍。
迭部縣是一個以藏族居民為主的民族地區(qū),臘子口在當?shù)夭卣Z意為“險絕的山道峽口”,是川西北通向甘肅南部的重要門戶,有“一夫當關(guān),萬夫莫開”的險要之勢。為了在天險臘子口阻止紅軍北進,蔣介石調(diào)派甘肅軍閥、國民黨新編第十四師師長魯大昌部駐守于此。1935年9月中旬,毛澤東率西路紅軍向天險臘子口進發(fā),面臨前有魯大昌的國民黨軍隊阻截,后有四川軍閥劉文輝的追兵,周圍有當?shù)刈磕峥h土司楊復(fù)興(藏名班瑪旺秀)的地方隊伍和隴南武都胡宗南主力的險況,如不能盡快突破臘子口,將面臨被敵合圍的危險。
早在9月初,魯大昌就調(diào)集兵力進駐臘子口,做好排兵布局。國民黨第二旅第五團第三營駐守臘子口橋頭陣地,第二旅第六團進駐臘子口外圍的康多等地。西路紅軍進入迭部縣后,魯大昌又急忙調(diào)動第一旅第一團2個營前往增防,在朱李溝口、臘子口、康多、道藏、黑扎一帶,分點設(shè)置數(shù)道防線,尤以臘子口為防守重點,將第一團主力第一營配備于臘子口橋頭東側(cè)陣地,并分別在狹隘的橋頭和兩側(cè)山腰構(gòu)筑碉堡,以4挺重機槍排列在橋頭堡內(nèi),構(gòu)成交叉火力網(wǎng),嚴密封鎖橋頭地帶。原駐守橋頭的第五團第三營,調(diào)配到臘子口內(nèi)的三角形谷地,沿山腳固守工事,隨時準備增援橋頭陣地。與此同時,沿著山脈還有1個旅的防守兵力,在相鄰的岷縣縣城更有4個團的預(yù)備隊策應(yīng)支援。敵軍早已在此地配置強大火力和筑牢防御工事,張網(wǎng)以待紅軍的到來。
西路紅軍剛到達臘子口外,便第一時間與固守在此的國民黨軍魯大昌部展開激烈的交火。因敵裝備精良,且有防備,紅軍戰(zhàn)士們的幾次進攻都被打退。毛澤東多次派人去前線查看戰(zhàn)況,收悉戰(zhàn)況信息后,毛澤東深入研究,表明必須盡快突破臘子口,否則8000人的紅軍大部隊將有全部傾覆的危險。在離臘子口不遠的朵里寺內(nèi),毛澤東向紅一軍團下達了盡快打通臘子口的命令,紅一軍團表態(tài)堅決完成任務(wù)。聶榮臻等人離開朵里寺后,立刻同參謀長左權(quán)趕往紅二師,向師長陳光、政委蕭華下達作戰(zhàn)任務(wù),隨后眾人一同到前線查探臘子口地形及敵情,他們了解到:臘子口雖不過30米寬,但兩面都是懸崖絕壁,臘子河從山澗奔流直下,水面架設(shè)有一座木橋,是通過關(guān)卡的唯一道路,而駐守在臘子口的國民黨守軍在狹隘的木橋兩側(cè)構(gòu)建碉堡,橋東的山坡上更是布滿火力點,橋西擁有大量防御工事,敵軍在臘子口后方還設(shè)置有軍火及糧食倉庫,顯然是為長久堅守臘子口做準備。
聶榮臻等人知悉臘子口的敵軍防御工事后,便向陳光和蕭華詢問道:“這一戰(zhàn)你們怎么考慮?”陳光和蕭華回答道:“準備以紅四團擔任突破臘子口的任務(wù)。”紅四團是一支身經(jīng)大戰(zhàn)的攻關(guān)隊伍,在長征路上被譽為“開路先鋒”,在之前的烏江之戰(zhàn)、飛奪瀘定橋等重要戰(zhàn)斗中一馬當先,為紅軍大部隊的前進掃清了無數(shù)阻礙。聶榮臻等人聽聞安排紅四團做主攻,懸著的心安定了不少。毛澤東獲悉后,給紅四團動員打氣:“同志們,敵人在臘子口布防重兵,企圖將我們堵回草地去,這回頭路可是走不得啊!我們要徹底打破蔣介石、胡宗南、魯大昌的堵截,攻克臘子口,沖出岷山,到抗日前線去。”
紅四團團長王開湘(黃開湘)和政委楊成武接到作戰(zhàn)命令后,立馬排兵布陣,調(diào)動第二營采取正面強攻,爭取一鼓作氣打下臘子口。當日下午,第二營營長張仁初帶領(lǐng)全營干部偵察敵情,副營長魏大全指著敵人的防御工事說道:“敵情、地形明擺著,要迂回到敵人的側(cè)后實施攻擊是不可能的,團首長的決心是符合實際的,打臘子口只能正面強攻!”魏大全話音剛落,對面的敵兵就一排子彈打了過來,還對紅軍喊話:“你們就是打到明年,也過不去臘子口。”

聽聞敵兵的喊話,參加偵察工作的眾人更堅定奪下臘子口的決心。營長張仁初快速作出作戰(zhàn)指示,由第二營第四連擔任突擊任務(wù)。當進攻沖鋒號吹響時,紅軍的迫擊炮彈、重機槍子彈像雨點一般朝著敵人的防御工事掃射,四連的戰(zhàn)士們在重火力掩護下,直插臘子口附近的敵軍碉堡。防守的敵軍仗著火力和工事優(yōu)勢,朝四連戰(zhàn)士瘋狂掃射,無所畏懼的四連戰(zhàn)士拼著命沖到敵人碉堡近處。國民黨守軍投擲的手榴彈像冰雹一樣落到?jīng)_鋒隊伍中。瞬間,關(guān)隘通道上火光炸裂,沖在最前面的紅軍戰(zhàn)士在震耳欲聾的槍炮聲里紛紛倒在血泊之中。紅軍的首次沖擊以失敗告終。張仁初看著倒在沖鋒路上的眾多戰(zhàn)士,沉住氣繼續(xù)指揮作戰(zhàn),下達繼續(xù)攻擊的指令。
當接到新的攻擊指令后,二營的十幾挺輕重機槍集中火力,再次發(fā)起火力壓制,四連的戰(zhàn)士們又一次向臘子口的敵軍防御陣地猛攻,敵軍憑借地勢和火力雙重優(yōu)勢,瘋狂阻擊。瞬間,臘子口新一輪的戰(zhàn)火又熊熊燃起。紅軍的攻擊受阻,但突圍的決心毫不動搖,二營接連5次進攻都被打退,紅軍戰(zhàn)士的鮮血染紅了臘子口的進攻通道。
三天限時攻占天險臘子口
在前有強敵、后有追兵的嚴峻形勢下,戰(zhàn)況已到時不我待的界點。自臘子口開戰(zhàn)起,毛澤東頻繁派人到紅一軍團指揮部詢問戰(zhàn)況,密切關(guān)注臘子口的戰(zhàn)斗進程,可每次等來的都是我軍進攻接二連三被打退和紅軍戰(zhàn)士犧牲的消息。毛澤東等人既心如刀絞又憂心如焚。經(jīng)研究分析,9月16日下午,毛澤東代表黨中央下達了“三天必須攻占臘子口”的死命令。
午夜時分,聶榮臻等人領(lǐng)命來到前線指揮所,與紅軍將領(lǐng)們商談執(zhí)行黨中央關(guān)于“三天必須攻占臘子口”命令的作戰(zhàn)策略。他們與紅四團團長王開湘、政委楊成武總結(jié)前期進攻失利的原因,又和在場的紅軍將領(lǐng)們共同研究下步作戰(zhàn)策略,一致認為強攻不下,只能奇襲,并形成作戰(zhàn)策略:由政委楊成武指揮二營繼續(xù)實施正面強攻,團長王開湘則率領(lǐng)一營的一連、二連繞開臘子口右側(cè)的敵軍防御工事,攀登峭壁,迂回至敵人背后進行突襲。因為敵軍的碉堡沒有封頂,只要迂回突擊隊能通過懸崖峭壁接近敵人防御陣地的側(cè)線,占據(jù)制高點,就能以奇襲的方式打亂敵軍陣腳。
按照迂回奇襲的作戰(zhàn)指令,由紅四團團政委楊成武、二營營長張仁初指揮臨時組建的敢死隊,率先展開正面進攻,吸引敵人的注意力,為迂回突擊隊的奇襲引開火力。
如何攀登陡峭絕壁成為迂回突擊隊的棘手問題,在大家束手無策之時,隊伍中一個綽號叫“云貴川”的17歲小戰(zhàn)士站出來毛遂自薦去攀爬絕壁。原來,“云貴川”是苗族人,從小爬山采草藥,早就練成了一身攀巖的本領(lǐng),再險峻的峭壁都不在話下。在所有人的期待中,“云貴川”拿出一根系著鐵鉤的長竿子,奮力一舉,將鐵鉤鉤在巖石的縫隙之中,一步步穩(wěn)健向上攀爬。抵達壁頂時,他甩下由戰(zhàn)士們卸下綁腿編織成的長布條繩索。隨后,突擊隊隊員在一連連長毛振華的帶領(lǐng)下,拽著“云貴川”放下的布條繩索,一個接著一個向崖頂爬去。
此時,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左權(quán)等人都在相距臘子口200米遠的樹林里密切觀察戰(zhàn)況。突然,臘子口上空升起一顆信號彈,那是迂回突擊隊成功登頂?shù)男盘枺o接著一顆紅色信號彈又升空,這是迂回突擊隊即將發(fā)起從敵后方進攻的信號。瞬間,一枚枚手榴彈從天而降,落向敵軍沒有封頂?shù)牡锉だ铮跀耻娮哉J為最安全堅固的堡壘里炸開。毫無防備的敵軍霎時血肉橫飛,沒炸死的紛紛奪門棄堡而逃,敵軍布置在山腰間的火力網(wǎng)癱瘓,防御陣線和士氣瞬間崩潰。楊成武趁機指揮正面攻擊部隊發(fā)起沖擊,敵軍在紅軍突如其來的前后夾擊中很快潰不成軍,向后方亡命奔逃。駐守臘子口的敵第六團團長梁應(yīng)奎部急忙組織潰散的部隊進行第二個隘口的防守。但此時,紅軍的后續(xù)部隊已沖過木橋,和先頭部隊形成合力,沿著河岸縱深追擊敵軍。敵軍在慌亂中來不及組織有效的抵抗,紅軍很快攻占了第二個隘口,彈藥庫和物資補給倉庫也被紅軍攻占。紅軍得到充分的彈藥補給后,向敵梁應(yīng)奎的指揮部發(fā)起攻擊,梁應(yīng)奎沒有等來援兵,狼狽潰逃。經(jīng)過5個多小時的激戰(zhàn),9月17日凌晨3時許,紅軍突破防線,勝利攻破敵重兵扼守的天險臘子口,后又追擊敵軍殘部四五十公里,并一舉占領(lǐng)了甘肅岷縣的哈達鋪鎮(zhèn)(今屬甘肅省宕昌縣),徹底消滅了敵軍對臘子口的威脅,取得臘子口戰(zhàn)役的最終勝利。
臘子口戰(zhàn)役中,西路紅軍共擊潰國民黨軍新編第十四師第五團2個營及第一團、第六團各1個營,繳獲手提迫擊炮3門,糧食數(shù)十萬斤,鹽2000余斤,極大地補充了紅軍的軍需。攀巖能手“云貴川”小戰(zhàn)士在戰(zhàn)斗中壯烈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xué)會依據(jù)《甘南故事》一書這樣記述“云貴川”小戰(zhàn)士果敢英勇的壯舉:長征臘子口戰(zhàn)役,紅軍中有位名叫“云貴川”的苗族少年,通過一根竹竿翻越絕壁,帶領(lǐng)隊伍迂回到敵后占領(lǐng)制高點,策應(yīng)主力軍在正面攻破敵人堡壘。時至今日,依舊未能查清“云貴川”的真實姓名,但“云貴川”已成為革命戰(zhàn)爭中涌現(xiàn)的無數(shù)無名英雄的代名詞!
天險臘子口塑英雄
臘子口戰(zhàn)役,是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征程中極其難打、極其慘烈的戰(zhàn)斗,這一役打出了紅軍的軍威,充分展現(xiàn)出“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勇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臘子口戰(zhàn)役結(jié)束后,紅二師政委蕭華感慨良多,寫下詩篇:“峭峰插云一線天,隴蜀千嶂狹道連。秋風夜雨臘河吼,關(guān)險防固敵兇頑。絕壁峭巖擋不住,神兵飛下萬重山。橫掃白軍葬深谷,征師高歌進甘陜。”1965年,蕭華上將為大型聲樂套曲《長征組歌》作詞,他激昂地寫道:“臘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懸崖當云梯!”
聶榮臻元帥在回憶臘子口戰(zhàn)役時評價道:“臘子口一戰(zhàn),北上的通道打開了。如果臘子口打不開,我軍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無論軍事上政治上,都會處于進退失據(jù)的境地。現(xiàn)在好了,臘子口一打開,全盤棋都走活了。”
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重走長征路時,站在天險臘子口前由衷驚嘆道:“這樣的天險,是不可逾越的!”他在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對紅軍攻破國民黨重兵把守的臘子口贊不絕口,認為臘子口本來是不可能被攻破的——這是人力難以做到的!
為紀念紅軍長征突破天險臘子口的英勇壯舉,1984年甘肅省人民政府在戰(zhàn)役舊址修建了臘子口戰(zhàn)役紀念碑。紀念碑寬2.5米,象征二萬五千里長征,高9.16米,寓意1935年9月16日是發(fā)起攻破天險臘子口的時間。紀念碑背面鐫刻著含有臘子口戰(zhàn)役簡介和稱贊戰(zhàn)役具有重大意義的緬懷碑文:“……臘子口戰(zhàn)役的輝煌勝利將永遠彪炳我國革命史冊;在臘子口戰(zhàn)役中光榮犧牲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紀念碑南、西兩面鐫刻著楊成武將軍親筆題寫的“臘子口戰(zhàn)役紀念碑”8個大字。
2005年,臘子口戰(zhàn)役紀念館建成,位于戰(zhàn)役紀念碑處。紀念館館藏革命文物303件,設(shè)有“歷史和紅色革命文物展”基本陳列,展示臘子口戰(zhàn)役前后的一系列重大革命歷史事件,配有再現(xiàn)天險臘子口戰(zhàn)役的影像資料。如今臘子口戰(zhàn)役紀念館已成為黨員干部、青少年緬懷革命先烈、接受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場所。2009年,臘子口戰(zhàn)役紀念館被中宣部列入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名錄。2016年,臘子口戰(zhàn)役遺址被列入全國紅色旅游經(jīng)典景區(qū)名錄,每年接待前來參觀學(xué)習(xí)、瞻仰英烈的國內(nèi)外游客近百萬人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