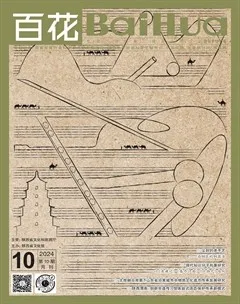雍乾時期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設(shè)計制作的雙重效能





摘 要:雍乾時期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作為御制機構(gòu),其承擔(dān)的設(shè)計制作活動不僅具有“家”與“國”兼顧的政治效能,還具有“技”與“藝”集合的藝術(shù)效能。在政治層面,造辦處不僅為皇家日常生活服務(wù),還承擔(dān)著國事軍需用品的制造任務(wù)。這些物品的制作和使用,既體現(xiàn)了清朝嚴(yán)格的等級制度和禮儀規(guī)范,又展示了清朝對多元宗教和外來文化的包容與融合。在藝術(shù)層面,造辦處的工藝品不僅在技術(shù)上呈現(xiàn)出多樣化和綜合性,還在審美追求上融合了民間藝術(shù)和西方藝術(shù)的元素,展現(xiàn)了清朝制造技術(shù)與藝術(shù)的輝煌成就。這種藝與技的結(jié)合,不僅提升了工藝品的藝術(shù)價值,還推動了工藝技術(shù)不斷進(jìn)步和創(chuàng)新。
關(guān)鍵詞:雍乾時期;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設(shè)計;效能
一、政治效能——“家”與“國”兼顧
(一)為皇家日常生活服務(wù)
1.皇家生活用品制作
皇家生活用品的制作與使用,是體現(xiàn)皇權(quán)至高無上和維護(hù)皇室尊嚴(yán)的重要手段。其中,皇帝的文玩雅器最能體現(xiàn)皇帝的個人品位和審美情趣。雍正時期,皇帝命造辦處設(shè)計制作了大量的眼鏡和寶冊,還對歷代古董進(jìn)行了大規(guī)模修復(fù)和改造。乾隆帝在位期間,不僅熱衷于收藏奇珍異寶,還親自參與設(shè)計大量精美的百什件、多寶格(圖1)、寶貝格以及博古格。這些文玩雅器,不僅在技術(shù)上體現(xiàn)了造辦處高超的工藝水平,也在設(shè)計上體現(xiàn)了清代帝王的審美取向和文化素養(yǎng)。
2.皇室穿戴用品制作
皇室成員的穿戴用品,也是御用物品的重要組成部分。造辦處負(fù)責(zé)籌備皇家除食物之外的所有隨身物品,包括服飾、配飾、飲食器皿以及出行時使用的傘、車、座椅等。這些用品的制作和使用都必須遵循嚴(yán)格的禮制規(guī)定,體現(xiàn)著清朝森嚴(yán)的等級制度。例如皇帝的龍袍(圖2)、朝珠(圖3)、冠冕等,都是由造辦處精心制作,不僅在材質(zhì)上選用最上等的絲綢、珍珠、寶石等,而且在工藝上也力求精細(xì),以彰顯皇權(quán)的尊貴。
3.皇家園林修繕及陳設(shè)制作
皇家園林的修繕及陳設(shè)也是造辦處的重要職責(zé)之一。在清朝,皇家園林的建造與維護(hù)是一項重要的文化與政治活動,這些園林不僅是皇室成員休閑的場所,也是展示國力與文化的重要平臺。如雍正帝時期的圓明園成為清代園林藝術(shù)的典范;乾隆年間的長春園、清漪園、靜宜園以及靜明園等園林建筑更是達(dá)到了頂峰。這些園林不僅規(guī)模龐大,而且設(shè)計和裝飾也體現(xiàn)了極高的藝術(shù)價值和審美理念。造辦處在這些園林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其精心制作的陳設(shè)品使園林更加雅致。
4.皇室陵寢器用制作
皇室的陵寢器用既是對先祖的敬仰和紀(jì)念,又是皇家權(quán)威的象征和傳承。陵寢器用的制作,涉及供奉器具、碑文刻制以及陵墓建設(shè)所需的各種物品。這些物品的制作同樣由造辦處負(fù)責(zé),皇室的陵寢器用不僅在材質(zhì)和工藝上追求極致,而且在設(shè)計上也體現(xiàn)了對先祖的尊敬和對傳統(tǒng)的繼承。陵寢的建造不僅是對逝者的紀(jì)念,也是對生者的教化,陵寢的莊嚴(yán)肅穆傳達(dá)了清朝對孝道的重視。
(二)為國事軍事需求服務(wù)
1.禮器制作
在清朝,禮器的制作與使用禁僭嚴(yán)格,特別體現(xiàn)在王公大臣的帽頂制式、帝王的冊封慶典以及國家祭祀活動中所使用的器物方面。這些典章禮器的制作通常由禮部聯(lián)合工部等相關(guān)機構(gòu),在獲得清宮內(nèi)務(wù)府的批準(zhǔn)后,與宮內(nèi)造辦處共同負(fù)責(zé)。其中的精細(xì)制作工序,各部門會交給造辦處負(fù)責(zé)。于是,禮部確定器物的樣式,造辦處提供精湛的工藝,工部負(fù)責(zé)基礎(chǔ)制作,共同完成清廷禮器的制作。
2.賞賜器物制作
賞賜是清朝重要的國事,帝王常以器物作為賞賜分發(fā)給宮廷內(nèi)外。在宮廷內(nèi)部,賞賜的數(shù)量相對較少,大量的賞賜用于邊疆地區(qū)、朝貢國家以及其他國家。雍正帝使用了大量造辦處的器物,來賞賜京城以外的各路將領(lǐng)。
3.武器裝備制作
自康熙朝起,造辦處便開始承接軍用兵器的制作。起初,武備院是兵器的主要制作機構(gòu),并時常與造辦處合作。到了清中期,武備院的制作重點轉(zhuǎn)向了冷兵器,造辦處開始承擔(dān)起更多熱兵器的制作,如鳥槍(圖4)和火炮等。從雍正時期開始,炮槍處歸屬于養(yǎng)心殿造辦處。
4.宗教法器制作
清朝的宗教信仰展現(xiàn)出極高的多元性,佛教、道教、薩滿教、基督教以及各種民間宗教在這個時代共存。其中,藏傳佛教在清朝得到了極大發(fā)展,統(tǒng)治者不僅在政策上給予支持,還在文化藝術(shù)上大力推廣。例如,乾隆九年(1744),清廷為了裝飾雍和宮以及制作宮廷內(nèi)的藏式法器,特意聘請了西藏的工匠。這些工匠不僅帶來了精湛的技藝,也將藏傳佛教的文化精髓融入宮廷藝術(shù)之中。
5.西方科技設(shè)備制作
在清宮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中,西方科技設(shè)備是一個新興項目,這主要得益于康熙帝對西方科學(xué)和藝術(shù)的濃厚興趣。在當(dāng)時,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技設(shè)備(圖5)成為造辦處的新任務(wù),包括對其進(jìn)行辨識、收藏、維修和仿制等。在雍正和乾隆時期,這一傳統(tǒng)得以延續(xù)。
《清宮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中有如下記載:
雍正五年十月十四日“太監(jiān)王太平交來樂鐘一件、大日晷一件,奉旨:著收拾,俟明年隨往圓明園陳設(shè)。欽此”。[1]
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郎中海望持出琺瑯西洋人物表一件、黑子兒皮套西洋人物表一件,奉旨:著對準(zhǔn)收拾。欽此”。[2]
雍正九年六月初一日“員外郎滿毗傳做備用賞用五十、六十、七十歲玻璃眼鏡,每樣五副,記此”。[3]
二、藝術(shù)效能——“技”與“藝”的集合
(一)工藝薈萃與技術(shù)發(fā)展
雍乾兩朝的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在技術(shù)發(fā)展上呈現(xiàn)出顯著的多樣化和綜合性特點。這一時期,造辦處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能工巧匠,包括漢族、少數(shù)民族以及西方的技藝能手,他們的技術(shù)與知識在造辦處相互交融,形成了獨特的御制工藝體系。這種技術(shù)的融合不僅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的多元文化,還反映了統(tǒng)治者對工藝技術(shù)的高度重視和開放態(tài)度。
首先,造辦處的技術(shù)來源多樣化為其工藝創(chuàng)新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各地工匠帶來的傳統(tǒng)技藝,如江南的織造技術(shù)、廣東的瓷器制作、西藏的金屬工藝等,都在造辦處得到了傳承和發(fā)展。同時,西方技藝的引入,如鐘表制作、玻璃工藝等,為造辦處的工藝技術(shù)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次,造辦處在技術(shù)層面的創(chuàng)新還體現(xiàn)在作坊的規(guī)模和數(shù)量上。在全盛時期,造辦處擁有超過四十個作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這些作坊不僅涵蓋了各種傳統(tǒng)工藝,如織造、瓷器、漆器、金銀器皿等,還包括西方技藝的制作,如鐘表、玻璃等。這種規(guī)模的工藝制造體系,不僅體現(xiàn)了清朝皇室對工藝品的極高要求,還展現(xiàn)了清朝強大的綜合國力。
再次,造辦處的技術(shù)發(fā)展還體現(xiàn)在其對技藝人員的培養(yǎng)和管理上。造辦處不僅吸引了眾多技藝高超的工匠,還經(jīng)過嚴(yán)格的選拔和培訓(xùn),培養(yǎng)了一批批優(yōu)秀的工藝人才。這些人才不僅保證了造辦處工藝技術(shù)的傳承和發(fā)展,還為清朝的工藝技術(shù)進(jìn)步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
最后,造辦處的技術(shù)發(fā)展還與其嚴(yán)格的質(zhì)量控制體系密切相關(guān)。清朝歷代君主對造辦處的工藝品要求極為嚴(yán)格,造辦處的工藝品,從設(shè)計到制作,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要經(jīng)過嚴(yán)格的審查和監(jiān)督,確保每一件工藝品都達(dá)到皇室的標(biāo)準(zhǔn)。這種對質(zhì)量的極致追求,不僅提升了造辦處工藝品的藝術(shù)價值,還推動了工藝技術(shù)不斷進(jìn)步和創(chuàng)新。
(二)審美追求與文化融合
在藝術(shù)審美方面,清宮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不僅遵循著宮廷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還積極吸收并融合民間及西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這種審美追求和文化融合,使得造辦處的工藝品具有獨特的“御制”身份,成為清朝文化的重要標(biāo)志。
首先,造辦處的審美追求體現(xiàn)在對工藝品的精細(xì)制作和藝術(shù)表現(xiàn)上。雍正和乾隆對造辦處的工藝品有著極高的要求,這種要求不僅體現(xiàn)在工藝品的實用性上,還體現(xiàn)在其藝術(shù)價值上。造辦處的工藝品,無論是金銀器皿、瓷器、漆器,還是織物、繪畫、雕刻等,都力求在造型、紋飾、色彩各方面達(dá)到極致的美感。這種對美的極致追求,使得造辦處的工藝品兼具實用價值和極高的審美價值。
其次,造辦處的藝術(shù)審美還體現(xiàn)在對民間藝術(shù)和西方藝術(shù)的吸收和融合上。清朝統(tǒng)治者在尚武的同時,也高度重視文化治國。因此,造辦處在遵循宮廷審美要求的同時,也積極吸收民間藝術(shù)的精華,如民間的剪紙、年畫、刺繡等,以及西方藝術(shù)的元素,如透視法、寫實主義等。這種文化的融合,讓造辦處的工藝品具有更加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再次,造辦處的審美追求還與其政治任務(wù)密切相關(guān)。造辦處的制器活動是藝術(shù)創(chuàng)作,也是國家政治任務(wù)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工藝品的制作和展示,雍正、乾隆兩位統(tǒng)治者展現(xiàn)了自己的文化品位和審美趣味,也借此傳達(dá)了統(tǒng)治階級的政治理念和文化政策。
最后,造辦處的藝術(shù)審美還體現(xiàn)在對技藝創(chuàng)新的鼓勵和支持上。雍乾二帝熱衷于親自參與制器活動,也為技藝的創(chuàng)新提供了條件。帝王的意志推動了傳統(tǒng)技藝的融合,這一過程雖然復(fù)雜且充滿變化,但無疑豐富了宮廷文化,也促進(jìn)了技藝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這種對創(chuàng)新的鼓勵和支持,使得造辦處的工藝品在藝術(shù)形式和表現(xiàn)手法上不斷突破和創(chuàng)新,成為清朝藝術(shù)寶庫中的璀璨明珠。
(齊魯工業(yè)大學(xué)山東省科學(xué)院、南京林業(yè)大學(xué)藝術(shù)設(shè)計學(xué)院)
參考文獻(xiàn)
[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xué)文物館.清宮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二冊(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52.
[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xué)文物館.清宮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三冊(上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44.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xué)文物館.清宮內(nèi)務(wù)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四冊(下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