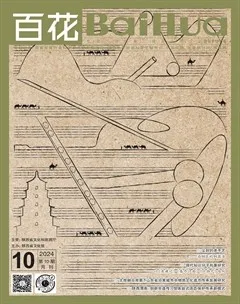從《毛詩傳箋通釋》引文看馬瑞辰的治學(xué)特色


摘 要:清代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廣泛吸收前人學(xué)術(shù)成果,引述典籍近四百部,反映了他廣博匯通、漢宋兼采、批判色彩濃郁、實事求是的治學(xué)特色以及通達、開闊的學(xué)術(shù)視野。時至今日,該書仍然是《詩經(jīng)》學(xué)研究的重要參考書。
關(guān)鍵詞:《毛詩傳箋通釋》;馬瑞辰;征引;治學(xué)特色
清代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以下簡稱《通釋》)是研究《詩經(jīng)》的名著,該書有五十余萬字,內(nèi)容充實,見解獨到,這與作者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善于廣泛征引前人的著作分不開。清代學(xué)者在治學(xué)過程中廣征博引的風(fēng)氣始于清初,《清史稿》載:“清興,崇宋學(xué)之性道,而以漢儒經(jīng)義實之。御纂諸經(jīng),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fēng)氣益精博矣。”[1]生于嘉道年間的馬瑞辰亦順應(yīng)了這種潮流,博采諸家之長,在研究《毛詩》的過程中廣泛借鑒前代和當(dāng)時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成果,并在征引的過程中細加揣摩,時下按語,融會貫通出一部自成體系的《詩經(jīng)》學(xué)大著,在清代經(jīng)學(xué)和《詩經(jīng)》學(xué)研究史上占據(jù)重要地位。馬瑞辰出身于文化底蘊深厚的桐城馬氏家族,崇德重學(xué)的家風(fēng)對其影響深刻。馬瑞辰的《通釋》反映出清代桐城文化崇德重道、崇學(xué)重教的內(nèi)在追求和價值取向,豁達開放、兼容并蓄的學(xué)術(shù)文化品格,以及始終與清代學(xué)術(shù)文化主潮融合發(fā)展的特色。下文將對《通釋》引書的情況進行詳細分析,立足于其征引情況的不同,總結(jié)馬瑞辰的治學(xué)特點和文化品格。
《通釋》征引了清及清以前近四百部書籍的研究成果,將其中所征引的書目全部析出,按照引書內(nèi)容的不同種類進行分類,可細分為十類:《毛詩》正文類,如《漢代熹平石經(jīng)》《唐石經(jīng)》《五代蜀石經(jīng)》;《詩經(jīng)》有關(guān)專著,如漢代鄭玄《毛詩箋》、魏晉南北朝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宋代歐陽修《詩本義》等;小學(xué)書類,如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唐代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宋代《廣韻》等;史地書類,如唐代梁載言《十道志》、令狐德棻《周書》等;群經(jīng)傳疏,如先秦的《尚書》《易》《論語》、唐代孔穎達《五經(jīng)正義》等;諸子類,如先秦《禽經(jīng)》、唐代楊倞《荀子注》等;類書,如唐代《北堂書抄》《藝文類聚》、宋代《類篇》等;治經(jīng)札記答問考訂書類,如清代姚范《援鶴堂筆記》、程瑤田《九谷考》等;集部別集及總集名注類,如東漢王逸注《楚辭章句》、南朝梁蕭統(tǒng)《文選》、清代朱彝尊《曝書亭集》;金石文,如春秋《和鐘銘》、秦代《石鼓文》、宋代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清代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馬瑞辰《通釋》的引書情況反映了他的治學(xué)特點,下文將詳細論述。
一、廣博匯通
馬瑞辰深受清代漢學(xué)文化思想的影響,又繼承了父親馬宗璉的漢學(xué)事業(yè),成為清代研治《詩經(jīng)》的三大家之一,所著《通釋》代表了清代《詩經(jīng)》學(xué)研究的最高成就。《通釋》的引書不僅遍及經(jīng)、史、子、集,而且涉及字書、類書、緯書等。
(1)淹通群經(jīng)。馬瑞辰治《毛詩》,不僅僅囿于其相關(guān)典籍、文獻,還對《三禮》《左傳》等其他經(jīng)書了然于胸,對經(jīng)書中引用的《詩經(jīng)》語句,常常信手拈來,隨時征引。馬瑞辰對后人經(jīng)學(xué)研究的著作,凡是能作為考據(jù)的證據(jù)或者為之補充解釋的,皆能得心應(yīng)手地引入《通釋》中。馬氏大量引用《三禮》經(jīng)、注中的有關(guān)材料來考證《毛詩》中所涉及的典章制度、語言文字,顯示出了一定的《禮》學(xué)功底。正是因為馬氏能貫通群經(jīng),所以他在研究《詩經(jīng)》的過程中,常常能對他經(jīng)隨事征引。
(2)匯通經(jīng)子。《通釋》廣泛征引諸子之書,引用最多的前幾位分別是《呂氏春秋》123次、《荀子》102次、《淮南子》80次、《莊子》51次、《管子》41次、《列子》24次。馬氏治經(jīng)能融通經(jīng)子,善于將子書作為疏解經(jīng)注的論據(jù)。
(3)貫通經(jīng)史。《通釋》也廣泛征引《戰(zhàn)國策》《國語》《史記》《漢書》《后漢書》《魏書》《晉書》《宋史》等史書。史籍的時間跨度從先秦至清代,種類達到69種,特別是對《漢書》《史記》的征引次數(shù)最多,均超過200次,足以表明馬瑞辰治學(xué)重視史料,貫通經(jīng)史。
(4)融古通今。《通釋》引書不避古今,時間跨度長。作為一名經(jīng)學(xué)家,馬氏融古通今不僅體現(xiàn)在大量利用先秦至清代的文獻材料,對《詩經(jīng)》文本進行專門研究,對古往今來《詩經(jīng)》學(xué)的各類相關(guān)理論問題、各種聚訟紛紜的爭論焦點進行研究和響應(yīng)上,還體現(xiàn)在這部著作的引書涉及從古至今包括名物、歷史、地理、禮制等諸多內(nèi)容上,可見其對各種經(jīng)學(xué)研究的著作都非常熟悉。
馬瑞辰論證《詩經(jīng)·豳風(fēng)·東山》中周公東征這一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地點時,舉了七個證據(jù)論證周公東征之地以奄地為主。引用書籍包括了歷史類《逸周書》《左傳》《補后漢書》,地理類《括地志》,群經(jīng)傳疏類《孟子》《尚書大傳》《四書釋地》,小學(xué)類《說文解字》《爾雅》,類書《皇覽》,諸子類《琴操》等典籍。[2]引書不僅數(shù)目多,且涉及多種門類,反映了其舉證引書遍涉經(jīng)、史、子、類書、字書,博古通今的特點,顯示出馬瑞辰頗為扎實的考據(jù)學(xué)功底。
二、漢宋兼采
明清兩代,桐城文化風(fēng)氣濃郁,理學(xué)興盛,文學(xué)繁茂,學(xué)人以學(xué)問道德相標榜,以文學(xué)行誼相砥礪,馬氏家族亦受此文化精神熏陶。桐城文化風(fēng)氣的主潮是對宋以來理學(xué)的傳承,學(xué)者們皆宗義理之學(xué)而少有純粹的考據(jù)學(xué)家,馬瑞辰顯然與里中學(xué)派不同,這正凸顯了桐城學(xué)術(shù)文化兼容并蓄、開放豁達的品質(zhì)。馬氏引書還反映了其治學(xué)的一個特色,即不據(jù)守門戶之見,漢宋兼采。馬瑞辰治《詩》能較為客觀地對待宋學(xué),征引了大量宋人的著述,合計55種。《通釋》引用朱熹學(xué)術(shù)觀點達89處,其中提出批駁的有19處,筆者按照征引內(nèi)容的不同將所引觀點進行分類,詳見表1。
馬氏征引朱熹的觀點有49處屬于文字訓(xùn)詁方面、4處史地方面、4處名物方面、1處禮制方面,四類合計占引用朱熹學(xué)術(shù)觀點總數(shù)的65%。馬氏《通釋》對朱熹詩義觀點的征引有31處(包括批評的10處),這在馬氏對朱熹觀點的征引中占比35%。首先,朱熹作為理學(xué)大家,解說思想義理是其長處,自然在通解詩義方面有更深刻、更細致、更獨到的發(fā)現(xiàn),這對馬瑞辰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馬氏解《詩》雖然以訓(xùn)詁考證為絕對核心,是漢學(xué)的研究方式,但他并不完全忽略對詩義的解讀,他常常不經(jīng)意地由詩句生發(fā)對國家、社會、人生的思考,亦有文學(xué)性的闡釋,顯示出其對詩歌義理思想的關(guān)注。其次,在清初以來形成的排斥宋學(xué)的社會思潮中,馬瑞辰能夠獨立自持,對朱熹以及其他宋代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成果進行仔細研究,在意見相左時又提出批評,這都體現(xiàn)出馬瑞辰治學(xué)沒有門戶之見,以漢學(xué)為主,兼采宋學(xué),切實做到了漢宋兼容、客觀求實。
三、批判色彩
馬瑞辰的學(xué)術(shù)研究具有較為濃厚的批判色彩,這和清代漢學(xué)家是很不相同的。漢學(xué)家最主張“實事求是”,但對這一理念的貫徹執(zhí)行往往不徹底。他們在對某一具體問題進行考據(jù)學(xué)研究時充滿刨根問底的熱情,但對自己所宗奉的某家某派學(xué)說完全沒有鑒別、批判能力。馬瑞辰對今古文《詩》學(xué)和鄭《箋》、孔《疏》,乃至宋儒《詩》學(xué)及同時代學(xué)者的見解,都不絕對予以肯定或否定,這從其對引文的處理上即可看出。比如,馬瑞辰在引用段玉裁、戴震、高郵“二王”等乾嘉大學(xué)者的學(xué)術(shù)成果時,能指出他們的謬誤,提出不同的見解。馬氏引用段玉裁學(xué)術(shù)成果的222處觀點中,有66處屬于批評,占總數(shù)的30%。馬瑞辰對段玉裁這位乾嘉大儒的批評相當(dāng)不留情面,雖然偶爾使用批評語氣稍微緩和的“說亦未確”[3]“非通論也”[4]這樣的字眼,但大多數(shù)情況下使用“失之”“非也”“誤矣”這樣比較直接的批評字眼進行評價,有時甚至使用“臆說”[5]“妄”[6]這樣語氣激烈的批駁性語言。馬氏對段玉裁提出批駁的66處觀點,實質(zhì)上反映出二人學(xué)術(shù)觀點的不同。如以下馬氏對《詩》文的訓(xùn)解: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瑞辰按:《說文》,“,艸旱盡也。”引《詩》“山川”,蓋本三家《詩》。從俶聲,俶從叔聲,叔與少長之少、多少之少皆雙聲而義同,故有艸旱盡之象。《說文》:“,無人聲。”“,禿。”凡從叔聲者,皆有無義,與之訓(xùn)艸旱盡者義正相近。毛《詩》作滌滌者,同部假借字也。段玉裁以《說文》作為誤字,其說非也。(《詩經(jīng)·大雅·云漢》)[7]
段玉裁認為《說文》所引《詩》“山川”中的“”為誤字,而馬瑞辰則認為“”乃“滌”的同部假借字。馬瑞辰對段氏的批駁很大一部分類似于此例,段玉裁常常做誤字的判斷,馬氏則認為是假借字,因而馬瑞辰直言不諱地批評道:“段氏輒疑為誤矣!”[8]在某些特殊的語言環(huán)境中,對字形不同的兩個字,段玉裁判斷為誤字,馬瑞辰則斷為同部或雙聲假借字,批評段氏“昧古文假借之恉”[9]。此外,馬氏對戴震的批評數(shù)占到征引總數(shù)的一半;征引惠棟觀點的28處中,有16處屬于批評,遠超贊成數(shù)。戴震和惠棟是乾嘉漢學(xué)界的兩大領(lǐng)軍人物,馬氏對他們觀點進行批評的數(shù)量之多令人驚訝。
四、實事求是
《通釋》引書具有求實性,反映了馬瑞辰治學(xué)實事求是的精神。實事求是是清代漢學(xué)家一貫追求的治學(xué)宗旨,梁啟超說:“本朝學(xué)者以實事求是為學(xué)鵠,頗饒有科學(xué)的精神,而更輔以分業(yè)的組織,惜乎其用不廣,而僅寄諸瑣瑣之考據(jù)。所謂科學(xué)的精神何也?善懷疑,善詢問,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說、一己之臆見,而必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既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wù)盡其條理,而備其佐證,二也;其學(xué)之發(fā)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發(fā)明者,啟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啟者爾競其業(yè),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shù)之異說,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凡此諸端,皆近世各種科學(xué)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漢學(xué)家皆備之,故曰精神近于科學(xué),……夫本朝考據(jù)學(xué)之支離破碎,汩沒性靈,此吾儕十年來所排斥不遺余力者也。雖然,平心而論,其研究之方法,實有不能不指為學(xué)界進化之一征兆者。”[10]梁氏論清代考據(jù)學(xué)盡管還有不夠客觀之處,但其“本朝學(xué)者以實事求是為學(xué)鵠,頗饒有科學(xué)的精神”“凡此諸端,皆近世各種科學(xué)所以成立之由,而本朝之漢學(xué)家皆備之,故曰精神近于科學(xué)”的論述還是比較公允的。馬瑞辰疏解《詩經(jīng)》,正體現(xiàn)了梁啟超所說的“善懷疑,善詢問,不肯妄徇古人之成說、一己之臆見”的科學(xué)求實之精神。他申明著書以“折衷于至當(dāng)”為目標,“實事求是,祇期三復(fù)乎斯言”[11],也很好地實踐了他在《通釋》的《自序》和《例言》中一再強調(diào)的“實事求是”的治學(xué)理想。
五、結(jié) 語
綜上所述,馬瑞辰的《通釋》廣泛吸收前人尤其是清人的學(xué)術(shù)成果,引述典籍近四百部。從引書情況可見馬瑞辰通達、開闊的學(xué)術(shù)文化視野,馬氏不拘門戶的治學(xué)追求和帶有批判色彩的學(xué)術(shù)研究都足以使這部著作以鮮明的學(xué)術(shù)風(fēng)格名載史冊。
(安徽工業(yè)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
項目基金:安徽省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規(guī)劃一般項目“皖籍經(jīng)學(xué)家馬瑞辰與胡承珙《詩經(jīng)》學(xué)比較研究”(AHSKY2019D120)。
參考文獻
[1] 趙爾巽.清史稿:第43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7:13099.
[2]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9:474-478.
[3] 同[2]:299.
[4] 同[2]:480.
[5] 同[2]:120.
[6] 同[2]:1184.
[7] 同[2]:982.
[8] 同[2]:481.
[9] 同[2]:647.
[10]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一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87.
[11] 同[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