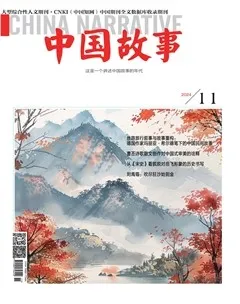審視《文心雕龍》對曹操詩歌的評鑒
【導讀】曹操作為建安文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上呈“漢音”,下啟“魏響”,對魏晉樂府詩歌向文人詩的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曹操詩歌的評價存在一些偏頗。原因主要在于曹操詩歌的內容和詩風,與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和時代風氣有著顯著差異。
《文心雕龍》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文學理論巨著,對中國古代文學發展與研究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文心雕龍》不僅系統論述了先秦以來文學創作體式、手法與經驗,更對歷代重要文學家及其作品進行了精辟評論。曹操作為建安文學的重要領軍人物,上呈“漢音”,下啟“魏響”,對魏晉樂府詩歌向文人詩的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中國古代詩壇的杰出代表之一。但劉勰對曹操詩歌的關注度并不高,其對曹詩的論述也存在偏頗。本文旨在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探析曹操詩歌的藝術風格,解析《文心雕龍》評鑒曹操詩歌的得與失,以期為曹操詩歌研究注入新活力。
一、對曹操詩歌的論述
目前,已有大量學者就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曹操的評述進行研究,如胡輝、董軍的《〈文心雕龍〉視閾下的曹操研究》,蔣凡的《〈文心雕龍〉建安三曹論評議》,高崎的《劉勰〈文心雕龍〉論“三曹”詩》等,但現存研究多集中于文學批評或“三曹”對比評析,就曹操詩歌進行研究的成果仍然有限。
《文心雕龍》全書論及曹操的片段共有十處,內容包括家世背景、人品修養、文論思想、文學表現等。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曹操詩歌的論述卻僅有《樂府》篇一處,在詩歌總論《明詩》篇中更是全然不見曹操的蹤影。對此,蔣凡、劉智禹兩位學者認為劉勰的視域太過局限,未能看到曹操詩歌的卓越之處。誠然,劉勰對曹操的詩歌并不十分推崇,但一些認為其完全無視曹操詩歌的論斷也是有失公允的。在曹操66年的人生中,所作詩文不少,但由于無系統性的文獻記錄,加之常年征戰導致大量作品遺失,今可考證的曹操詩歌僅存22首,且均為樂府詩歌。劉勰應該在此考量下,選擇將曹操的詩歌置于《樂府》篇來評述,但不可否認,他的觀點存在一些偏頗之處。
《樂府》篇記載:“至于魏之三祖,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眾引,《秋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于淫蕩,辭不離于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在劉勰看來,曹魏三祖的樂府詩歌并非無可取之處,他夸贊其作品氣質爽朗,文才富麗,音調柔靡,節奏平和。不過,“宰割辭調”這一論述向來存在爭議。范文瀾先生根據《宋書·樂志》中“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的記載,認為劉勰“宰割辭調”的評述實際是帶有批判意味,而陸侃如、牟世金兩位先生則認為這是一種褒獎。
本文認同后一種觀點,原因如下:觀《文心雕龍》開篇三章可知,劉勰的創作理論以儒家思想為先導,他對先秦時期中正平和的雅樂格外推崇。然而,由于禮崩樂壞,雅樂逐漸衰微,漢朝雖然也沿襲舊樂并設立樂府,但在劉勰看來,這時的樂已經變成了淫靡之樂。即使是郊廟祭祀之樂,也是“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可以說劉勰對漢舊樂的評價并不高。基于這種觀點,“宰割辭調”也就僅僅是一個不帶情感導向的客觀陳述而已。另外,在一個完整的、前后均為肯定語句的評述中,貿然插入批判觀點也不符合言語邏輯。故而可以說,對于曹魏三祖的詩歌,劉勰實際上還是肯定的。
不過,之后的論述則明顯帶有鄙棄色彩:“志不出于淫蕩,辭不離于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劉勰將曹操的詩歌歸類為不同于《韶》《大夏》等雅樂的鄭曲。為儒家摒棄的鄭衛之音,向來被認為是不符合中正平和之理的靡靡之音。“三調之正聲”明確肯定了曹詩的音樂形式,那么“志不出于淫蕩,辭不離于哀思”就是指向詩歌的內容和情感。劉勰認為上品詩應當體現孔子所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特性,但曹詩悲涼雄壯的藝術風格和詩中的戰亂慘象,帶有強烈的情感色彩。被劉勰批評的“淫蕩”“哀思”,事實上正是曹操內心情感的真實再現。所以,“志不出于淫蕩,辭不離于哀思”這個以儒家教化為出發點的評論,在今天看來過于片面,并不完全可取。
二、曹操詩歌的新變
縱觀歷史,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向來附著于大一統的政權格局。但東漢末年,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的局面讓經學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也使之無法再與現實政治的需求相匹配。上層建筑的崩塌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在政治、經濟、文化百廢待興之際,文學變革自然應運而生,曹操的詩歌就是這個特定時代下的產物。據統計,曹操現存的22首樂府詩歌,內容多為行軍和政治抒懷,但他的詩最為突出的特點是擅以樂府“舊題”寫“時事”,從而開創了文人“擬樂府”詩歌創作的新局面。曹操為何熱衷于樂府詩歌卻又以舊題寫時事?這其中有兩個重要原因:
其一,曹操好樂。《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說曹操“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宋書·樂志》亦載:“《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由此可以推斷,和樂而唱的樂府詩歌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然成為曹操的第一選擇。魏晉時期有兩種擬樂府的創作方式:一是擬調(曲調旋律為主),二是擬篇(體式內容為主)。曹操的樂府詩多為擬調而作的相和歌,如《陌上桑》《步出夏門行》《短歌行》等,相較于古題,這些作品的主旨和內容明顯已被作者更改,用以述志抒情了。當曹操東臨碣石而觀滄海之際,他的創作或許并不僅限于文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或許在那一刻,浮現于這位亂世梟雄腦海之中的,是一曲澎湃壯闊的激昂樂歌。如此,歌樂相襯而生的《觀滄海》才能將曹操獨有的壯懷激烈展現得淋漓盡致。
其二,這與曹操所處的特殊時代背景和人生經歷有關。鐘嶸《詩品》言:“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宋人敖陶孫也說“魏武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因此不少人常用“悲涼沉雄”來評價曹操詩歌的藝術風格。東漢末年董卓亂政,群雄逐鹿,征戰四起,曹操的大部分詩歌創作就是開始于這個時期,其中《薤露行》《蒿里行》都是反映董卓之亂的代表作。《薤露行》和《蒿里行》均屬樂府挽歌,原為出殯時挽柩者所唱,但曹操卻用它們寫時事,可謂另辟蹊徑。公元190年,曹操、袁紹、韓馥、劉岱等人合力起兵討伐董卓,然而群雄各懷異心、躊躇不前,袁紹欲謀廢立之心昭然若揭,曹操于極度悲憤之際寫下了《薤露行》:“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蒿里行》:“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大廈將傾,基業欲亡,“白骨”“蟣虱”這樣極具沖擊力的詞語更是將戰亂紛爭下,百姓之生死慘狀描述得淋漓盡致。由此可見,曹操的樂府詩以舊題寫時事,視域更為廣闊,他放眼天下蒼生,悲宗廟傾覆、生靈涂炭,已然超越了原題情感邊界,并將其上升到新的高度,所以用“悲涼沉雄”來概括曹操的詩歌風格無疑是準確的。
另外兩首《苦寒行》《卻東西門行》寫行役之苦。《卻東西門行》以“鴻雁出塞北”起興,鴻雁是候鳥,有居無定所之意,“塞北”“無人鄉”又烘托了全詩孤寂寥落的氛圍。值得一提的是結尾處的“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兩句,詩人一反孤凄哀傷的基調,而改用“神龍”“猛獸”作比,在悲涼之余反而生出一股剛健壯烈之氣。《苦寒行》中“悲彼《東山》詩,悠悠令我哀”兩句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表面來看詩句表達的是作者對士卒行役之苦的深切憫傷之情,但《東山》詩是周公平亂勝利后士卒返回故園所作,因而曹操在此想要表達的并非只有簡單的思古之幽,更多的還有他渴望統帥三軍安定天下,以使士卒“勿士行枚”的悠悠壯思。悲而不凄是曹操詩歌的一大特點,雖然上文論述的作品多寫于特定的歷史事件①,但在悲愴低迷的情感背后是曹操本人欲圖大業、老驥伏櫪的慷慨志向。后人觀之,也得以體會那個磅礴厚重時代下所特有的悲壯之氣。綜上所述,以“志不出于淫蕩,辭不離于哀思”來評述曹操的詩歌其實并不可取。
詩歌鑒賞向來秉承“知人論世”的原則。曹操作為一個擁有多重身份角色的復雜個體,他的生平經歷并非常人能夠想象,其思想高度也遠非一般文人所能望其項背。《文心雕龍》在文學評論領域的重要價值毋庸置疑,但它并不是絕對權威。劉勰以原道、征圣、宗經的儒家政教思想作為創作導向,顯然與曹操輕禮教、重刑名、唯才是舉的思想內核相悖,故而劉勰無法理解亂世風云下曹操詩歌特有的那份慷慨壯氣和超越時空的深刻現實意義。
除此以外,曹詩古直,簡約質實且不尚藻飾,而劉勰雖也極力反對南朝時期文學創作的浮華夸飾之風,但受時代風氣影響,他亦主張追求文學作品的藝術審美性。因此,曹操詩歌便也不可避免地被冠上了“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的評價。客觀而論,三曹詩歌中曹丕、曹植的作品更為劉勰所肯定。曹丕文采清麗,曹植詞采華茂,鐘嶸在《詩品》中也將曹植詩列為上品,而曹操在詩歌煉字造境方面相較于其子來說的確并不突出,想必這也是劉勰更為推崇贊賞曹氏兄弟的詩歌而忽略曹操詩歌的重要原因之一。
總體來看,盡管《文心雕龍》對曹操詩歌的論述過于片面保守,但不可否認的是,相較于后世一些帶有極度強烈的主觀情感,一味拔高或貶抑某些作家作品的評述,劉勰還是能夠站在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以動態的視野盡可能理性公正、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也正因如此,《文心雕龍》才能經得住歷史和現實的考驗,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注釋
① 《蒿里行》《薤露行》寫于董卓亂政,《苦寒行》寫于北征高干,《卻東西門行》寫于赤壁之戰后。
參考文獻
[1] 王運熙,周鋒. 文心雕龍譯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 曹操. 曹操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59.
[3] 陳慶元. 三曹詩評選[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4] 上海辭書出版社文學鑒賞辭典編纂中心. 三曹詩文鑒賞辭典[M]. 上海:辭書出版社,2020.
[5] 陳壽. 三國志[M]. 北京:中華書局,2022.
[6] 郭茂倩. 樂府詩集[M]. 北京:中國紡織出版社,2019.
[7] 郭預衡. 中國古代文學史[M].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8] 羅宗強.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M]. 北京:中華書局,2019.
[9] 吳大順. 曹操“擬樂府”與建安風骨的發生[J]. 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2).
[10] 劉曉莉. 曹操詩歌對漢樂府敘事題材的突破[J]. 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S2).
[11] 傅剛. 論曹操的樂府詩寫作[J]. 銅仁學院學報,2014(3).
[12] 蔣凡.《文心雕龍》建安三曹論評議[J]. 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16(1).
[13] 劉智禹. 劉勰的曹操詩歌創作論[J]. 淮南師范學院學報,2014(5).
[14] 胡輝,董軍.《文心雕龍》視閾下的曹操研究[J]. 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14(1).
[15] 木齋. 論曹操詩歌在五言詩形成中的地位[J]. 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2).
[16] 陸侃如,牟世金. 文心雕龍譯注(上)[M]. 濟南:齊魯書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