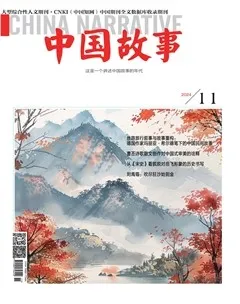探析蘇軾的九日詩
【導讀】蘇軾在眾多歲時節令中特愛重九,即重陽節,寫下了多篇九日詩。蘇軾的九日詩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與親人、友人的寄贈詩,另一類是“和陶詩”。與親友的寄贈詩展現了蘇軾與親友的良好關系和他的重情形象。在貶謫期間所寫的“和陶詩”則展現了蘇軾在極致困境下,對自我心靈的探尋。最終他以堅韌的精神和超脫的態度,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找到了心靈的安寧。
一、重陽節與宋前九日詩的發展
重陽,又稱重九,時間在每年的農歷九月初九,是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節日。重陽節大致起源于東漢中后期至魏晉之間,當時還只是一個聚會宴飲、戶外娛樂的節日,并無后來的佩茱萸、賞菊花、登高、敬老等習俗。與九月九同時興起的還有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等重數節日,以“重陽”命名九月九最早可考于南北朝時期梁朝庾肩吾的《九日侍宴樂游苑應令詩》,從其中“獻壽重陽節,回鑾上苑中”一句可知,當時重陽節已有與“長壽”相聯系的文化傾向。。
關于重陽節的詩又稱“九日詩”,最開始是集會上的公宴詩,如庾肩吾的作品,也有私下作詩的。南北朝時期最為出名的當屬陶淵明的《九日閑居》,詩中描寫的是詩人罷官后閑居在家,抒發空對盛開的秋菊卻無酒可喝的感慨,涉及了飲酒、餐菊、祈禱長壽等習俗。及至唐代,重陽節因為濃厚的道教色彩,以及有長壽之意得到了官方推重,許多公開場合的重陽節應制詩留了下來。當然唐代最出名的九日詩,應當還屬王維十七歲離家,在長安科考期間所作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可見登高、佩茱萸這樣的習俗在唐代就有了,王維這首詩的影響非常大,此前九日詩的內容涉及祈禱長壽、佩茱萸消災、飲菊花酒、登高,等等,主題上與思親友的牽絆不是特別深,王維作此詩后,九日詩又多了一份思親友的內涵。
值得一提的是,此時九日詩與陶淵明還不見有什么很強的關聯,只有仕途較為失意的人會在九日詩中提到陶淵明,如被流放湖北三年的崔國輔的《九日》中寫道:“江邊楓落菊花黃,少長登高一望鄉。九日陶家雖載酒,三年楚客已沾裳。”隨著陶淵明在唐宋時期逐漸被發現和接受,九日詩與陶淵明的關聯也逐漸加深。
二、思親念友:蘇軾九日詩的情感表達
蘇軾留下的詩作眾多,其中吟詠各種時節的不在少數,如新年、上巳、端午、中秋等。在宋人蒲積中所編《古今歲時雜詠》中,幾乎每一個時節都能看到蘇軾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屬于所謂的應制詩,但有相當一部分屬于私下作品。蘇軾對于“重陽節”十分關注,寫過約三十首“九日詩”,并且幾乎都不是公開場合的應制之作。從內容來看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親人、友人的寄贈詩,與親情友情相關,體現了蘇軾與現實世界的聯系;另一類是“和陶詩”,體現了蘇軾對自我的探尋。
蘇軾較早期的九日詩有《捕蝗至浮云嶺山行疲苶有懷子由弟》,此詩作于熙寧七年(1074年),蘇軾二十七歲,重陽節他在治理蝗災的路上想起了弟弟子由,但“憶弟難憑犬附書”。另一首是作于元豐元年(1078年)的《次韻張十七九日贈子由》:“千戈萬槊擁篦籬,九日清樽豈復持。(是日南都敕使按兵。)官事無窮何日了,菊花有信不吾欺。逍遙瓊館真堪羨,取次塵纓未可縻。迨此暇時須痛飲,他年長劍拄君頤。”可能是黨爭傾軋使蘇軾感到疲憊,這首九日詩在表現九日常見的主題賞菊、飲酒之外,也流露出了對官場的厭倦。張十七即張恕,他的原詩已不可見,不過蘇轍的詩留了下來,《次韻張恕九日寄子瞻》:“茱萸插遍知人少,談笑須公一解頤。”蘇轍用了王維詩的典故,展現了兄弟間的真摯感情。次年蘇軾經歷烏臺詩案,獄中寫下“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此后人生浮沉幾十年,蘇軾與蘇轍一直互相扶持。
紹圣三年(1096年)的重陽節,蘇軾被貶惠州,蘇轍也被貶筠州,蘇軾在《次韻子由所居六詠其二》中寄托了對過去的懷念:“詩人故多感,花發憶兩京。石榴有正色,玉樹真虛名。粲粲秋菊花,卓為霜中英。萸盤照重九,纈蕊兩鮮明。”五十九歲的蘇軾在重九菊花開的時節,又想起了尚在京都時那段風華正茂的時光,那如花一般絢麗的歲月最終也如花一般消逝,幸而兄弟之間的真心一直未曾改變。
蘇軾的九日詩寄贈對象出現次數最多的是他的摯友“琢玉郎”王鞏,這是因為蘇軾在徐州為官時期曾與王鞏定下了重陽之約,卻一直未能如愿,他寫下大量九日詩,從熙寧十年(1077年)《王鞏屢約重九見訪,既而不至,以詩送將官梁交且見寄,次韻答之。交頗文雅,不類武人,家有侍者,甚惠麗》到元豐元年(1078年)《次韻答王定國》“愿君不廢重九約”催促友人快來看望自己,《次韻王定國馬上見寄》:“但恨不攜桃葉女,尚能來趁菊花時。”又再次催促友人快來,趁菊花尚在盛開。終于到《九日次韻王鞏》有了來之不易的見面,勸對方“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而《次韻王鞏留別》則是已到離別之時。
王鞏為人剛直,曾接連兩次因牽連他事被追官勒停,而蘇軾與新黨不和,自請離朝外任,兩人皆是失意之時。九日詩寫失意的傳統自陶淵明始,《九日閑居》詩序曰:“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蘇軾的九日詩繼承了陶淵明的失意,如《九日次韻王鞏》:“我醉欲眠君罷休,已教從事到青州。鬢霜饒我三千丈,詩律輸君一百籌。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同在重陽之日飲酒賞菊,同樣的醉眼朦朧,失意也與君同,及第之時的榮光已恍若隔世,去國八年只余身影寥落與危機四伏,幸得友人不遠千里而來,重陽九日得以相會。
元豐二年(1079年),烏臺詩案發生,蘇軾下獄,九死一生,王鞏受牽連被貶去賓州,這對王鞏來說是一次非常大的打擊,出身名門受家族庇護的王鞏,在以往的政治打擊中,最多是被罷官,從未遭受如此嚴厲的處罰。蘇軾在《王定國詩集敘》中說:“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蘇軾心中有很深的愧疚感,以至于“不敢以書相聞”,但王鞏主動聯系了尚在貶謫地的蘇軾。
元豐八年(1085年)舊黨上臺,蘇軾被重新起用,但不久因為批評舊黨的過激行為,蘇軾同樣不見容于舊黨,再次外任,在揚州任上時的重陽節,蘇軾又寫了一首《九日次定國韻》:“朝菌無晦朔,蟪蛄疑春秋。南柯已一世,我眠未轉頭。”十幾年倏忽而過,王鞏氣節不改,依舊是從前的王鞏,蘇軾歷盡千帆,依然是當初的蘇軾,如同多年之前,這一個相逢的重陽日。
三、以陶鑒己:蘇軾九日詩的自我探尋
蘇軾九日詩中,《和陶貧士七首》《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和陶九日閑居》屬于“和陶詩”。和陶詩是蘇軾晚年所創造的一種特殊形式,在和陶詩之前有眾多的擬陶、效陶之作,但與“追和古人”這種形式還是有著根本的區別。雖然唐代已零星出現追和古人詩的現象,但并沒有和韻,也不成規模。蘇軾和陶詩的創作始于元祐七年(1092年),這一年蘇軾五十五歲,在揚州任上,閑居寡歡,連夕飲酒,作《和陶飲酒二十首》。他再度提筆寫和陶詩已是三年之后,紹圣二年(1095年)他在惠州出游時看到荔枝樹,有一老人邀請他等荔枝成熟時攜酒來游。回家后聽見兒子蘇過誦讀《歸園田居》,于是提筆和之,接下來的幾年貶謫生涯里,他幾乎遍和陶詩,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他離開儋州,和陶詩的創作才結束。
《和陶貧士七首》作于紹圣二年(1095年),自從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執政,新黨再度登臺,蘇軾又開始了貶謫之途。蘇軾初到惠州時,知州詹范照顧他住到合江樓中,但十幾天后又遷居到偏僻的嘉祐寺。“余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伊邇,樽俎蕭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蘇軾寫下了《和陶貧士七首》。陶淵明原詩《詠貧士七首》,第一首寫自己高潔品性,第二首敘自己的貧困之狀和不平懷抱,從“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以下五首開始分詠歷代貧士行跡,最后以“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表達自己的志向。
蘇軾在重九佳節,同樣感嘆于自己的貧窮:“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陽,徂歲慘將寒。無衣粟我膚,無酒嚬我顏。”缺衣少食的生活使蘇軾感到沮喪,但幸好還有門生與兒子的追隨,雖然貧窮,但能留給他們的是安心,從中我們可見蘇軾以陶鑒己,進行自我探尋后在人生的困境里實現了精神上的超脫。同年十月,蘇軾作《和陶己酉歲九月九日》,菊花盛開之際,他想到了因飲菊水而長生的胡廣。范曄《后漢書·李固傳》認為同高風亮節的李固相比,小人品行的胡廣如糞土一般。蘇軾也贊同范曄這個觀點,品性不正之人,即便長壽又如何,連帶對傳說能治病的菊水發出“飲此亦何益”的感嘆,不如“持我萬家春,一酬五柳陶”。飲一杯嶺南所釀的“萬家春”酒,可與心中偶像陶淵明達到精神共鳴。
紹圣三年(1096年),蘇軾以為自己會在惠州了此余生,于是開始建白鶴峰新居,新居未成,七月時伴侶朝云去世,葬于西湖邊,九月蘇軾寫《丙子重九二首》,發出“西湖不欲往,暮樹號寒鴉”的感嘆,故人的接連離去,對蘇軾是不小的打擊,《丙子重九》第二首寫與客買魚放生之事,已心生歸耘田園之意。誰知次年朝廷重貶元祐黨人,蘇軾被貶至海南島,最初蘇軾極其不適應,新的昌化軍使張中到任后,對蘇軾禮遇非常,加以照顧,之后蘇軾漸漸適應了海島生活,《和陶九日閑居》體現了這一年重九時蘇軾的心境,雖然已被貶至絕境,反而心境愈加平和豁達,“九日獨何日,欣然愜平生。”“登高望云海,醉覺三山傾。”蘇軾此生已經度過了許多個重陽節,有身居高位、高朋滿座之時的,也有因事獲罪、擔憂難安之時的。如今登高望遠、賞菊飲酒等活動與以往似乎并無分別,但他很高興。嶺海時期的蘇軾已將一生風浪閱盡,以陶為友,完成了對自己內心的探尋。雖然現實不夠圓滿,但他找到了自己內心的圓滿。
參考文獻
[1] (晉)陶潛. 陶淵明集[M].龔斌,校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 (宋)蘇軾. 蘇東坡全集[M]. 張志烈,校注. 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
[3] 張強. 從“和陶詩”看蘇軾的心態變化與審美追求[J].社會科學戰線,2012(10).
[4] 郭佳. 九月九日重陽節探源[J]. 文化遺產,2017(5).
[5] 姜俵容. 蘇軾“和陶詩”的形式特征及其文體史意義[J]. 中國文學研究,2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