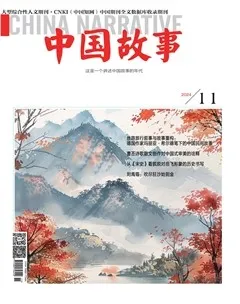左宗棠治疆政策及其對邊疆的貢獻
【導讀】1878年,左宗棠收復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南北兩路后,對新疆進行了一次頗具規模的改造與開發。左宗棠的治疆政策有力地捍衛了祖國統一與領土完整,鞏固了新疆局面,發展了新疆的經濟與文教事業,對后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在左宗棠成功收復新疆之后,針對該地區的善后處理與重建工作,成為了研究左宗棠及新疆不可或缺的重要議題。對左宗棠的研究多為專題性研究。包爾漢和紀大椿指出左宗棠推動新疆建省,有效維護西北邊陲。洪濤和馬振舉認為左宗棠收復新疆后,通過設置善后局、改善新疆經濟結構,有效恢復與改善了新疆經濟。汪長柱和孫占元則指出左宗棠發展新疆文教事業有效維護了清代大一統格局。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綜合探析左宗棠治疆政策。
一、左宗棠收復新疆
1865年,浩罕國阿古柏入侵新疆,先后占領了喀什噶爾、疏勒、和闐、葉爾羌等地,通過出賣清朝的國家和民族利益,與英、俄兩大列強勾結,控制了新疆大部分地區。1870年,沙俄強占伊犁,并向東推進。
新疆日益緊張的局勢亟需清廷化解。1866年,左宗棠任陜甘總督之時就積極謀劃新疆的反侵略斗爭。但此時清廷財政窘迫,無法為邊疆防務提供充足的經濟支持,遂出現“海防”與“塞防”的爭論。基于此,左宗棠提出:“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決不能扶起東邊倒卻西邊。”針對李鴻章等提出的收復新疆僅僅是“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的謬論,左宗棠給予堅決駁斥。
1875年,清廷任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面對清廷窘迫的財政狀況,為收復新疆,左宗棠在獲得清廷同意后,向外商借款。1875年到1877年,總共獲得兩千六百七十萬兩,1878年到1881年,又獲得二千五百六十萬兩。
解決糧餉問題后,1876年4月,左宗棠命劉錦棠、金順率隊出關,開始收復新疆,至1878年1月清軍進入和闐(“和田”的舊稱)收復南疆四城,左宗棠收復除伊犁以外新疆南北。1880年6月,左宗棠駐軍哈密,聲援赴俄談判的曾紀澤,同年,清廷命左宗棠回京覲見。五年時間內,左宗棠針對新疆問題展開種種舉措,為鞏固祖國統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左宗棠治疆政策
“回疆之役,削平易而善后難”。1878年,左宗棠收復新疆后,將修河渠、筑城堡、行屯墾、設義塾以及改革賦稅作為治疆的舉措。
(一)力主新疆建省
左宗棠對新疆設省問題的關注由來已久。1833年,左宗棠寫下“西域環兵不計年,當時立國重開邊”“置省尚煩他日策,興屯寧費度支錢”的詩句,提出在新疆設省的主張。
1875年,左宗棠在與劉典的書信中提到出兵新疆在于討伐逆賊,更在于“劃分疆界,駐兵置守,立省設郡縣,定錢糧”。1877年,成功收復北疆后,左宗棠指出“伊古以來,中國邊患,西北恒劇于東南……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強調新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提出“為新疆畫久安長治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首次提出新疆設省一事。1878年,左宗棠收復新疆南北,再次上書“擬改行省郡縣,一并通盤籌畫”。
新疆改設行省是一項重大的行政體制改革,清廷對此顧慮頗多。1878年2月,清廷認為新疆改設行省茲事體大,要求左宗棠拿出具體方案。1878年10月,清廷又寄諭左宗棠:“其余各城改設行省,究竟合宜與否?……倘置郡縣,有無可治之民?不設行省,此外有無良策?”清廷與左宗棠對設省一事的態度不同,主要緣于二者看待新疆問題的角度不同。
一方面,從左宗棠的角度看,1759年,乾隆帝平定大小和卓之亂,在新疆建立起以伊犁將軍為核心的軍府制度,輔之以伯克(官名)制與札薩克制。隨著時間的推移,軍府制為主的多元行政體系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端。就軍府而言,“地周二萬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政教旁敷、遠民被澤,不亦難哉”。伯克制和札薩克制更是如此,在數次叛亂中,阿奇木伯克(清代新疆回部各伯克中官階最高者)往往起到了推濤作浪的作用。軍府之下,新疆基層社會大多掌握在伯克手中,民眾往往知伯克而不知國家,清廷對新疆的治理僅在表面。另而,伯克借助新疆各級大臣權勢壓迫民眾,伯克制成了潛在的分裂因素。總之,舊制度已然不適合在新疆繼續推行,行省的設立是時代所需。
清廷所持的慎重態度是針對新疆內部特點考慮的。其一,軍府制下,伊犁將軍、都統、參贊大臣、辦事大臣、領隊大臣等高級官員均是旗人,郡縣的實行可能會沖擊滿人在新疆的地位。其二,此前清廷的“因俗而治”政策在某種程度上是民族平等的體現,更是清代統治者構建和睦民族關系的嘗試。軍府之下,新疆的直接管理較為松散,縣及以下政權多半由地方領袖掌握,郡縣的設置可能會影響新疆局勢。
阿古柏之亂時,許多少數民族首領擁護清廷統治,奮起反擊。如1871年,“經扎齊魯克齊伯克瓦齊爾督兵追擊,殲斃賊目一各,余匪四五十名”。1879年,左宗棠上書朝廷建立忠義祠。再如哈密王,在阿古柏之亂時,拼死抵御,籌措糧餉,收復哈密。各少數民族首領在面對侵略時維護國家統一的行為,體現出清廷治理新疆的政策較為得當。因此,在左宗棠的力諫之下,1878年末,清廷明示左宗棠:“新疆議設行省,事關創始,必須熟籌于事前,乃能收效于后日。……然后設官分職,改設郡縣。”左宗棠揆諸當下,經營新疆,在各城設置善后局惠澤各地百姓,為1884年新疆建省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二)恢復戰后經濟
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在其統治區域內“搜索糧石,搶殺橫行”,導致民不聊生。為安撫新疆民眾,左宗棠秉行“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國必與焉”的宗旨,強調用兵后安民利民的重要作用,與阿古柏形成鮮明的對比。
新疆十余年動亂,新疆各地民眾深受其害。為幫助民眾度過艱難時期,西征軍在左宗棠率領下采取收復一城、改造一城的辦法,各城“由各善后局轉飭各回目糾集民夫民匠帶赴工次……仿以工代賑之法,每日給發食糧”,通過以工代賑的方式,在鞏固城防的同時給予民眾一條生存之路。隨后左宗棠命“飭各地方官散給牛籽,招徠開墾”。1878年,善后局在北疆地區安置五千多戶流民,為鞏固北疆地區作出重大貢獻。
賦稅方面,雍正時期的攤丁入畝制度因形式復雜并未在新疆推行,新疆仍實行按丁索取的制度,因而常常導致富者稅少而貧苦者稅重。另外,南疆地區因語言的限制,各伯克在征收稅款之時,常借清廷名義橫征暴斂、中飽私囊,“民眾不怨其頭目,而怨恨于清廷”。因此,左宗棠認為改革新疆傳統的賦役制度是極為必要的,并規定“辦理善后征糧各局,暫按什一征收”。對于徭役,規定“布縷粟米之征外,不廢力役之征”,與民休息。左宗棠對賦役制度的改革,激發了新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保障了新疆經濟的恢復。
此外,還有恢復屯墾,興修水利。左宗棠認為農業是“人生第一要務”。清末新疆社會局勢動蕩,田地荒蕪,嚴重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因此,恢復新疆農墾成為左宗棠急需解決的問題,屯田成為恢復農墾的重要舉措。歷代邊疆屯田,首重軍屯建設,軍屯既可解決戍守軍隊的軍糧,也可穩定將士、鞏固邊疆。隨著軍屯的建設發展,兵寓于農,卻出現“強募游手以充兵而兵廢,卒至戰不能戰,守不能守”的情況。軍屯戍邊固然重要,但左宗棠認識到:“要籌軍食,必先籌民食,乃為不竭之源;否則兵欲興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興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濟?”因此,為“籌民食”,左宗棠開始重視民屯的恢復。
新疆多年動亂,荒地多,人員少,因此,難民安置成為當時的難題。左宗棠采用收復一城、改造一城的方式,在收復地區設置善后局,由善后局協助民屯的推行。如經烏魯木齊一役后,善后局向解救出的和躲匿在周邊各地的民眾發放種子、耕牛等生產資料。收糧時除民眾日常的食用與種子之外,余糧按照當地價格收購,這一舉措對烏魯木齊周邊地區的開墾起到推動作用。左宗棠招撫難民屯墾取得了極大的成效,1878年,迪化州、鎮西廳等地耕地規模擴大,人口增長,北路地區屯墾成效顯著。在南路地區,清軍進軍莎車之時得知“多裹纏回至喀什噶爾”后率軍擒賊解救民眾。左宗棠對各族民眾加以安撫,“設撫輯善后局,籌給賑種,待其來歸,課以耕牧”。左宗棠在南疆的舉措奠定了良好的軍民關系,增強了清廷在南疆地區的公信力,推動了南疆農業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進軍新疆前,左宗棠就指出軍屯所存在的問題:“且既掛名伍籍,又令其從事耕耘,譬猶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兩者相兼,必致一無所就。”多年戎馬生涯使其深知兵在精而不在多。因此,左宗棠在出兵前上奏清廷“擇其精壯有膽之兵”,以此方式進行地區性的軍隊改革,通過篩選裁汰老弱、保留精壯,使各營的戰斗力得到提升,推動軍屯的建設。1878年,“鎮西廳屬兵民報墾五萬數千余畝,奇臺報墾民戶九百有余,軍營新墾六千六百余畝”。由此可見左宗棠在屯田方面的舉措得當。
同時,左宗棠也著眼于與屯田相輔的水利設施的修建。新疆土地“非沙即堿,厥性輕浮,消長無常”,屯墾工作的恢復定然涉及各地區水利設施的修建。1880年,左宗棠下令在哈密、迪化州、庫爾勒等地廣泛修建水渠,并對各地的舊渠進行修復。對參與修渠的民眾,“給以雇值”,“亦議給工食”。各地修建水利設施,雇傭民工,發放錢糧,將國家救濟與基礎設施修建相結合,幫助民眾度過困難時期。總之,左宗棠在新疆對舊渠的修補與對新渠的開鑿,極大地改善了新疆各地用水窘迫的局面,為屯田的恢復奠定了基礎。
(三)改善經濟結構
新疆地域遼闊,地區間自然條件差異較大。隨著屯墾工作的推行,左宗棠開始嘗試改革新疆的傳統經濟結構。
第一,禁鴉片,推桑棉。清末,鴉片巨額的利潤和極大的需求量使罌粟的種植由我國的東南擴大至西北地區。新疆鴉片產量較大,產地主要分布在南路的庫車、輪臺及北路的呼圖壁、塔城、奇臺、昌吉等地。新疆罌粟的廣泛種植多基于巨額利潤驅使。考慮到新疆地區日用品多為毛氈,對于桑棉的需求較大,另外國外購絲量龐大,新疆的供給有限。為肅清新疆的罌粟問題,左宗棠揆諸當下,勸導民眾種植桑棉,使民獲利于桑棉,以禁絕鴉片。
棉花方面,左宗棠勸解民眾種植棉花時提到“皆知棉利與罌粟相埒,且或過之”,彼時棉花的產量雖低,每畝僅有二十斤的產量,但獲利仍高于罌粟。蠶桑方面,新疆的桑樹較多,陸續統計共有八十萬六千余株。但除和闐蠶絲興盛以外,其余各地均將其或醫或食。為改善這一現狀,1880年,左宗棠“請賞給已革知縣祝應燾原銜,飭赴新疆各處教習蠶桑”。在養蠶的生產技術方面,左宗棠則于同年“飭募雇湖州士民熟習蠶務者六十名……教民栽桑、接枝、壓條、種葚、浴蠶、飼蠶、煮繭、繅絲、織造諸法”。各地區設置紡織局收購民眾手中的蠶絲。在官方幫助及高額利潤的驅使下,新疆地區的紡織業獲得一定的發展,鴉片問題有了較大的改善。
第二,發展畜牧業。新疆北路地區地域廣袤,水草豐足,畜牧業較為發達。阿古柏之亂后,草場荒廢,牧民顛沛流離,畜牧經濟由此深受其害,安撫各地區牧民成為首要工作。1878年,左宗棠請奏“土爾扈特人眾陸續旋回游牧,前有旨賞給銀四萬兩”,幫助各部落尋歸草場。同年,左宗棠令鎮迪道周崇傅選擇水草豐美處,查明戶口,向鄉民散發羊種、牛、耔,所領成本三年無息歸還。該政策在各地的推行并不盡人意。就富農而言,這是徒增瑣事,因此其領養的積極性不高。對貧民來說,長期地方救助養成的惰性使領養的羊成為盤中之餐。這導致促進邊疆畜牧業的實踐無疾而終,但仍是左宗棠對于邊疆經濟發展的一次嘗試。
幫助牧民恢復生產是其一,畜牧產品銷售也同樣重要。在傳統認知中,邊疆地區城堡的修建多用于軍事方面,經濟職能較少涉及。但左宗棠認為“以城堡工作言之,居國屋宇,以利棲止,農商工匠之所宜也。行國氈廬,移逐水草,畜牧游獵之所便也”。因此,左宗棠命人修繕各城,如奇臺、綏來、喀喇沙爾、庫車。各城或因舊基,或拓新地,各城的修補不僅鞏固城防,更使得周邊游牧的民眾有一個交換商品的固定地區,從而改善了牧民的生活。
第三,植樹造林。左宗棠素來重視植樹工作。他主政陜甘時見風沙嚴重,便開啟了對邊疆生態治理的實踐。彼時,西北的生態問題已不容小覷,自嘉峪關以外“地近戈壁,飛沙堆積,州城東、西兩面沙與城齊”。收復新疆后,左宗棠考慮到新疆經歷兵燹,民眾“棲身無地,糊口無資,焉有余力種樹”,這樣的重擔便落在了西征軍身上。
各營軍隊在左宗棠的號召之下廣植官樹,形成“征戍更番,士氣常新,樂事赴功,爭先恐后。則防軍之前勞不可沒,而后效固可期也”的局面。對于樹種的選擇,左宗棠也多加考慮,他認為桑樹的種植不僅可改善環境,更讓官民有利可得。1911年,袁大化在赴任新疆途中曾寫道:“驛路一線……長楊夾道,垂柳拂堤,春光入玉門矣。”
綜上所述,左宗棠因地制宜地發展新疆各地經濟,使各地區的經濟結構趨于合理。新疆各地基礎設施的完善,也使得官民們“閭閻鮮水旱之憂,行旅忘跋涉之苦”。
(四)推行文教
清代新疆治理基于維持邊疆穩定的目的,重在軍政,對于文教事業卻甚少涉足,導致新疆文教滯后。左宗棠認為新疆社會的穩定與教育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教育不力則語言不通,民眾才受“所謂條勒阿渾”迷惑。遂左宗棠收復新疆后對教育極為重視。1880年,左宗棠指出:“新疆勘定已久,而漢、回彼此捍格不入,官民隔閡,政令難施。”為改變這一現狀,左宗棠提出廣設義塾,通過義塾振興新疆的文教事業。
新疆所建義塾,“吐魯番八、精河三、烏蘇二,焉耆、拜城、沙雅各以次建設”,共37處。在廣設義塾的基礎上,左宗棠還以重資延請教習,教習每月多達六七十兩白銀。對于入學的普通民眾子女,供給筆墨書籍,減輕其負擔。繼任者劉錦棠主政新疆時延續左宗棠廣設義塾的政策,繼續在新疆普及基礎教育。左宗棠對于新疆文教的重視同樣體現在教育形式與內容上。就教育內容而言,義塾所授內容多為基礎性讀物。在教育形式上,為使民眾方便學習,左宗棠提倡雙語教育,如“譯刊圣諭十六條,附律易解一卷,刷印多本,分發各城義塾及大小伯克頭目誦讀講解,并令傳告鄉民共知觀感”。
收復新疆后,面對教育讀本的匱乏,左宗棠應州縣稟請創辦了崇文書局、關中書院和迪化書局等出版機構。所刻發之書,針對不同人群,如幼童、成人,并且不乏治國安民之書、道德教育之書。面對新疆教育滯后的局面,左宗棠命部屬在烏魯木齊開設書局,刊發《千字文》《三字經》《百家姓》《四字韻語》及《雜字》各本,“令回童讀書識字,通曉語言”。通過印刷基礎性讀物,培養新疆少數民族兒童學習漢語。左宗棠希望通過這種方式來復興新疆文化教育、弘揚儒家思想,將中原先進文化和生產技術傳播到各少數民族中。
左宗棠對新疆文教事業的推動,相較之前頗具成效,入學的少數民族學生“聰穎多者,甫一年而所頒諸本已讀畢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讀書為榮,群相矜寵,并請增建學舍”。縱使新疆建省后文教推行不力,但左宗棠對于新疆文教事業改善的嘗試卻是不爭的事實,可為今日所鑒。
三、左宗棠治疆政策的成效
左宗棠治疆立足實際,措施得當,為新疆的恢復與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左宗棠昔日之舉,對于今日新疆的發展仍有借鑒價值。
(一)政治方面
左宗棠收復新疆、治理新疆。在此期間,為克服傳統軍府制的弊端,各城的善后局深入新疆基層。從此,伯克制度正式退出歷史舞臺,為1884年新疆建省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各地方首領自覺抵御阿古柏入侵。經此一役,新疆各民族在反抗阿古柏的斗爭中團結一致,共御外敵,民族意識向民族自覺轉變。建省后,新疆與中原地區一軌同風,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凝聚力鞏固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國家大一統局面得到鞏固。新疆建省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為“因俗而治”的邊疆地區改革提供了寶貴借鑒。總之,左宗棠為新疆建省的功績永遠留在中華民族邊疆建設史中。
(二)經濟方面
左宗棠在收復新疆后實施了一系列經濟政策,頗有成效。在推廣桑棉時,湖州民眾來到新疆,傳播蠶桑技術。與此同時,左宗棠不忘生態建設,“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所植楊柳被后世稱為“左公柳”。左宗棠之后,歷任巡撫也在不斷地進行著改革,或有所得,或有所失,但總體上推動了新疆地區的經濟發展,對改善民生、維持社會安定、加強邊疆建設起到積極的作用。
(三)文化方面
清朝時期,在軍府制下,新疆的文化和教育幾乎停滯不前,特別是南疆地區,人口相對閉塞,部分勢力以宗教為名,利用新疆官民之間的語言交流障礙,“捏造邪說,肆其誘脅之術,人心易為搖惑,禍亂每由此起”。左宗棠收復新疆后,加強了對新疆教育的管理,并在新疆各地開辦義塾。通過普及文化知識,加強交流和合作,確保新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進而維護國家整體的安全。
參考文獻
[1] 左宗棠. 左宗棠全集[M]. 長沙:岳麓書社,2014.
[2] 費正清. 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3] 趙爾巽. 清史稿[M]. 北京:中華書局,2020.
[4] 清實錄·德宗實錄[M]. 北京:中華書局,1987.
[5] 羅正鈞. 左宗棠年譜[M].長沙 :岳麓書社,1983.
[6] 清實錄·穆宗實錄[M]. 北京:中華書局,1987.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光緒朝朱批奏折[M]. 北京:中華書局,1996.
[8] 慕壽祺. 甘寧青史略[M]. 臺北:廣文書局,1972.
[9] 袁大化. 撫新紀程[M]. 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10] 曾問吾. 中國經營西域史[M]. 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
[11] 王樹枬等,朱玉麒,等. 新疆圖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2] 朱壽朋. 光緒朝東華錄·第一冊[M]. 北京:中華書局,1984.
[13] 梁家貴. 左宗棠與劉錦棠在新疆建省方案上的分歧[J].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4).
[14] 方駿. 中國近代的鴉片種植及其對農業的影響[J].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0(2).
[15] 苗普生. 廢除伯克制度與新疆建省[J]. 新疆社會科學,1987(4).
[16] 季云飛. 左宗棠和新疆建省[J]. 南京社會科學,2003(6).
[17] 包爾漢. 再論阿古柏政權[J]. 歷史研究,1979(8).
[18] 紀大椿. 論清季新疆建省[J]. 新疆社會科學,1984(4).
[19] 陳理. 左宗棠與新疆建省[J].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1(2).
[20] 洪濤. 左宗棠對新疆經濟建設的貢獻[J]. 歷史教學,1984(9).
[21] 馬振舉. 論左宗棠經營新疆的重大貢獻[J]. 南開史學,1983(2).
[22] 馮志文. 左宗棠歸復新疆及其對發展新疆經濟的貢獻[J].喀什師范學院學報,1985(1).
[23] 劉軍. 左宗棠新疆社會經濟改革思想初探[J]. 遵義師范學院學報,2006(6).
[24] 汪長柱. 試論左宗棠民族思想的特點[J]. 湖南師范大學學報,1985(5).
[25] 孫占元. 論左宗棠的教育思想[J]. 社會科學戰線,1996(6).
[26] 付宏淵. 左宗棠發展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思想和實踐[J]. 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