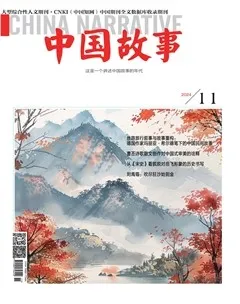淺論訓詁的現世價值
【導讀】《左傳·隱公元年》載“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后世對此句有不同的注解,造成歧義現象。本文運用訓詁學方法來消解歧義,對此句進行歧義分析,從而彰顯出訓詁的現世價值。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這一解經語,我們認為是對《春秋公羊傳》經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的解釋。后世學者對這一解經語有不同的注解。魏晉時期的杜預作《春秋經傳集解》,這是現存最早的《左傳》注本,他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下批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據此,我們可以歸納出杜預對此解經語的分析,他認為“隱公”是“立而奉”的施事主語,“之”即“桓公”,是“立而奉”的受事賓語,動詞“立”的間接賓語為“太子”。今人楊伯峻作《春秋左傳注》,指出:“實則是隱公行國君之政,而實奉桓公為君,非立為太子。桓公之被立為太子,惠公未死時已如此,不待隱公再立之。桓公雖非初生嬰兒,其年亦甚幼小,不能為君,故隱公攝政焉耳。”據此,我們可以歸納出他對此解經語的理解為“隱公被立為代理國君,尊奉桓公為國君”。
后世學者對“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產生了不同解讀,我們可以理解為產生了歧義。歧義是現代漢語研究的問題,國內最早對歧義現象進行研究的是趙元任先生,他曾經舉出“雞不吃了”這一經典的歧義結構。我們認為單獨看“雞不吃了”這一語言單位是具有歧義的,但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確是意義明確的。設想一個吃飯時的語言環境,說話者傳達出“雞不吃了”這一語音,聽話人在接收到語音信息進行解碼時,一定會自然地解讀為“他不吃雞這道菜了”。同理,對“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這一書面文字的解碼也要依托于一個真實的語言環境。我們認為只有通過訓詁才能還原其語境,構建貼切真實的語言環境,從而消解歧義。正如閻若璩在《潛邱札記》卷六中所言:“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
一、“本立而道生”——以訓詁消解歧義
消解“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歧義的路徑是要構建一個貼切真實的語言環境,而方法則是訓詁。下文將對“歧義”“訓詁”的相關內容作出說明,為后文“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的歧義分析提供理論支撐。
(一)訓詁的定義與方法
學界內研究文獻給歧義下的定義不下20種,綜合來看,大多數學者對其定義的意見較為統一。據此,我們可以歸納出,歧義就是把一個不違反語法和邏輯的語言形式孤立起來(即脫離語境來看),而導致的若干種不同的理解。因此,閱讀者無法準確選擇歧義的結構構成和意義內容。
關于“訓詁”的原本意義,現在的人多簡單理解為“解釋古代詞義”。這一認識具有片面性。黃侃在《文字聲韻訓詁筆記》中寫道:“詁者,故也,即本來之謂。訓者,順也,即引申之謂。訓詁者,用語言解釋語言之謂。若以此地之語釋彼地之語,或以今時之語釋昔時之語,雖屬訓詁之所有事,而非構成之原理。真正之訓詁學,即以語言解釋語言,初無時地之限域。”由此,我們將訓詁定義為“以語言解釋語言”,而非片面的“解釋古代詞義”。
宋永培先生在《訓詁方法新論》中指出了三種基本的訓詁方法及其聯系,分別是以形索義、因聲求義和比較互證。以形索義的理論依據是漢字形義統一的原則,我們在運用以形索義的方法時要從本字出發,以漢字的構形意圖即筆意來解說意義,還要有大量翔實的語言材料作為證據。因聲求義的理論依據是“訓詁之旨,存于聲音”的原則,我們在運用因聲求義的方法時要利用古音研究的成果,注意同根詞“音近義通”的現象。“比較互證”是以形索義和因聲求義得以正確運用的基礎,其實質在于對語言文字材料進行系統貫通。
(二)訓詁是消解歧義的不二法門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文字將言語從語言環境中孤立出來,以文字符號的形式來記錄語言事實。我們認為,中國文字起源于圖畫記事,其象形性濃厚,在社會發展早期,運用象形、指事所創造的文字已經可以滿足人們的需要。這一階段文字的形體與其所指稱的事物一一吻合,文字解碼者很難會有多種解碼。隨著社會生產力提高,文字指稱事物的準確性與字符數量精簡性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一個書寫單位即字符,承擔著不止一個義項。例如,“花”既可以指稱自然界的花朵,也可表示動詞,花費多少錢。單一漢字義項的增加也增大了歧義產生的可能。在記錄言語事實的時候,文字是沒有歧義的。而文本解讀者在對文字記錄的言語事實進行解碼的時候,往往會產生歧義。造成歧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書面文字具有語境缺失的先天不足。歧義現象是一種普遍的語言現象,不僅存在于各種語言之中,而且也存在于某一語言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我們將訓詁定義為“用語言解釋語言”,這就將訓詁從傳統“小學”中解放了出來。“用語言解釋語言”,具體來說,就是用“今語解釋古語”,用“通語解釋方言”。通過訓詁的方法,把某一語言形式的語境盡量貼切真實地構建出來,可突破文字記錄語言的先天不足。從這個角度來看,訓詁可謂是消解歧義的不二法門。
二、“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的歧義分析
歧義產生于文字符號解碼環節,而訓詁可以構建起文字符號編碼時的語言環境來消解歧義。霍爾是“語言學和符號學轉向”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編碼與解碼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編碼者依據語言規則實現了信息的符碼化,信息通過一系列復雜的傳播路徑到達解碼者那里。然而,當解碼者解讀由編碼者所編碼的信息時,卻無法保證能夠真正地理解編碼者最初設定這個信息的本意。由此便產生了歧義,即符號信息解碼與編碼過程中的偏誤。其原因則可從信息編碼者與解碼者的知識背景、價值觀念、社會身份、思想意識等方面綜合考量。這就是霍爾的編碼與解碼理論的基本內容。在霍爾理論的基礎上,我們對“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進行了解碼,得出了6種不同的理解,然后通過訓詁的方法來構建語境,從而消解歧義。
(一)“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的多元解碼
1.這是隱公把桓公立為太子并且以桓公為尊的原因。
2.這是隱公把桓公立為太子但以隱公為尊的原因。
3.這是隱公被立為國君并且以隱公為尊的原因。
4.這是隱公被立為國君但以桓公為尊的原因。
5.這是隱公被立為代理國君并且以隱公為尊的原因。
6.這是隱公被立為代理國君但以桓公為尊的原因。
“是以”在古文中經常連用,相當于現代漢語的因此、所以。具體來分析,“是以”是賓語前置。“是”為代詞,“以”是介詞,因、由于之義。在對“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解碼時,我們參考了諸葛亮《出師表》“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中“是以”的用法。造成這6種不同解碼的影響因素具體來看有三方面:首先是桓公在惠公生前是否被立為太子;其次是隱公是被立為國君還是代理國君;最后是“而”作為連詞所連接成分的多重語義關系。
(二)隱公與桓公的身份確認
據《左傳·隱公元年》載:“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說文》載:“元,始也。”“元妃”為第一次所娶正夫人,“繼室”聲子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為“賤妾”,《左傳·哀公二十四年》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左傳·隱公三年》載:“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那么隱公的生母“聲子”并非為夫人,由此可以確認隱公并非正室所生,不是嫡子,桓公的生母“仲子”應當為正室。楊伯峻在《春秋左傳注》中提出的“桓公之母仲子死,以夫人之禮為之葬”和《左傳》“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可以為證。總之,桓公和隱公都是魯國國君惠公的兒子。桓公是夫人仲子所生,為嫡子。隱公是繼室聲子所生,不是嫡子。結合中國古代嫡長子繼承制可得,隱公是沒有資格被立為太子從而繼承王位的,桓公作為嫡子具有被立為太子的資格。
桓公是在惠公死前還是死后被立為太子的呢?楊伯峻認為:“桓公之被立為太子,惠公未死時已如此。”我們同意他的意見。《左傳·隱公元年》載:“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駢雅訓纂》:“古人太字多不加點,如大極、大初、大素、大室、大廟、大學之類。后人加點,以別小大之大,遂分而為二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言:“后世凡言大而以為形容未盡則作太。”由此可以得出“大子”即“太子”,是封建時代嗣君之稱。根據“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我們可以再次確認惠公未死時,桓公就已經被立為了太子。
最后,隱公是國君還是代理國君呢?我們同樣贊成楊伯峻先生的意見。他認為:“訖隱公之世,不稱即位,惠公之葬弗臨,與桓公母仲子之死則用夫人之禮,于己母則僅稱‘君氏卒’,是不用夫人禮,處處皆足以明之。攝位稱公以猶周公攝位稱王,故周禮也。”魯國姬姓,周文王之子周公旦之后,承襲周禮理所當然。另外,《左傳·隱公元年》明確記載:“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說文》言:“攝,引持也。謂引進而持之也。攝猶兼也,皆引持之意。”《孟子·萬章上》載:“堯老而舜攝也。”這里的“攝”也為代理、兼理之義。可見,“公攝位”明確了隱公為代理國君佐政的身份,更是春秋經文“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公即位”的又一例證。
通過訓詁的方法,我們比較互證出了隱公與桓公的身份,得出隱公為代理國君,桓公在惠公在世時就已經被立為太子這一結論,從而還原了書寫者編碼時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至此,我們可以否定“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多元解碼的前四種情況。
(三)“而”的多重語義關系
《說文》載:“而,頰毛也,象毛之形。”可見,“而”最初是一個名詞,指頰毛。考察古代文獻,除在《周禮·考工記·梓人》“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這一處見過“而”用作名詞,其余多用作代詞、語氣詞和連詞。“而”作為連詞的用法較為復雜,《古代漢語虛詞詞典》將連詞“而”的用法分為十種。既可以表示并列、順承、進層、強調或轉折,還可以連接主語和謂語或者表示時間期限等作用,用法多樣且復雜。這加深了明確辨析“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語義歧義的難度。
縱觀“而”作為連詞時的不同用法,我們可以發現,其分類依據是“而”所連接的語言片段之間的語義關系與語法成分。對“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進行語法和語義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不同的情況。
1.是以隱公|立而奉之(主謂結構,“而”表順承)
2.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而”連接詞組,表示轉折)
其中,代詞“之”的語義指向決定著“而”的語法功能。代詞“之”可以理解為指代隱公,也可以理解為指代桓公。杜預在《春秋經傳集解》中說:“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可見,他認為“之”指代的是桓公。再結合古代漢語書面語行文簡練、多省略的特點,我們認為代詞“之”指代的是桓公。“是以隱公立而奉”完全可以表達“這是隱公被立為代理國君并且以隱公為尊的原因”。而沒有必要再加一個“之”字。“之”所指代的對象明確后,“而”所連接的語言片段的語義關系也就固定了下來,“是以隱公立而奉之”中的“而”表示轉折的語義關系。至此,我們可以否定“是以隱公立而奉之”的第五種解碼:“這是隱公被立為代理國君并且以隱公為尊的原因。”“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應該理解為第六種解碼:“這是隱公被立為代理國君但以桓公為尊的原因。”
三、結語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書寫者將言語轉化成字符進行編碼并將言語固定在文本中,對于言語的發出者和書寫者來說,這一階段是不產生歧義的。歧義產生于符號的解碼階段,其對象是聽眾和文本讀者。文本歧義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書面文字具有語境缺失的先天不足。歧義不僅僅是現代語言學家研究的范圍,其作為一種語言現象普遍地存在于人類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
中國傳統語言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古文字、古文獻,即古代漢語書面語。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語言不斷發展變化,記錄語言的文字形體也必然會產生變化,正如《說文解字》所言:“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以字考經,以經考字”是中國古代傳統學術規范,后世的人們在閱讀傳世典籍時,必然會有諸多不明之處。例如,顏之推僅在《顏氏家訓·書證篇》中便記錄了自己在閱讀經史典籍時所作的47條考證。古代的“小學”大體上相當于今天的“傳統語言學”,而又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傳統語言學”。“訓詁學”是中國傳統語言學“小學”的核心內容,它濫觴于周秦,成熟于西漢,在清朝時達到頂峰。但古人認為“小學”就是為經學服務的,是經學的附庸,這既不利于人們對語言本質的認識,也不利于人們對語言作理論上的探討,更不利于整個傳統語言學的發展。周祖謨先生指出:“訓詁學就是解釋語詞和研究語義的學問。舊日只看作‘小學’的一個部門,現在正逐漸發展為一門有科學體系的漢語語義學。”這一看法肯定了訓詁在解釋詞語和研究語義方面的價值,也預示了中國傳統訓詁學的發展方向。
總之,訓詁學不應被禁錮在“小學”的牢籠中。通過以形索義、因聲求義和比較互證等訓詁方法,可以構建書面語在編碼時候的語言環境,從而消解書面語言在解碼環節可能產生的歧義。
參考文獻
[1] 杜預. 春秋經傳集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2] 楊伯峻. 春秋左傳注[M]. 北京:中華書局,2016.
[3] 田清秀. 現代漢語歧義及其積極意義[J]. 漢字文化,2024(3).
[4] 閻若璩. 潛邱札記[M]. 北京:中華書局,2023.
[5] 尤慶學. 漢語歧義研究綜述[J]. 漢語學習,2001(4).
[6] 黃侃. 文字聲韻訓詁筆記[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
[7] 宋永培. 訓詁方法新論[J].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4).
[8] 葉蜚聲,徐通鏘. 語言學綱要[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9] 肖爽. 電視話語中的編碼與解碼[J]. 上海文化,2018(2).
[10] 許慎. 說文解字[M]. 湖南:岳麓書社,2020.
[11] 張萬春. 淺析“而”字用法[J]. 青年文學家,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