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反智主義”回歸

生物制藥,被譽為美國經濟皇冠上的明珠,它為美國患者提供了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藥物選擇,也創造了數百萬個高薪崗位。
但現在,這樣一個彰顯美國榮耀的產業,正在瑟瑟發抖。
近期,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提名了一位“怪杰”,小羅伯特·肯尼迪,來領導美國最高衛生機構—美國衛生部。任命消息一出,美國多個衛生和醫療企業的股價應聲下挫,疫苗公司最為慘重。
小肯尼迪今年8月投靠特朗普,但他其實來自民主黨歷史上權力顯赫的名門望族—肯尼迪家族(其伯父是大名鼎鼎的約翰·F. 肯尼迪)。跟這個輝煌一時的精英家族格格不入的,是小肯尼迪四處傳播公共衛生陰謀論,給人留下的“滑稽”形象。
他是知名的反疫苗活動家,除了質疑疫苗的作用,他還認為Wi-Fi會致癌,認為HIV病毒不是導致艾滋病的元兇,宣揚自來水加入消毒用的氟化物會導致生物性取向改變,以及堅稱5G信號對人體有害。
他即將走馬上任的衛生部,下設13個機構,包括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職責涉及公共醫療衛生的方方面面,權力不可謂不大。
小肯尼迪的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健康”,但科學家們無不表示震驚。醫療專家警告,也許美國將會在未來四年將出現難以收拾的公共衛生危機,并且在全球范圍內鼓勵針對醫學專業的陰謀論風潮。一位制藥公司的說客說:“對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行業來說,說些無稽之談的人來掌權,是個壞消息。”
而事實上,盡管精英人士對此震驚和疑惑,但放在美國的政治文化中,小肯尼迪的出現,并不令人意外。相反,一個“充滿實干精神”的陰謀論者,遠比“心思復雜”的知識精英更加無害,也更受普通民眾歡迎。這個定律,不僅適用于總統選舉,也適用于普通官員。
“他們吃的是毒藥”
在社交媒體上,這樣一張照片引起了熱議:
在特朗普的私人飛機“特朗普一號”的餐桌上,特朗普、馬斯克、小特朗普和小肯尼迪分別坐在兩旁,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則站在小特朗普的身后—眾所周知,特朗普一直是快餐連鎖品牌的忠實消費者,在私人飛機上吃漢堡、薯條和喝無糖可樂的照片和視頻已經充斥網絡。
餐桌上擺滿了麥當勞的外賣盒子,其中小肯尼迪格外吸引眼球。只見他手拿著漢堡,臉上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在美國的社交媒體上,小肯尼迪這幅形象很快成了惡搞對象。
“當你進入癮君子巢穴的時候,人家讓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起吸毒,這樣才能測試出你不是警察。”
美國網友之所以把漢堡和薯條往“涉毒”方向想,皆因小肯尼迪過去把快餐說成是“毒藥”。就在11月13日,小肯尼迪面對美國記者還說:“特朗普專機上的食物,簡直就是毒藥。”

小肯尼迪說話聲音顫抖,話音未完就會吃力地大吸一口氣,仿佛氧氣不足一樣,這會導致他的頭部輕微擺動。他臉部皮膚也總是顯出紫一塊紅一塊,脖子的肉疙瘩隨著嘴唇開合而上下抖動。他用沙啞的聲音告訴別人,自己的腦子曾經住了一條蠕蟲,所以,他的大腦被吃掉了一部分。
這事沒人知道真假,就像他一直宣揚的那些陰謀論一樣。但反快餐的論調,確實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畢竟,快餐的確導致美國人肥胖,也出現多種健康問題。然而放在喜歡吃快餐的特朗普團隊里,他又格外違和。
總之,小肯尼迪能成為衛生部長,本身也充滿了矛盾和撕裂。
一方面,他暴論頻出,很多公共衛生言論半真半假,甚至毫無根據。另一方面,憑借著對美國醫療體系的批評,他總能收獲大量的支持者。畢竟,在很多人看來,這個系統的確需要變革。
其中與他最不對付的,便是FDA,他指責這個機構聽命于大制藥公司和大食品公司,大選前,他還說“FDA對公眾健康的戰爭即將結束”,奉勸那些阻止美國人獲得生牛奶、伊維菌素和其他爭議療法的衛生官員趕緊“收拾行囊”。
至少,從民主黨“轉”到特朗普陣營,小肯尼迪的個人人設,已經成功打造成特朗普支持者心中“撥亂反正”的象征。
在一張被大量轉發的網絡圖片上,左側是拜登任命的跨性別助理衛生部長瑞秋·萊文,右側則是裸著上身露出肌肉的小肯尼迪。
在特朗普粉絲群體中,練成一身肌肉的小肯尼迪,形象更“健康”,擔任公共衛生部門一把手比萊文更加有說服力。
環保先鋒還是陰謀論者?
肯尼迪家族到了小羅伯特·肯尼迪這一代,已經淪落到了政壇的邊緣。
隨著老牌參議員泰德·肯尼迪在2009年去世,肯尼迪家族再也沒有在美國行政或者立法系統中占據一席之位的要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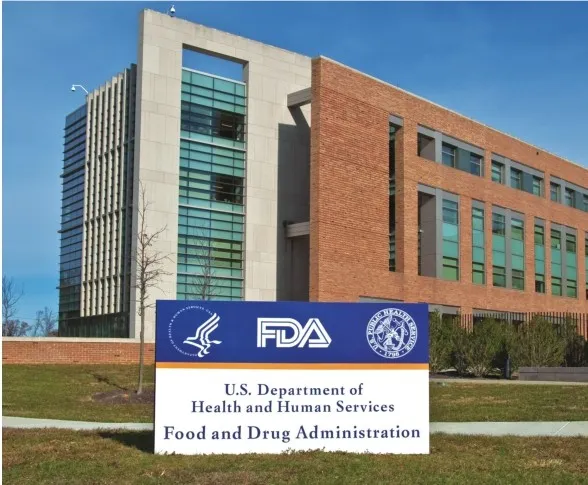
小羅伯特·肯尼迪一直以“環保律師”活躍,多關注河流污染議題,在2020年前,其政壇影響力微乎其微。隨著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美國社會對疫苗和各種抗疫措施的態度出現極大的撕裂。
關于抗疫措施的取舍,乃至病毒的起源,衛生領域的問題很快上升為政治爭議。在一段偷錄的視頻中,小肯尼迪在某次宴會上宣稱,新冠病毒是“專門針對高加索人種和黑人人種的”,而“最有免疫功能的人種是中國人和歐洲猶太人”。
小肯尼迪的諸多主張,聽起來淺顯易懂,但經不起推敲。跟許多陰謀論者一樣,初聽煞有介事,但是話鋒一轉,就拐向充滿政治目的的結論。在多次反疫苗集會中,小肯尼迪開始向美國社會傳遞這樣一種聲音:精英權貴集團借助疫苗和醫學隔離手段,試圖顛覆美國的民主制度。
就這樣,反對疫苗和質疑疫苗作用的人,把疫苗議題拔高到美國根本制度存廢的高度。美國人歷來重視個人選擇權和隱私權,加之對大型醫療公司的質疑,反疫苗隊伍迅速向特朗普支持者群體集中。
跟特朗普和其他反對疫苗接種人士一樣,小肯尼迪也把矛頭指向當時擔任白宮首席醫療顧問的福奇。
人們還記得,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福奇在特朗普講話時,站在一邊不時搖頭,或暗中偷笑。其意味深長的表情,仿佛是在取笑總統的滔滔不絕。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來,福奇就是暗中給特朗普下套,導致其應對新冠疫情失分,出現大量死亡案例,最終導致其敗選的關鍵人物。
2021年,小肯尼迪專門撰寫了一本書,名為《真實的安東尼·福奇:比爾·蓋茨,大型藥企,以及全球范圍內對民主和公共醫療的戰爭》,書中觀點正中特朗普支持者的下懷。小肯尼迪在書中認為,福奇從1980年代艾滋病疫情開始就玩忽職守,勾結美國大型藥企,在全球范圍內推行不可告人的目的。
無獨有偶,2022年6月,小肯尼迪在自己的臉書賬號上分享了一篇批判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大重啟》倡議書的文章。在新冠疫情期間發布的《大重啟》,被相當一部分人視為全球主義精英試圖用高科技手段剝奪平民發言權和財產的“反烏托邦”陰謀。倡議書中“你不會擁有任何東西,但是你會很幸福”的句子,被抽出來大肆鞭撻。在小肯尼迪和一眾特朗普支持者看來,這句話已經暴露了倡議書的“驚天大陰謀”,要把個人自主權和選擇權讓渡給全球精英,在全球范圍內沒收公民財產。
再來看看倡議書發起人,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本的個人形象:一個光著頭戴著眼鏡的德國人,滿口術語,有著工程師和經濟學家的雙重身份,跟全球范圍內的政商高層保持密切的關系。
這個施瓦本,正是美國底層民粹主義者們一直痛恨的再世“雞蛋頭”。
遭恨的“雞蛋頭”

英語里所謂“雞蛋頭”,指的是戴著眼鏡的光頭書呆子。上世紀50年代美國通俗流行文化里,雞蛋頭形象就開始流行,他們跟平民生活脫節、滿口讓人難以明白的術語、沒有實際勞動能力……因此備受奚落。
對于大部分美國選民來說,他們寧愿把權力交給一個膚淺直白但是“能夠干實事”的政客,也不愿意把權力交給滿腹經綸而且內心過于復雜的知識分子。所以,在當代,美國總統幾乎沒有一個是戴著眼鏡的學者。
從立國之初,美國人對知識分子就有某種愛恨交織的矛盾心態。“白手起家”的建國理念,讓美國文化基因里長期存在某種“會做事”的實業家崇拜,而對于挑剔的知識分子卻保持警惕態度。
在《美國的反智主義》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德看來,美國從誕生開始就體現了“智者建國”和“實業建國”兩極之間的張力。對啟蒙進步理念懷著向往的建國者給美國定下了憲政框架,但龐大的清教徒群體卻更加重視傳統和虔誠。從十三個最原始的聯邦州一直向西部擴張,美國社會一直推崇的是展示體力和勇氣的莽夫和牛仔,而不是心思復雜的讀書人。
“我對書的要求,就是不要讀書。”
“我對所有書都嗤之以鼻,為的只是讀懂唯一那本書(指的是《圣經》)。”

到了冷戰白熱化時期,美國社會對知識分子的警惕和懷疑達到了高潮。知識分子讀書多了,思想也就更加復雜了,也就會產生“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理想,從而讓美國在冷戰意識形態中走向不可挽回的道路。因此,在公共衛生和教育領域,美國社會對醫生和教師的要求,并非灌輸過于復雜的理念,而是“常識”。老師應該傳授的是技能,而不是知識和觀念。醫生不應該為了展示過人的智力和實驗能力,而是用“常識”去救人。
到了冷戰后,全球化盛行時期,美式“反智之風”一度有了下降的趨勢。克林頓和奧巴馬等自由派精英知識分子問鼎白宮,“進步派”美國人難得有了可以施展才華的舞臺。然而到了全球化進入逆風期,普通勞工在感到被資本出賣的時候,“反智文化”又重新有了反撲的跡象。

在這種語境下,“知識分子是危險的”“精英是虛偽的”“專家是愛撒謊的”,這種思維重新冒出頭了,并且找到了大肆宣揚的平臺。
對于許多美國人來說,脫了衣服露出肌肉的小肯尼迪,比戴著眼鏡的福奇博士更加有說服力。盡管說著不著邊際的論調,但他可能比“心思深沉”的知識精英更“無害”。
隨著要辦實事而且“武德充沛”的特朗普第二任內閣拉開帷幕,美國社會的鐘擺又從“智者”倒向“實業”的方向,美國人將會很快體會到一身肌肉的小肯尼迪,帶來的到底是福還是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