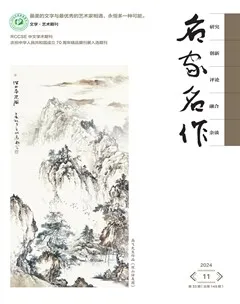貝多芬《第三鋼琴奏鳴曲》第一樂章音樂學分析
[摘 要] 《C大調第三鋼琴奏鳴曲》(Op.2 No.3)是貝多芬獻給海頓的作品之一,也是他音樂生涯早期的一部作品。通過對《第三鋼琴奏鳴曲》第一樂章的音樂本體進行分析,以及觀照該作品創作時的社會歷史語境,對其進行深入詮釋,以揭示作品內涵。
[關 鍵 詞] 貝多芬;音樂本體;音樂學;《第三鋼琴奏鳴曲》;和聲分析
路德維希·凡·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 — 1827)是集古典之大成、開浪漫之先河、古典主義三杰之一的德國作曲家。他創作的32部鋼琴奏鳴曲更是有“新約圣經”的稱號,《第三鋼琴奏鳴曲》(1975)是在他患上耳疾前創作而成,屬于早期的鋼琴奏鳴曲之一,后被編入第2號作品,其中的三部鋼琴奏鳴曲均是獻給海頓。由此,在貝多芬的早期奏鳴曲中能夠觀察到海頓的風格痕跡,即質樸與嚴謹的音樂風格、主題式發展的作曲技法。貝多芬在對前輩音樂的繼承基礎之上有所創新,將原本安排在第三樂章具有宮廷氣質的小步舞曲替換成更具有動力感的諧謔曲,比如與《第三鋼琴奏鳴曲》同年創作的《第二鋼琴奏鳴曲》。通過對《第三鋼琴奏鳴曲》第一樂章的音樂本體進行分析,以及觀照該作品創作時的社會歷史語境,進而對其進行較為完整的詮釋,以揭示作品內涵。
一、音樂本體分析
奧地利音樂學家漢斯立克(Eduard Hanslick,1825—1904)于19世紀中葉發表的《論音樂的美》一文,對當時乃至現在均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提出“音樂的內容就是樂音的運動形式”。其中蘊含的自律論美學思想在當時引起不小的爭論,即強調音樂的美在于其自身形式。隨著A.B.馬克斯(Adolf Bernhard Max,1795—1866)建立的19世紀最完善的曲式原則,以及里曼的功能和聲的提出,形式主義分析愈來愈占據作品分析的主要地位。盡管在后現代的語境下,西方學者開始追求從多元化、多重角度解讀音樂作品,如社會、文化、女性視角等,但是作品本體仍然是獲得音樂意義的一項重要的基本分析過程。“音樂學分析”由音樂學家于潤洋先生提出,指“一種更高層次上的、具有綜合性質的專業性分析;它既要考察音樂作品的藝術風格語言、審美特征、又要揭示音樂作品的社會歷史內容,并做出歷史的和現實的價值判斷,而且應該努力使這二者融匯在一起,從而對音樂作品的整體形成一種高層次的認識。”筆者認為,對于音樂本體之外其他維度的分析是分析一部作品必不可少的過程,作品正是在這種多元互動之下獲得更寬闊的詮釋空間,從而對作品產生更高層次的認識程度。
(一)曲式結構分析
《第三鋼琴奏鳴曲》第一樂章篇幅較長,但曲式結構尚在傳統范式之中,即為含有尾聲的奏鳴曲式。呈示部為1—90小節,其中主部為1—12小節,含有4小節補充的平行樂段,且補充的終止為侵入終止,同時鞏固了主調的調性。需要提及的是,開頭部分靈動、輕快的雙音跳動具有莫扎特的風格。
連接部為13—26小節,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具有過渡性質,主要是為了將調性過渡至G大調;副部為27—77小節,篇幅相對較長,且含有兩個發展階段與一個連接,第一副部為兩句式平行樂段,于g小調上陳述,第二樂句含有擴展,終止于g小調。兩個副部間5小節的連接,既是對副部一的補充又是對副部二的引入,同樣具有調性過渡的性質,將調性過渡至G大調。第二副部為平行樂段,第二樂句尚未結束,突然便在61小節C大調終止,直至77小節于G大調完滿終止,故筆者將77小節作為副部的結束。結束部為78—90小節,可劃分為兩個階段,終止于G大調。范乃信認為,整個呈示部仿佛可以一分為二,形成象征意義上的協奏曲雙呈示部,其中第一呈示部包括主部、連接部、第一副部三部分;第二呈示部包括第二部分、連接部材料的轉折部分和結束部。
展開部為91—138小節,可劃分為三個部分:其一為引入91—108小節,在結束部的材料之上進行發展,結束部兩個階段的材料均得到擴展,調性經歷了“c小調-f小調-#f小調-D大調”轉變;其二為展開部第二階段109—128小節,將主部材料進一步發展,并在過程中逐漸強調主部主題的后半段材料的變化,調性經歷了“D大調-g小調-c小調-f小調”的轉變;其三為屬準備129—138小節,低聲部的屬持續音為再現部的出現做調性準備。需要注意的是,這一部分仍延續了主部主題材料。
再現部為139—233小節,變化再現。主部為139—146小節,規模上有所縮減,原本的4小節補充被刪去;連接部為147—160小節,結構上并無變化,仍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節奏型發生變化;副部為161—211小節,結構上無變化,第一副部的調性于c小調上呈示,直到第二副部調性才回歸主調C大調,這成為判斷該樂章為奏鳴曲式的主要依據;結束部為212—217小節。在其之后增添了具有幻想風格的華彩段,最終在233小節于C大調完全終止。此后進入尾聲,為第233—257小節。
(二)動機、主題分析
動機一般為含有一個節拍重音的短小片段,而主題往往是一個樂句,在調性、旋律表達上具有一定的完整性。樂章開頭即出現了十六分音符do-re-do的一個二度級進,將該動機視為X。主部主題旋律簡練,力度對比明顯,震音、頓音等修飾音的運用加強了主題的動力感,這種力度與節奏的變化正是貝多芬所喜愛的張力感。連接部第一階段以十六分音符為主,快速在主調上經過;材料X在第二階段的高聲部和低聲部再次出現。進入副部主題,柔美、線條性的旋律開始陳述,即使存在切分導致的重音錯位,但旋律的線條感仍然能夠感受到,第二副部出現dolce(甜美的、柔和的)音樂術語,使女性化的聽覺更加明顯,材料X在旋律伊始便出現。結束部的第一部分將材料X與連接部中的顫音結合運用發展;第二部分則是運用了連接部材料。在展開部的發展過程中,愈能看出主題式發展在貝多芬這首鋼琴奏鳴曲中的運用,筆者將呈示的主題一一與展開部開始之后的發展對應:導入延續了結束部材料,這是一種常見的手法;展開部第一階段同樣發展了結束部材料;展開部第二階段發展了主部主題材料,并逐漸擴大、夸張主部主題動機的一個展開單元,形成流星狀;屬準備依舊是展開主部主題動機,并且動機X貫穿于整個展開部。
再現部整體并無變化。尾聲由主部主題開始,摻雜了連接部材料,更多是與開頭主部主題的呼應,強調主部主題的音響效果。從整體來看,主部主題在全曲大量運用,暗藏于主部主題中的材料X更是貫穿全曲。
(三)調性-和聲分析
全曲主調為C大調,整體呈現出T-D-S-T的調性安排,調性多為四五度關系調或同主音大小調轉換,符合古典主義時期調性變化,由主部開始在C大調上陳述,經過連接段過渡至g小調,再經過一個小連接進入G大調,兩個副部為同主音大小調,增加了調性色彩的對比,結束部延續G大調至呈示部結束。進入展開部,雖然延續了結束部的材料,但調性轉向了c小調,隨后又上行四度模進至f小調。展開部第一階段高聲部的分解和弦與低聲部的柱式臨時主和弦相結合發展,將調性不斷變化,第二階段的調性形成了一個等四度關系轉換:D大調-g小調-c小調-f小調。屬準備G音持續為進入主調C大調做準備。再現部由C大調開始,經過c小調和降A大調,最后結束在C大調。
第一樂章的和聲進行以主、下屬、屬、主為基礎,主-屬進行居多。主部、副部均以主屬進行開始陳述。展開部的和聲較為復雜,不過仍是有規律可循。引入部分兩小節為單位作模進,通過屬七和弦到主和弦的進行可判斷其調性。緊接著展開部第一階段高聲部的分解和弦與低聲部的柱式臨時主和弦相結合發展,和聲始終也并不穩定,第二階段同樣通過模進使和聲在不斷變化,終于在第139小節進行到C大調主和弦。華彩段與展開部第一階段相似,采用同樣的手法,終止處的主46和弦后接顫音的手法與莫扎特的鋼琴曲奏鳴曲、協奏曲如出一轍。如此看來,貝多芬早期的鋼琴奏鳴曲仍受到莫扎特的影響。雖然貝多芬此時的聽力狀況開始逐漸弱化,但不可否認他是一位技藝精湛的鋼琴演奏家,故第一樂章的結尾華彩段也是情理之中。
(四)音響分析
第一樂章為快板,且是大調性質,所以更具有活力,動力感十足。通過譜面可以觀察到力度sf(突強)音樂記號,甚至有些跟在力度p(弱)的后面,導致力度對比更加明顯,作曲家幾乎每次在十六分音符的八度同音跑動時均會加上f(強)或ff(很強)的力度記號,似乎要為這種快速跑動添上一股躁動、不安的情緒。力度上的對比是貝多芬喜愛用的一種音樂表現手法,如若聆聽一下第二樂章,這種對比會更加明顯。第二樂章的主題旋律由開頭的柔和的力度至中間突然被強奏出來,這種對比反差可能正是貝多芬想要的,這種情況在他的作品中也是屢見不鮮。
在節奏上,貝多芬同樣喜歡運用切分和休止,為音樂帶來動力感,其中最著名的莫過于“命運動機”,還有《悲愴奏鳴曲》第一樂章的引子部分等等。在《第三鋼琴奏鳴曲》第一樂章的第一副部,貝多芬通過切分和延音線將重音錯位,震音、頓音和顫音等修飾音符號也為節奏增添許多風味。
在織體上,半分解柱式和弦、十六分音符八度同音反復、均勻的半分音符分解和弦這三種為此樂章的主要織體,織體并不繁雜,旋律線條也較為清晰。
二、社會歷史分析
18世紀末,貝多芬創作出《第三鋼琴奏鳴曲》。雖然這是作曲家早期的一部作品,但已經展露出高超的作曲水準。啟蒙運動給歐洲帶來巨大沖擊,使社會發生深刻變革,通過提倡自由、平等的觀念,從而讓音樂不再只服務于教會、宮廷貴族,逐漸走入市民階層。作曲家身份的意識開始逐漸增強,此前的職責只是創作音樂,并且音樂作品幾乎均是獻給王室、教堂或上帝等,而貝多芬的這首鋼琴奏鳴曲則是獻給了自己的老師——海頓。1972年,貝多芬定居維也納并跟隨海頓學習作曲技術和音樂理論。《第三鋼琴奏鳴曲》在吸收海頓音樂風格的同時,也展現出另一位前輩——克萊門第(Muzio Clementi,1752—1832)的創作特點,如雙音、短琶音組成的經過句等等。時至今日,貝多芬仍然受眾多學者所研究,其作品中蘊含的人文精神和開創性的舉措是一大重要原因。
隨著作曲家身份的逐漸確立與完善,作曲家漸漸地被神圣化,推向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反而導致西方音樂史書上主要圍繞“萬神殿”作曲家大費筆墨,并且將作曲技術的進步視為衡量作曲家歷史地位的唯一標準。進入20世紀80世紀左右,“新音樂學”潮流興起,多種美學思想的提出,其中之一大轉變是將研究重心從作曲家移向了音樂作品,如達爾豪斯在其著作《音樂史學原理》中說道:“對于音樂歷史寫作而言,清除‘作品’概念的后果實際上是不可想象的。”作曲家通過作品想要表達的含義并不是作品本體意義的唯一答案。
接受美學最初是關于文學理論的研究,其主要思想是將文學作品的中心研究從作者轉向作品。但接受美學中所指的文學作品概念并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文學文本,僅僅單獨的文本是無意義的,需要讀者(聽眾)使之具體化,進而文本(樂譜)才具有價值,即強調讀者(聽眾)的主觀意識。這種思維方式在音樂作品的研究中同樣適用。文學作品與樂譜的區別在于,作者可以直接通過閱讀來了解其表達的內容,但一般的聽眾無法通過樂譜上的音符來獲取音樂表達的內容(除具有極強的內心聽覺的專業人士),音樂表演無疑成為作品與聽眾之間的重要環節。由此,對于作曲家音樂作品的接受歷史考察成為詮釋的另一大重要維度。一個尤為典型的例子是英語世界1980年版與2001年版的《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詞典》之間的對比,前者所有的作曲家詞條均未專門列出“接受”(reception)內容,而后者在許多重要作曲家辭條中加入了這部分內容。如今,在各大音頻、視頻軟件上以貝多芬的《第三鋼琴奏鳴曲》為關鍵詞,就可查詢到不少著名鋼琴家對這部作品的不同演繹。作品中華麗的演奏技巧和英雄主義的氣概,不僅吸引了鋼琴家,也吸引著聽眾。相較于貝多芬其他作品,這部作品沒有非凡的號召力,如若將目光轉向貝多芬更加精美絕倫的作品如《第九交響曲》,其中主題旋律《歡樂頌》的傳唱度稱得上家喻戶曉。國內擁有許多關于貝多芬音樂作品的研究文獻和著作,其中不乏含有接受史視角的研究,但將其與作品本體相聯系的文章數目較少,研究深度較淺,這仍是需要填補的空缺之一。
三、結束語
《第三“英雄”交響曲》的誕生標志著貝多芬進入創作的成熟時期,雖然《第三鋼琴奏鳴曲》在時間上早于前者,但是在這部奏鳴曲中已經初見作曲家的創作風格,比如頻繁的節奏變化、力度的強弱對比、豐富的音調,華彩段營造出的鳥鳴聲、作品開端的號角聲等。在這部鋼琴奏鳴曲中,展現出貝多芬宏大的交響性思維,并試圖在鋼琴上制造出樂隊的效果,結束部后的華彩段即是證明。此外,這部作品的許多因素來源于貝多芬的《C大調“青年”鋼琴四重奏》。貝多芬不僅具有內涵豐富、可供專業學者研究與分析的作品,也適用于普羅大眾,如《致愛麗絲》等易于識別的旋律線條,這或許是貝多芬在國內接受度高的原因之一。國內外關于貝多芬其人其樂的研究著作、論文已經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而隨著新的美學觀念、研究視角的提出,以及大眾審美觀念的變化均會引起音樂作品的重新審視,不同時代之下的學者對作品均會有不同的闡釋,正是這種新的詮釋出現,才使得已被記錄在譜面的作品獲得了更多有意義的呈現。
參考文獻:
[1]范乃信.貝多芬密碼[M].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出版社,2013.
[2]于潤洋.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分析(下)[J].音樂研究,1993(2):15.
作者單位:浙江音樂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