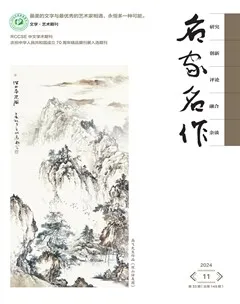影視敘事中的文化符號與身份認同構建
[摘 要] 影視敘事作為大眾文化的重要形式,通過對文化符號的選擇性再現,建構觀眾的身份認同。從符號學視角出發,深入剖析影視敘事中的語言、服飾、行為、空間等文化符號的類型及其表征特點,揭示文化符號依托記憶強化情感、借助想象塑造自我、突出差異確立他者、重塑秩序協商身份的建構機制,進而提出影視敘事挖掘本土資源、融合多元元素、關注邊緣訴求、直面認同困境的文化身份建構策略,以期為新時代影視文化創作注入文化自覺,為觀眾文化身份構建提供精神資源。
[關 鍵 詞] 影視敘事;文化符號;身份認同;建構機制;建構策略
影視敘事作為重要的文化生產方式,肩負著傳承文明、塑造價值、引領風尚的使命。在全球化語境下,影視敘事日益成為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因素交織中,折射出復雜的身份認同訴求。當代中國正經歷從“差異性他者”到“話語平等主體”的身份重構,需在影視敘事中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從容借鑒吸收外來文明有益成果,在繼承與創新、堅守與開放中努力構建中國特色、世界表達的當代民族-國家身份認同。
一、影視敘事中的文化符號類型與表征
(一)語言文化符號的敘事呈現
語言文字是影視敘事最基本的文化符號,銀幕內人物使用的語言文字直接指涉其身份屬性,如使用普通話、方言還是外語,從而體現人物的地域文化歸屬;使用正式、隨意還是諧趣幽默的語體,透露其性格氣質、教育背景等。畫外音解說所用的語言會反映創作主體的文化立場,如運用何種語言講述中國故事,折射“誰的話語”主導敘事,字幕、話語權、翻譯腔等呈現方式也能體現文化話語權力關系,如好萊塢電影常借助英語字幕再現異域文化,體現西方中心主義傾向。國產科幻片中的“翻譯腔”,用以折射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中的語言自信問題。語言文化符號往往通過紛繁復雜的敘事手段呈現,既塑造個體身份,又反映群體關系,所以我國影視敘事需立足本土語言文化,講好中國故事。
(二)服飾文化符號的敘事再現
服飾是影視敘事塑造人物身份的重要文化符號,人物穿著的服裝、佩戴的飾物等會指涉其職業特征、階層身份和性格氣質。如名媛的華服珠寶,彰顯其顯赫的階層出身和奢靡的生活方式。服飾變遷也會折射時代變遷和價值變遷,如女性從旗袍到工裝的轉變,再現知識女性從傳統家庭角色走向社會獨立角色的歷程。影視敘事對服飾的選擇性再現,也能體現創作主體的文化訴求,如渲染旗袍的東方神韻,彰顯民族國家認同;關注草根階層的粗布衣,體現尋根文化訴求。影視敘事對服飾文化符號的運用,不僅能塑造個體身份認同,也會折射時代價值取向。我國影視敘事應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服飾符號資源,進而彰顯民族特色、引領時尚風潮。
(三)行為文化符號的敘事建構
儀式、禮節等行為方式蘊含著群體的價值規范,而影視敘事也是塑造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特定行為能呈現個體對群體價值觀的遵從和內化,如三跪九叩、灑掃應對等體現儒家“名分有序”的價值規范;行為方式也會折射個體的身份認同傾向,如《霸王別姬》中程蝶衣行路坐定、言談舉止極盡女性柔美,表達其對戲曲生命的絕對忠誠。影視敘事也常以行為沖突再現不同文化身份間的碰撞協商,如《喜宴》通過男同性戀者與華人傳統家庭間的矛盾,折射出美國個人主義文化與中國集體主義文化間的觀念沖突。因此,影視敘事對行為文化符號的運用,既能塑造個體價值追求,又能體現群體觀念形態。我國影視敘事應立足優秀傳統行為規范,既要彰顯立身處世的文化價值,又要體現時代精神、兼容多元差異。
(四)空間文化符號的敘事營造
空間景觀中寄寓著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念,影視敘事是塑造文化身份的重要領地,影視景觀直接指涉地域文化特征,強化地緣認同,如紫禁城的莊嚴端莊彰顯北京的帝都文化,上海外灘萬國建筑再現海派文化的包容開放。空間也承載著主體的情感寄托,由客觀景觀轉化為主觀意義空間,反映了主體的價值追求,如《霸王別姬》中程蝶衣的舞臺與更衣室,由戲曲表演的客觀空間轉化為其生命存在的主觀家園。影視敘事對特定空間的聚焦,凸顯創作視角和文化立場,如聚焦民族地標建筑,彰顯愛國情懷,關注底層民眾生存空間,表達人文關懷。影視敘事通過對空間文化符號的選擇性再現,既能塑造地域認同,又能表達主體訴求。因此,我國影視敘事應立足多元地域文化資源,因地制宜打造承載民族記憶、彰顯時代精神的銀幕空間。
二、影視敘事中文化符號的身份認同建構機制
(一)依托文化記憶,強化情感認同
文化記憶是一個群體對其獨特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的集體回憶,影視敘事通過選擇性地再現與民族、國家命運相聯系的重大歷史事件、風物人情,能觸發觀眾的集體記憶,從而喚起其對民族文化的情感認同。通過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再現,將個體身份與民族國家的宏大敘事相聯結,能喚起觀眾對民族苦難輝煌的共同體驗,如《建國大業》以開國大典、香山臥底等為歷史坐標,再現民眾的家國情懷。影視敘事也注重在歷史宏大敘事中穿插市井風情,讓觀眾在鮮活的文化細節中喚起溫情記憶,如《芳華》在特定語境下講述民兵連知青的青春成長,特定記憶被個人化、柔性化。影視敘事依托群體的文化記憶,建構國家、地域、個人身份間的情感聯結,增強觀眾對本土文化的認同黏合力。我國影視敘事應進一步增強文化記憶意識,在歷史與現實、宏大與微觀的互文中唱響中華文化的時代主旋律,著力發掘承載民族情感的重大歷史題材,用主流價值觀詮釋歷史,凝聚國人對偉大復興的情感認同,如《建黨偉業》呈現中國共產黨革命史,強化人民群眾對黨的擁戴。此外,要關注不同群體、階層的文化記憶,呈現個體命運與國家命運的同頻共振,試圖用文化多樣性守望國家認同的大一統,如《人世間》呈現南北差異的市井風情,彰顯了普通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二)借助文化想象,塑造自我認同
文化想象是對未來理想生活圖景的憧憬以及對本民族文化未來的理想期許,影視敘事塑造文化身份,不能僅僅立足過去,更要放眼未來,以文化想象托舉國民的自我認同。影視敘事為觀眾提供了一個理想的“鏡像”,觀眾在對銀幕人物的認同中,能實現自我身份的“反身性”建構,如《紅海行動》塑造了無私奉獻、舍生忘死的國家英雄形象,引發觀眾對自我價值的思考。影視敘事通過營造出民族文化的理想圖景,讓觀眾在跨越現實局限的想象中體驗文化認同,如《流浪地球》超越當下困境,營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愿景,彰顯中國擔當。影視敘事以文化想象為翼,實現個體自我認同與集體理想圖景的對接,為文化身份注入理想主義的激情。我國影視敘事應積極借力文化想象,為國民提供自我認同的精神高地和價值指引。要立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塑造新時代民族英雄形象,引領國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如《攀登者》塑造不畏艱險、為國爭光的登山英雄形象,激勵新時代青年奮發圖強,著眼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要塑造人類理想未來的宏大愿景,展現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引領人類文明進步潮流,如《上海堡壘》表達了人類攜手抗擊外星侵略的理想圖景。
(三)突出文化差異,確立他者認同
文化身份建構往往以“差異性他者”為參照,通過強調本民族文化的獨特內核,彰顯文化自尊,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和認可。影視敘事對文化差異的再現,為國民提供了“向外看”的世界想象,影視敘事通過對異質文化的再現,強化觀眾的文化“我群”意識,如《花木蘭》對比中西武士精神,彰顯東方文化的仁義觀。影視敘事從差異中尋求對話的可能,在碰撞中完善文化自我,如《龍門飛甲》呈現東方功夫與西方機關槍的對決,表達在民族危亡時刻放下成見、攜手抗敵的人道主義訴求。影視敘事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再現,也警示我們在文化交往中要尊重差異,以平等包容的姿態實現“和而不同”,如《喜宴》呈現華人移民面臨的文化認同危機,引發觀眾對多元文化并存的反思。影視敘事以差異構建身份,既彰顯本民族的文化自尊,又以“他者”為鏡鑒己,在對話交流中完善自我。我國影視敘事應進一步增強文化自覺,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心態看待文化差異,在平等對話中彰顯大國風范,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煉體現中華文化獨特內核的價值符號,以文化自信姿態展現國際形象,如《孔子》《梅蘭芳》書寫體現儒家思想、京劇藝術神韻的文化名人,令世界重新審視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
(四)重塑文化秩序,協商身份認同
文化秩序是社會各群體協商的結果,當現有文化秩序無法調和各群體矛盾時,影視敘事往往通過顛覆舊秩序、重塑新秩序,引導觀眾在新的文化權利結構中獲得身份認同。影視敘事直面文化沖突,揭示既有秩序的弊端,為重塑秩序積蓄力量,如《讓子彈飛》通過黑色幽默揭示軍閥割據時期的混亂無序,展現出革命正確性的時代趨勢。影視敘事為觀眾提供了理想的文化權利結構,引導觀眾在新秩序建構中實現身份認同,如《集結號》塑造敢于犧牲、不畏強敵的革命英雄形象,引導觀眾認同革命力量對舊秩序的顛覆。影視敘事在重塑秩序的同時,也注重呈現不同群體在新秩序中的協商博弈。
三、影視敘事中文化符號的身份認同建構策略
(一)挖掘本土文化資源,彰顯民族身份認同
影視敘事建構文化身份,必須體現文化自覺,立足本民族悠久燦爛的文化積淀,善于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提煉文化符號資源,凸顯民族性,培育家國情懷。要著力建構民族文化的集體符號,增強觀眾對國家的象征認同,如《建軍大業》《建黨偉業》等主旋律影片頻繁出現五星紅旗、黨旗等符號,建構革命歷史的宏大敘事,引發觀眾的民族自豪感。善于從神話傳說、歷史故事中提煉凝結民族性格的符號,如《花木蘭》對巾幗英雄的刻畫,彰顯忠孝節義的民族品格。立足名勝古跡,表現家國情懷,如《長城》以雄偉的長城造型凸顯中華民族的歷史感和使命感。注重在傳統節日、民俗風情中體現鄉土情結,如《紅高粱》用高粱寓指故鄉山東的紅色記憶。
(二)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構筑包容性身份認同
在全球化時代,影視敘事應以更加開放包容的胸懷看待異質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交織對話中捕捉共通價值,塑造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身份,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超越文化隔閡,彰顯中國擔當,如《流浪地球》表現世界各國聯手應對全球危機,彰顯人類休戚與共的共同體意識。在異質文化的交鋒中完善自我,如《龍門飛甲》以東方武士抗擊西方侵略者,既凸顯東方功夫的獨特魅力,也體現中華文化兼收并蓄的開放品格;以多元文化并置反映差異性訴求,如《海上傳奇》通過中西建筑、服飾、習俗的多元呈現,凸顯海派文化的包容性。以跨文化視角關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如《太平輪》呈現中外乘客在危難時刻休戚與共、患難與共的人性光輝。影視敘事在堅守本土立場的同時,要以海納百川的文化自信融合多元,在文化交流互鑒中構筑人類命運共同體,引領人類文明進步。
(三)關注邊緣群體訴求,呼喚弱勢身份認同
影視敘事作為大眾文化載體,要體現以人民為中心,關注邊緣群體的生存狀態和情感訴求,以同理心喚起社會對弱勢群體的關切,為其爭取應有的文化話語權。以草根視角再現底層民眾訴求,如賈樟柯電影關注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的生存困境,為邊緣群體發聲;以女性視角反思男權文化,如《嘉年華》聚焦未成年女性遭受性侵,引發對男權文化的反思。以移民視角透視文化沖突,如《喜宴》再現華人移民在異國的文化認同困境,呼吁多元包容。影視敘事關注邊緣群體,呼喚弱勢群體身份獲得社會承認,在再現邊緣群體命運的同時,要以同理心引導觀眾反思文化權利結構,在多元共生中實現文化自覺。
(四)直面文化身份困境,探尋認同解決之道
當代中國正經歷社會轉型,新舊文化交織、價值多元分化,個體在不同文化場域間游移,影視敘事要敢于直面困境,引導觀眾在反思文化身份困境根源的基礎上,探尋文化認同的出路。通過再現時代變遷引發的認同沖突,如《芳華》聚焦知青的身份重構,既呈現認同迷失,也指明新的出路;直面全球化語境下的身份焦慮,如《世界》通過小鎮青年追逐出國夢,反思全球化浪潮下民族文化的失落;聚焦信息時代的虛擬認同問題,如《網絡謎蹤》警示網絡時代虛擬身份認同的迷失;關注個體化進程中的原子化困境,如《小偷家族》透過邊緣家庭的生存,反思個體化進程中親緣紐帶的瓦解。影視敘事要在再現困境的同時,引導觀眾從家國情懷中汲取文化認同的力量。
四、結束語
文化身份認同建構是全球化時代影視敘事的重要議題,本文基于符號學理論,剖析了影視敘事如何通過語言、服飾、行為、空間等文化符號,依托記憶強化情感認同,借助想象塑造自我認同,突出差異確立他者認同,重塑秩序整合多元認同的基本機制,進而提出影視敘事挖掘本土資源、融合多元文化、關注邊緣訴求、直面認同困境的身份建構策略。
參考文獻:
[1]朱斌,張雅清.身份與認同:非遺紀實影像的“記憶之場”構建[J].天府新論,2023(3):131-137.
[2]先勇.當代影視劇中的蘇東坡形象及其美學內涵[J].南腔北調,2023(3):52-61.
[3]彭紅艷,胡安江.中國網絡文學國際傳播的視覺化研究:文化邏輯與運營機制[J].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32(1):68-80.
[4]柳耀杰.虛擬現實技術在影視敘事中的應用與未來展望[J].文苑,2023(34):103-105.
[5]李陽.新農村影視敘事中干部典型形象及其成長演進[J].新世紀劇壇,2022(5):54-60.
作者單位:上海立達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