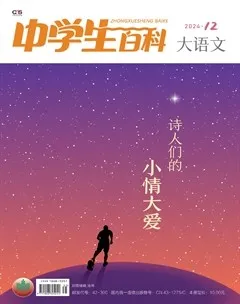燃燒是時間里的顫動
有人說,聞一多是歷史中的血肉,是歷史中最生動昂揚的部分之一。在他兒子聞立鵬創(chuàng)作的油畫《紅燭頌》中,也有相同的敘述。畫中的聞一多頭發(fā)蓬松,蓄長須,叼煙斗,眼神犀利,作扭頭凝視狀;背景是層層疊疊的紅、層層疊疊的火焰,有恣意燃燒的紅燭鑲嵌其中。你能看到他身上心上那種至死不變的倔強與斗志,就像那些在風中飄搖的燭光,它們燃燒,絕不是為了等待熄滅,也不會熄滅。
事實上,除了最廣為人知的《紅燭》,聞一多以生命闡釋的“紅燭精神”也潛伏于他另外的作品中,比如這首《一句話》。詩中的每一行每一句也都是燃燒著的,又或者說隱于背后的詩人是燃燒著的。如果不能理解和體會這種燃燒,我們就讀不透聞一多,讀不透他身上那種悲劇性的英雄主義。
這首詩寫于1925年至1926年間,是他回國后愛國主義詩情的結晶之作。他哀嘆山河破碎、國弱民窮,胸中積郁難平,似有一團火躥出來。這團火是什么?是割舍不掉的愛,亦是抑不住的“愛中之恨”。這種愛恨赤足游走于他的精神高地,步步真切,然后又在彼時的中國和理想的中國之間久久回蕩。
全詩節(jié)奏短促,詩人仿佛一刻也不能再等。而他想要說的“一句話”,也在激越的語境里幻化成矛。這句話是什么?他不直接說,而是圍繞這一題旨,運用大量隱喻發(fā)散、延展。“說出就是禍”點明黑暗時局中革命星火面臨的打擊和鎮(zhèn)壓;“能點得著火”則暗示民眾的不滿和反抗,且這些情緒已然累至時代的岸邊,即將排山倒海。鐵樹可無花,但火山不會永遠沉默,青天終會響起霹靂。至此,詩人寫下堅定信念——中國,是“咱們的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中國。
我們在這首詩中讀到了《紅燭》之外的聞一多。其實,他本身就是一支紅燭。在沒有紅燭意象的詩作里,他繼續(xù)燃燒,始終燃燒。朱自清也說,他是一團火,照徹了深淵,燒毀了自己。這種燃燒,是時間里的顫動,生命里的顫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