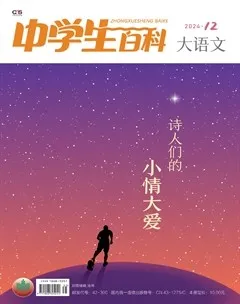不愿聲張的美好
2024-12-14 00:00:00夏魚
中學生百科·大語文 2024年12期
有太多的人,讀林徽因的詩,總小心翼翼,一點點地,輕微而又細膩地去撫觸其中的意境,仿佛面對的是待在風里又待在荷葉草尖上的晨露。美是美的,卻美得讓人不敢聲張,生怕驚擾,又或是不愿聲張,擔心被人分享去了。讀她的《你是人間的四月天》如此,讀這首《山中一個夏夜》亦是如此。
林徽因也被讀成了柔軟、詩意的女子,全然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小情趣里。大家在她的詩里感受歲月靜好。可是,從風云變幻的年月走來,走過張裂與泥濘,走過槍聲與炮火,也走過生命本身的苦痛與折磨,一個與時代共脈搏的女子身上,又哪有那么多的歲月靜好?所以,我們讀林徽因、讀她的詩,或許只讀到一半。
從人生價值的追求和實現講,她首先是杰出的建筑師,然后才是詩人。她愛好文學,不過是業余所喜。但是,對于中國古建筑研究,她一開始就是當作一種近乎神圣的事業來獻身的,并將這份熱愛視為超越生命的信仰。她自然也愛她的祖國,哪怕目睹了種種殘破。抗日戰爭后期,一位老友去了美國,有人說他不會再回來了,她卻正色厲聲地說,他一定回來!這不僅反映了她對朋友的了解,也反映了她自己的心聲。1948年,她在冷落中等待,有人勸她出國,她終是搖了搖頭。
很難想象,她的詩會與畢生所愛所求毫無牽絆。所以轉換視角再讀,在《山中一個夏夜》中,我們是不是也能讀到她在深得沒底的黑夜中的祈禱與盼望?在夏夜里活過來的松林、流水、石頭、風與夢,它們在窺探一縷終將醒過來的晨光嗎?她把對腳下大地的摯愛與初心、對美好的向往,寄于草木,寄于山河,寄于細碎又微妙的溫情事物。這種愛與盼,在她的詩里生根,也在她心上生根。
在劇變的年代里,在戰亂硝煙中,她于有機會靜下來的夜里,點一燭清香,擺一瓶插花,隨清風拾掇靈感,一點點地,不緊不慢地,吟詠人間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