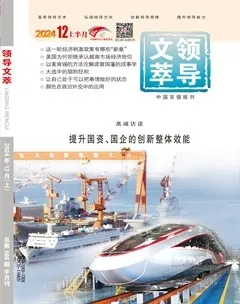載灃:正常的失敗者
政治斗爭,有勝便有敗。失敗者安靜退場,本是正常之事。但在中國歷史上,少有平心靜氣的失敗者,多的是懷恨陰謀的復辟者。民國時期,被推翻的滿族權貴中就出了一些復辟者,但滿族的復辟運動動靜很少,幾乎可以忽略。究其原因,從滿族自身來說,除了長期養尊處優導致素質退化,政治上難有作為之外,作為晚清政權領袖的隆裕、載灃二人的淡泊、豁達、與世無爭,是不可忽視的重因。
1908年,慈禧太后臨終前,設計了隆裕皇后和醇親王載灃共同掌權的政治格局。她這么做多半是出于私心,想把實權保留在葉赫那拉家族手中。但這一決定,影響了清朝的國運,也徹底改變了隆裕和載灃兩個人的命運。
隆裕太后時年40歲。在清人和民國的筆記中,隆裕既得不到慈禧的關懷,又得不到丈夫光緒的愛,只能在后宮對坐枯燈,生活單調而枯燥。冷板凳一坐就是21年。關于隆裕的為人處世,經常出入宮廷的德齡評價她“個性溫和”“不愛管事”。至于軍國大事,她都推給了載灃處理,當起“甩手掌柜”。
和40歲的隆裕搭檔的是25歲的攝政王載灃。
光緒九年(1883)正月初五,愛新覺羅·載灃出生在北京宣武門內太平湖醇親王府。父親奕譞是道光皇帝的兒子,娶了慈禧胞妹為妻,所以既是慈禧的小叔子,又是妹夫。奕譞的一生,戰戰兢兢,謹小慎微。載灃很好地繼承了奕譞的作風,恪守家訓。長大后,載灃緘默少語,相貌清秀,不及中等身材。作為庶出的小兒子,載灃本來是和權力無緣的。但哥哥們不是早亡就是進宮當了皇帝,載灃成了事實上的最長子,9歲時父親去世,襲承了醇親王爵位。
胞弟載濤評價載灃:“遇爭優柔寡斷……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晚清時節,滿族子弟缺乏可用之才。榮祿、奕劻之下無人可續。慈禧不得不超擢年輕人上臺。你說滿族自私也好,趕鴨子上架也好,人家總不能眼看著祖宗的江山無人接掌,任由外人做主吧?于是乎,滿族年輕權貴粉墨登場。載灃登上政治舞臺,是在八國聯軍大亂后去德國“謝罪”,時年18歲。“德國本打算讓我父親見德皇時行中國式的跪拜禮,由于父親不答應,經多方交涉算是沒有再度丟臉。在見到德皇和在德國參觀后回到北京。這件事使慈禧覺得父親辦事有能力,更加重用他。”次子溥杰回憶道。1908年,光緒、慈禧相繼逝世,幼子溥儀當了新皇帝,載灃突然成了攝政王,“監理國事”。
溥儀的登基和載灃的上臺,帶有某種強烈的預兆。1908年12月2日,清朝最后一次登基大典。那天天氣奇冷。小溥儀被折騰了半天,等被抬到太和殿,再放到又高又大的龍椅上的時候,小孩子的耐性完全喪失了。溥儀放聲大哭。三跪九叩禮磕起頭來沒完沒了,小皇帝的哭叫越來越響。載灃急得滿頭是汗,只好哄他說:“別哭別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禮結束,文武百官竊竊私議起來了:“王爺怎么可以說什么‘快完了’呢?”“太不吉利了!”大家都垂頭喪氣地散去,覺得載灃的話給剛剛揭幕的宣統王朝罩上了不祥之兆。三年多后,小皇帝溥儀就宣布退位了,載灃的“快完了”成了一句讖語。
載灃在政治上乏善可陳。他和軍機大臣們同席議事,一切不敢自專,別人說什么都覺得有道理,就是提不出自己的主張來。往好了說是“監國性極謙讓”,往壞了說就是“無能”。無能也就罷了,載灃還不敢于任事。東三省總督錫良、湖廣總督瑞澂入見,陳述各自轄區的政務。載灃召對時只勞慰了幾句場面話,就說不出其他的了。瑞澂想向載灃匯報湖北革命黨的事,開口說了幾句,載灃就打斷他:“你的痰病還沒好嗎?”瑞澂馬上住嘴,不再說話。出使日本大臣的汪大燮屢次上書密陳日本政治動向,提醒載灃關注日本勢力的擴張,一直沒接到載灃的回復。汪大燮干脆趕回國內,請求面陳機宜。他對著載灃慷慨陳詞,載灃默然無語,最后提醒汪大燮說:“已經十點鐘了。”說完就讓汪大燮退下。
當然,作為攝政王,載灃在1909年到1911年間也不是什么事情都沒干。時代畢竟不同了,新情況、新事物不斷撲來,而載灃多少沾染了新觀念。在根子上,載灃肯定是希望大清王朝復興強盛的,也不反對洶涌時興的立憲思潮。他基本繼承了慈禧末年開啟的新政事業,繼續推動預備立憲。資政院、咨議局及其選舉,都是在這幾年搞的。只是載灃相信一點:執政者必須掌握大權,滿族親貴們只有大權獨攬,才能確保王朝長治久安。載灃無視地方分權、近代化開啟的國情,重用少年親貴,大力推行中央集權,反而激化了矛tt0TCxBS2M/CTX1L1MZILaMuhyQydhsw1wh3NEGjCzo=盾,加快了革命的到來。話又說回來,你讓載灃主動放棄滿族親貴的權利,奉送給漢族人,未免對他期望過高。清朝廷立憲的本意,就是鞏固皇權,用改革來對抗革命,絕非采納西方民主制度。
不可忽視的根本一點是,載灃執掌的清朝大船,早已經破敗不堪,積重難返了。再精干的舵手,都無力回天,更何況他這個不太稱職的舵手。
“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父親立即主動放棄了攝政王的地位,回家以后反而高興地對家人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說罷輕輕抱起了我。當時母親被他那種輕松的神氣氣得哭了一場,父親倒是心安理得地開始了新生活。”宣統皇帝溥儀回憶:“(母親)后來告誡弟弟,‘長大了萬不可學阿瑪那樣!’”“他對那三年監國是夠傷腦筋的。那三年可以說是他一生最失敗的三年。”
從1912年開始,載灃從高處跌落,過起了“退休生活”。載灃在清亡后的日子也過得很平淡,但他的心態很好,沒有郁郁寡歡,更沒有像隆裕那樣抑郁成疾。
載灃曾書對聯“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來明志。“溥杰回憶說:“父親本來是個淡泊的人,早晨起來向祖母請過安后,就到寶翰堂書房去洗臉吃早點,然后看書寫字。中午和母親一起吃午飯后,又到他的書房里繼續看書。到了吃晚飯的時間,回到內宅和母親一起吃晚飯,飯后又到祖母處問晚安。然后他們夫妻倆說些閑話,結束一天的生活。”
偽滿洲國成立后,載灃又成了“皇父”,平淡的日子受到了打擾。干擾主要來自日本人和偽滿洲國的“邀請”。對日本人的拉攏,載灃一概婉拒,不受利用。
溥杰回憶:“父親生前堅持不參預偽滿洲國事,只是短時間去看望過溥儀兩三次。他曾表示不同意溥儀當偽滿皇帝,因為溥儀不聽,氣得哭了一場。溥儀想把父親留在東北,他用裝病等方法堅持回到北京。”根據溥任先生回憶,他16歲時陪著父親載灃去長春看溥儀。“有一天晚上,屋里只有載灃、溥儀、溥任的時候,載灃語重心長地對溥儀說:‘別拿日本人當傻子,他們不傻。他們不會打下江山讓你坐,朝鮮就是個例子。古代的石敬瑭也是個例子。當這個皇帝沒意思,不如當個百姓,活得像個人。’載灃說完這話,神色怡然,仿佛放下了千斤重擔似的輕松。溥儀聽完這話,起身去拉門,還探出身子左右看了看,待關好了門,才悄聲對載灃說:‘往后您別再出關,弟弟妹妹們也別再出關,就是我請,也別再來。’”
抗戰期間,載灃先是避居天津,1939年遷回北京王府。1947年他利用王府屋舍,出資創辦了競業學校。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載灃遣散了王府的下人,開始著手解決醇親王府的善后。征得北京大學同意后,載灃把王府收藏的圖書、文獻等拉到北大,捐給了學校。接著,他賣掉了王府,得到了一億元錢(折合新人民幣一萬元),舉家搬到了西揚威胡同的一所普通四合院。整個院子有十幾間房子,載灃親手在庭院中栽了兩株海棠。載灃死于1951年2月,享年68歲,葬于北京福田公墓。載灃生前,在福田公墓購買了10個墓穴,或許有意讓家人一起安息于此。
(摘自《失敗者:被遺忘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