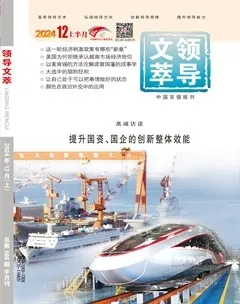造反的李淵為何卻“尊隋”

從太原到長安李淵的大局觀
大業十三年(617),李淵起兵時,他擔任的是隋朝太原留守,從大業十一年(615)開始,他就坐鎮山西了。李淵起兵的地方是太原,這里的太原指太原郡,郡治晉陽(今山西太原)。自北朝以來,晉陽就是北方軍事重鎮,是中原農耕區和北方草原地區的交替地帶,常年配備精兵良將,武器輜重無數,軍事戰略意義重大。
到了隋末,太原可謂四戰之地。當時的太原北有突厥以及后來割據馬邑(今山西朔州)的劉武周,東南有李密,南有歷山飛義軍,西有代王楊侑坐鎮關中。這種形勢對李淵起兵而言非常不利。
李淵當時雖為太原留守,手握五郡之兵,掌控著河東北部地區的軍政大權,但他的一舉一動都被隋煬帝的耳目所監視,手中也并無可以依靠的軍隊,李淵恐怕沒有太多心思去考慮帝王功業,更多的想法是如何在亂世洪流中保全自身。所以李淵在太原起兵前就向周邊勢力示好,一方面對突厥稱臣,與之結盟,另一方面則向李密通信示弱。
當時如許世緒、武士彟等勸說李淵割據太原自立,但因為太原是四戰之地,隨時都有被周邊的強大勢力吞噬的風險,故而需另尋他處作為穩定的后方和基地,保證自己不被周邊強大的勢力所消滅,自保之后再伺機爭雄天下。
李淵為何最終要選擇關中和長安呢?
第一,關中具有得天獨厚的軍事戰略價值,從軍事地理角度來說,關中這里號稱“四塞之地”,憑高據險,進可攻,退可守,是不折不扣的軍事戰略要地;第二,李淵謀劃起兵時,瓦崗軍正與東都的隋軍相持不下,無暇西顧;第三,李淵出身關隴貴族集團,李淵不僅熟悉關中地區,而且在關中也享有強大的政治資源;第四,長安是隋朝故都,也是關隴集團的大本營,以“尊隋”的名義攻取長安,就能贏得關隴集團的支持,為日后奪取天下奠定基業。
就當時的情況,關隴集團是隋朝統治賴以維系的基礎,隋煬帝過早與關隴集團決裂,導致隋朝的統治基礎迅速薄弱。所以,隋煬帝下江都以后,很多關隴集團勢力紛紛倒戈,他們迫切希望有一個新的領袖來重建關隴本位的政治秩序。
李淵決定攻取長安,并打出“尊隋”的名號,就是看到了關隴集團內部的政治訴求。李淵清楚,只要有了關隴集團的支持,就意味著日后奪取天下成功了一半。更何況,李淵自己的家族也是這個集團內的重要成員,他去拉攏關中地區關隴集團家族的支持,肯定更得心應手。
從歷史發展的眼光看,被稱作“群盜”的農民起義軍,的確是消滅暴隋的主要力量,但是他們只起到推翻舊世界的歷史作用,而建設一個新世界,則需要有宏大政治眼界和格局的人。關隴集團是當時最具政治影響力和號召力的門閥,歷史的勝出者極大概率是出身于這一集團內部。歷史的重任,最終落在了李淵的肩上。
大業十三年(617)十二月初九,李淵大軍正式攻克長安城。
入主長安的李淵并沒有忘記自己“尊隋”的旗號,對隋朝的宗廟、宗室以及代王楊侑都秋毫無犯。十二月十五日,李淵在天興殿擁立代王楊侑即位稱帝,遙尊遠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改元義寧,自己進位為唐王,以李建成為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
這也直接影響了后來的歷史書寫,以魏徵領銜的貞觀史臣在編撰《隋書》時,除了把隋文帝楊堅和隋煬帝楊廣列入本紀之外,也把隋恭帝楊侑列入本紀。我們一般說隋朝是二世而亡,隋煬帝是亡國之君,不過,按照官方話語主導下的正史記述,隋朝具有正統性的帝王應該有三位,隋恭帝楊侑才是真正的亡國之君。
“尊隋”的政治深意
在隋末群雄中,李淵在太原所舉之義軍,與其他群雄的義軍相比,有個非常鮮明的特點——其他各路群雄打出的旗號普遍是反隋,而李淵的旗號卻是“尊隋”。
當然,“尊隋”不是尊隋煬帝。隋朝的正統性還在,只要另立皇帝,就能實現“挾天子以令諸侯”,進而改朝換代。所以,李淵從太原起兵開始,就打出了尊立代王楊侑的旗號。
李淵剛剛攻克長安,就宣布“約法為十二條。惟制殺人、劫盜、背軍、逆者死,余并蠲除之”。“約法為十二條”的舉措,和當年劉邦進入關中“約法三章”極為相似。隋煬帝失盡民心就在于他的橫征暴斂、濫用民力,李淵一舉廢除了隋煬帝的暴政苛法,意味著隋煬帝的政治權力在關中徹底失效,也意味著李淵在向關中百姓以及天下黎民宣誓——長安的政權仍然是隋朝的,但卻是一個全新的政權,要一改往日對天下百姓的橫征暴斂,剔除一切苛法。
當時,文臣將佐還向李淵勸進,要他早日代隋自立,切不可學劉邦那樣不稱關中王,結果被項羽所制。聽完此言,李淵卻面色凝重,先是表了一番忠心,說:“舉兵之始,本為社稷,社稷有主,孤何敢二。”然后話鋒一轉,說道:“劉季不立子嬰,所以屈于項羽。孤今尊奉世嫡,復何憂哉。”李淵認為,劉邦之所以入關后還被項羽所制,關鍵原因并不是他不自立關中王,而在于他沒有即時立秦王子嬰為帝,如果有了秦王子嬰這塊旗幟,還怕不能號令天下諸侯嗎?還會被項羽所制嗎?
從北朝后期到隋末唐初,社會上一直都流傳有“李氏將興”“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言,其來歷一方面可能和周隋時期李賢、李穆家族的貴盛有關,也可能和道教李弘的信仰有關。隋末很多割據勢力都在借助“李氏當為天子”的讖言為自己的勢力構建合法性,并搖旗吶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密、李淵和李軌。
李淵早在太原起兵前就意識到讖語的重要性,并有意借此大作文章,史書明確記載:“帝(指李淵)自以姓名著于圖箓。”李淵之后打出的“尊隋”的旗號,以及入主長安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尊隋”的舉措,其實都是為了應和。
從李淵進兵關中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李淵對“尊隋”旗號的政治號召力的運用可謂爐火純青,李淵大軍在進軍長安途中得到不少民眾擁護。大軍的主要戰役其實都在渡過黃河之前,渡河之后關中地區可謂傳檄而定,所以,李淵大軍進駐到長安城下時才會擁有二十萬部眾,絕大部分是沿途各支勢力投靠而來的。
到這個時候,李淵想搞改朝換代已經輕而易舉。但是,此刻還不能操之過急,因為太上皇隋煬帝還在江都。他如果過早接受禪讓,就會顯露出自己的虛偽,并讓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時機很快就到了,義寧二年(618)三月,隋煬帝在江都被弒殺,宇文化及擁立秦王楊浩為帝。不久,王世充又在東都洛陽擁立越王楊侗為帝。到這個時候,也就不存在什么篡位之說了。
隋煬帝被弒殺的消息傳到長安,李淵慟哭,說道:“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然而,李淵的眼淚終究是廉價的,一切都是在為他改朝換代做輿論準備。隨后,隋恭帝楊侑封李淵為相國,加九錫和殊禮,這也意味著李淵做好了禪讓準備。
五月十四日,隋恭帝楊侑正式禪位給李淵;二十日,唐王李淵在太極殿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號義寧為武德,推求五行的運行屬土德,顏色以黃色為尊。
表面上看,唐承隋火德,故為土德,色尚黃,這就是在昭示唐朝繼承自隋朝正統,這不存在什么問題。但實際上,唐之土德、尚黃恐怕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東漢末年以來,天下擾攘,長期處于南北對峙,一直到隋才實現大一統,所以唐朝所奉土德也可以理解為是直承漢朝的火德。對此,后來的唐玄宗就曾下詔,明確指出唐朝是承繼漢朝的德運,魏晉至隋朝皆非正統。
總之,隋唐之際,在政權合法性構建的問題上,李淵做出了一系列政治舉措,而這些都是在其“尊隋”旗號之下有條不紊地進行的,也是隱藏在傳統歷史書寫下李淵政治智慧和手段的體現。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