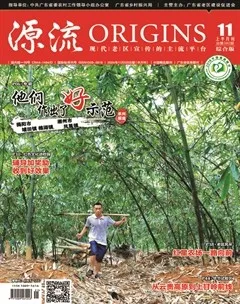要實事求是不容易
近日,筆者陪同馮活曉重返牛江鎮高聯村委會。望著在艷陽高照下田疇沃野的稻穗,馮活曉動情地說,水稻種植改革,才引來稻花香,引來糧食年年增產豐收。
2019年1月和3月,《源流》雜志和《華夏》雜志各以《馮活曉:再現40年前震動恩平的一段改革傳奇》和《恩平一段改革故事》為標題,刊登了恩平市知名企業家馮活曉在計劃經濟年代頂住上頭壓力,堅持“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從實際出發指導農民群眾發展農業生產并取得顯著成績的故事。馮活曉以安全抽穗期為節點插植水稻的理論與成功實踐,成為當地后來組織農民發展水稻生產的寶貴經驗。
馮活曉的水稻安全抽穗期理論與實踐是心血來潮的產物,還是他人指導的經驗?帶著問題,今年8月筆者再度訪問了今年已77歲高齡的馮活曉。事有湊巧,當年與馮活曉一齊在牛江公社工作且任公社黨委辦主任的梁奕基也在場,大家一起回憶往事,談笑風生。
1968年,馮活曉高中畢業返鄉務農,當了二年的牛江公社高聯大隊黨支部副書記。當他看到農民辛勤耕作仍食不飽腹時,內心很是感慨。就是想農民兄弟吃上飯這個原生動力,促使他更自覺地去讀書鉆研,尤其是讀一些來自國內外的科技書籍。其中,日本著名的水稻專家松島省三所著的關于水稻安全抽穗期的書籍令他大有裨益。
1977年,地區領導通過佛山地區種子公司撥給了牛江公社50斤名叫株26的稻種。一心想通過良種增產的公社書記即召集一班技術人員進行浸播。但個別技術人員只照本宣科,浸種后用谷蘿堆裝。馮活曉認為,穗上出芽的谷種浸后堆在一起是會引發高溫焗死芽的。但一些技術人員只憑發下來的“說明”去做,結果導致稻種絕大部份被焗死了。而馮活曉自己則要了一斤種子,浸后晾開,播種插植后收獲了二百多斤稻谷。公社書記因此事贊揚了馮活曉,批評了那幾個照本宣科的技術員。馮活曉的故事開始在牛江傳開。
當時由于不少地方基層推行大施化肥,甚至在高溫的中午時段也施肥,結果在高溫加化肥雙重高壓下,焗死禾的事例比比皆見。馮活曉頂住壓力,在他的駐點要求在傍晚太陽落山后才施肥,從而避免高溫燒死禾。結果,他到哪里駐點,哪里糧食就會大豐收。因此,年輕的馮活曉也成為當地種糧“常勝將軍”,以至于出現當地干部群眾爭搶他到駐點的趣事。
梁奕基告訴筆者,1975年馮活曉被安排到牛江公社最落后的平嶺村駐點。馮活曉不搞催耕催種,更不搞“階級斗爭”。在田頭調查掌握實情后,他耐心向群眾講述科學種田的道理。結果,當年由于氣候影響,恩平全縣幾乎都減產,唯獨平嶺村糧食產量實現倍增,不但一舉摘去長期吃返銷糧帽子,人均分糧超50斤,還能向國家上賣余糧。此事震驚了牛江公社,公社黨委辦即草成通報,發往全社。
但在“以階級斗爭為綱”年代,馮活曉此舉被領導扣上“只抓生產,不抓階級斗爭”的帽子,強令他檢討。直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馮活曉實事求是取得的成績才得到認同。他后來出任牛江區黨委副書記、區長和圣堂鎮黨委書記。憶起在牛江公社樁樁往事,馮活曉動情地說,實事求是說起來容易,實踐起來不容易,如果處處想到自己的利益和面子,就很難做到了。此話令筆者感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