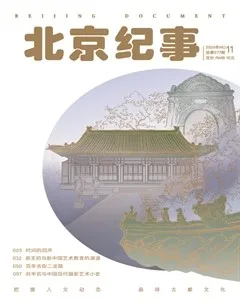一個家具展二十年守藝人
2022年9月16日,北京藝術博物館歷經五年的修繕,重新對社會公眾開放。與之同時,館內推出了五個全新的展覽,立足于館藏古代家具的《云落佳木:中國傳統家具展》便是其一。
本人作為展覽策劃人,從館藏二百余件古代家具中,根據樣式、種類、材質的不同,精選出47件藏品與9件散件,分別放入序、明式家具、清式家具和民國共計4個展廳中。力爭使廣大游客能感受到明式家具的凝練古拙,清式家具的繁縟奢華,以及民國時期家具在中西方文明交匯中的繼承與發展。希望通過展覽讓觀眾領略古典家具精良的材質、精巧的做工和深厚的文化底蘊,真正做到“讓文物活起來”。
但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館藏的這二百余件家具文物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物局統一調撥,一大部分均有殘損,以當時的狀態,無法直接將其作為展品對社會展出。長此以往,只會讓殘損進一步加重直至成為朽木。只有趁殘損還在可修復的程度時及時修復,才能做到文物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由此便引出了今天要說的主人公——劉金良師傅。
劉金良生于1967年,是通州人。1991年底進入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開始在報國寺進行大木作的修繕工作。1995年底,北京市文物局有一批家具亟待修復。這個工作被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承攬了下來,交由金良師傅以及劉金良師傅的師父——王希田老師負責完成。
據金良師傅回憶,王老師是1929年生人,河北衡水人,解放前在東曉市大街的興隆木器商行工作。當時的環境是前店后廠。前面的店鋪內,擺放著八仙桌、條案、圈椅、屏風等各類制作好的家具。店鋪后面便是制作家具的場地,店鋪伙計在后面既要加工制作各類家具,也會對殘破的舊家具進行修復。王老師自然也就學會了各類家具的制作等手藝,并重點學習了硬木家具的制作修復工藝。說到曉市大街,在當年可是很有名的。曉市大街位于天壇公園北側,西起珠市口,東至磁器口,全長2公里左右。當時在金魚池、魯班館、曉市大街一帶,大大小小聚集了四十多家木器作坊和店鋪,被稱為“家具街”,著名的龍順成家具廠、同興和木器店都在此處。到后來公私合營,王老師離開商行,進入故宮博物院工作,直至1989年退休。
1996年至1999年的這三年時間,金良師傅在王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百余件家具的修復。木匠行里有句老話,叫“老先生,少木匠”。這是說在木匠這行里,基本都是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因為從當學徒開始,用錛、鑿、斧、鋸進行刮、拉、鑿、砍,干的都是體力活兒。當年六十多歲的王老師,教導著二三十歲的金良師傅,在干活中學習。面對不同材質、不同類型的家具上,存在的不同殘損和問題,依次解決,將家具合格修復完成。
自2004年開始,金良師傅在文物古建工程公司的安排下,來到了北京藝術博物館,開始對館藏家具木器類文物進行修復。期間雖有幾年間斷,但截止到2019年最新一次的修復,已然有128件/套家具、木器類文物被修復。這里面包括了早至明代的亮格柜,晚至民國時期的辦公桌;大到三米多的落地鏡,小到巴掌大的木器座。
據金良師傅回憶,這期間印象最為深刻的,當屬一對漁樵耕讀紋飾的插屏板。
修復的這對漁樵耕讀紋飾的插屏板,長178厘米,厚4.3厘米,高258厘米。修復過程中為了保證其結實完整,并能長期對社會展示,用酸枝木恢復了邊框。兩個插屏板圖案對稱,為漁樵耕讀紋飾。屏心雕刻出山水間植被郁郁蔥蔥,右側一棵桃樹碩果累累。溪邊漁夫在垂釣,山腳下樵夫已經砍完柴火,滿載而歸。一農夫扛著鋤頭看向漁夫,涼亭內一書生正在閱讀。此紋飾在清朝較為流行,漁夫、樵夫、農夫與書生,代表了漁樵耕讀四個在農耕社會中常見的職業。刻畫的人物多為成年男性,配合青山秀水以及田園風光,借以隱喻古代文人追求的隱士情懷。
這對插屏板修復前的狀態很差。原有的邊框已經丟失不見,導致共計八條木板整體散架,并且長期以零散狀態保存又造成木板翹起、開裂、變形,以及部分缺失。
金良師傅說,修復家具類文物,確定好文物傷殘現狀后,一是要確定材料,修復的材料最好是和文物本身所用的材料一致。比如要修復的是件紫檀的家具,那么缺失部分修補的時候,也最好使用紫檀材質的。這對插屏板根據木紋、顏色,以及缺口的斷茬等特點判斷,為柏木材質的。二是進行修補過的地方,還是要遵循修舊如舊的原則。這樣整體看上去不至于那么突兀,而且也更能展示古代家具的特點與美感。但同時也要注意,修復不是造假。所以雖然修舊如舊,但也要保留能夠讓人近距離細看時能發現修補的痕跡。三是盡量少破壞、少干預。文物本身的歷史價值,以及歲月沉淀的美,是不可復制和估量的。修復時對于殘缺的部分,盡量去除糟壞腐朽的部分,然后修一下形狀,再根據修好的形狀,制作修復的配件,最大程度地保留文物本身。四是修復可逆。所有修復過程都是按照古代工匠的傳統做法進行,使用榫卯結構。需要填補拼接的地方,使用鰾膠進行粘合。這樣就算修復完成后再出現什么問題,也可以將修補的地方在不損傷文物的情況下拆下來重新修復。
第一步,是將八條木板用清水擦拭,先將表面的陳年老灰和污漬用布擦凈。板縫拼接處的舊鰾膠本已凝固干涸,附著在木板的兩側,用溫水反復涂刷后,逐漸軟化,此時再清洗就容易得多。
第二步是整形,將八條木板中所有發生形狀變化的地方都復原回去,同時開裂的部分要重新對齊拼好,使木板恢復平直的狀態。金良師傅先將單條木板放于平整的工作臺上,在木板下方加橫向的方木條,再用麻繩加“摽棍兒”將裂開的縫隙收緊。這里所說的“摽棍兒”,是指專門用來擰轉麻繩,使麻繩逐漸勒緊的短棍。圖中的這條木板左側變形較嚴重,于是金良師傅在木板左側上下均增加方木條,然后用卡子的一頭抵住底部的方木條,另一頭用螺旋扣調節,逐漸加力,在上下兩個方木條的合力之下,使木條慢慢恢復平直。遇到木板整體變形嚴重的,就得“大刑伺候”了。
第三步則是將殘缺的木板補全。為保證木材的一致性,本次修復木板所用的木材均為黃柏。先將殘缺部分的斷茬清理平直,然后把缺失的形狀在新材料上畫出,用鋸和刨子做出對應的形狀,用鰾膠粘合好后,依舊是用麻繩加摽棍兒來勒緊固牢。木板與木板之間拼接的拼口處,也要用刨子刨刮得十分平直才行,這樣才能使兩個拼面完全貼實,用鰾膠之后才會粘合牢固。將木板拼對好后,以原有的穿帶槽為基礎,新做了5根貫穿4條木板的穿帶。穿帶是“貫穿面心背面、出榫與大邊榫眼結合的木條”,其作用是防止木板拼接后發生翹起卷曲。側面看穿帶并非是正方或長方形,而是一端稍窄,一端稍寬的梯形。這種做法叫做“出梢”。出梢不可太大,如果一端過窄,使兩端的寬窄差異過大,那么穿帶會比較容易向寬的一端回竄。但也不可太小或者沒有,不然一來穿帶不緊,起不到應有的作用,二來會造成穿帶兩端都可進出,時間久了很容易松動。
下一步,便是將新補全的部分刻畫紋飾。這對插屏板雖說殘損嚴重,但萬幸的是其圖案是對稱的,并且一塊插屏板上缺失的部分,在另一塊板上剛好能對應上。于是金良師傅先將原有的圖案在紙上畫出來,然后再用拓藍紙,將圖案復刻到新補全的位置。通過長短粗細不同的刻刀,以減地浮雕和陰刻的手法,將圖案雕刻完成。雕刻過程需要集中精神,并且要很有耐心,要一點一點地下刀。畢竟如果一刀下得深了,傷到了不該刻掉的部分,則追悔莫及。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明清時期的家具極具個性化,在造型與裝飾上很多都是由買家訂做的,所以很難找到像修復的這對插屏板這樣完全相同的式樣照著做。在修復其他家具時,就需要金良師傅憑借著他多年的修復經驗,和對古代家具的時代特征、結構造型的理解,再對比各種家具圖錄上的圖片,找到相似的,最終設計出有理有據、合情合理的修復方案。必要的時候還會先用雜木做出小樣,放回到要修補的位置看看效果,再根據效果的好壞決定是再作調整還是正式動手修復。
雕刻完成后要進行打磨,一是把不平的地方磨平,二是圖案邊緣雕刻所留下的刀痕過于生硬,也要打磨光滑。打磨工具除了目數不同的砂紙之外,金良師傅還使用了古代匠人打磨拋光時會用到的木賊草。木賊草全株呈長管狀,節狀生長,每節中間是空的。表面有多道棱形凸起。將其與木材摩擦時,會起到打磨的作用。
為了讓修復好的插屏板更好地長久保存,金良師傅用酸枝木重新恢復了邊框,將穿帶的榫頭貫穿大邊。整體拼裝好后,上鰾膠固定,再用麻繩加摽棍兒整體勒緊。在等待鰾膠干透的時候,對新補全的部分進行做舊處理,最終修復完成,被展示于《云落佳木:中國傳統家具展》中的清式家具展廳中。
這一對“漁樵耕讀”插屏板的修復,前后歷經三個月才完成。北京藝術博物館的家具木器類文物,在金良師傅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中,共有128件套得以修復。它們在徹底損毀于時間的長河之前,被金良師傅一雙巧手,恢復了往日的風采,得以用于展覽對社會展示,或繼續在庫房得到良好保存。2021年6月,由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政府公布,北京市西城區文化和旅游局頒發“古舊家具修復技藝北京市西城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證,將其授予到以劉金良師傅為首的修復團隊。希望劉金良師傅能夠帶領修復團隊,將幾十年的修復經驗傳授下去,讓老手藝永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