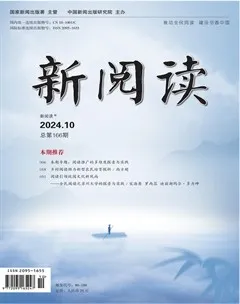喬傳藻兒童文學中蘊含的生態教育觀
生命意識是兒童文學研究的永恒主題,也是生態教育觀的重要體現。生命意識以生命為本位,關注人類及非人類生命個體存在的意義與價值。喬傳藻在他的兒童文學創作中,尊重兒童本位,將兒童解放到大自然中自由暢快地嬉戲玩耍。他關愛非人類生命個體,抒寫動植物生命之美,向兒童傳遞著自然生命的整體意識和人類自我的反省意識。喬傳藻通過在兒童文學創作中傳達生命意識,完成了對兒童的生態教育。
兒童文學與教育觀念的發展
在現代中國兒童文學走過的百年道路中,兒童文學發展理念經歷了三次轉型,分別是與世界兒童文學的接軌和學習、內容以兒童的生存與命運和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生存結合為中心及兒童文學逐漸以兒童為中心,兒童本位,為兒童服務。[1]因此,兒童文學的樣貌也不斷發生著改變。“兒童文學”的概念是由五四啟蒙思想家從西方譯介過來的。啟蒙思想家們發現了兒童,確立了兒童本位的兒童文學觀。這種本位思想強調兒童文學屬于兒童,要求作家以兒童為本位創造出兒童喜歡且能看的文學。于是,當時出現了一批尊重兒童、崇拜童心的兒童文學作家,如葉圣陶、冰心、王統照等。他們書寫自然,通過表現自然中的美好詩意來保持純凈無暇的童心。然而,基于中國20世紀前半葉動蕩的社會現實,兒童文學中的教育理念與社會問題有著緊密聯系。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兒童文學立足于“為人生”配合革命現實的需要,對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直到新時期以來,兒童文學再一次回到了“為兒童”的兒童本位。
魯迅認為過去西方對于兒童的誤解,是把他們當作是成人的預備,而中國人對于兒童的誤解在于把他們視為縮小的成人。但是,兒童的世界與成人是截然不同的。兒童既不是成人的預備,也不是縮小的成人。兒童是區別于成人獨立存在的生命個體。喬傳藻兒童文學創作中的兒童散發著生命的活力,富含自由的天性。他筆下的兒童在自然中得到了解放,獨立暢快地做回了兒童自己。
時代的進步及前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現代社會對兒童天性的壓抑日趨嚴重,部分家長對兒童過多的控制與要求導致兒童心理和生活壓力過大,生態教育便應運而生。生態教育樹立人與自然的整體主義。首先,它突出了人和自然之間的普遍聯系和互動作用,反對二元對立和一元價值觀。其次,它注重人的精神生態,強調對兒童深層心理進行教育。因此,對兒童的教育觀念必然是立足于具體的兒童發展實際。
喬傳藻兒童文學創作中的生態教育
基于“生態教育”這個詞語,生態批評學家提倡把生態學和教育學有機地結合起來,強調兒童對生態建設的參與。兒童教育者相信,引導兒童們到田野中去,可以促進生態教育的實施。他們鼓勵兒童親身體驗大自然,欣賞花草樹木的五彩繽紛,觀察動物們的生命活力,觸摸自然大地的肌理。這樣做,不但有助于兒童在早教中健康成長,還能提高他們閱讀文學的代入性和想象力。只有對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進行反思,才能找到解決生態危機的有效途徑。喬傳藻在他的兒童文學作品中,引導兒童輕松地、歡樂地走出課堂,走進自然世界,并從中獲得了審美的力量。
喬傳藻的兒童散文《醉麂》里面就包含了對生態教育的思考。年輕的女教師帶領著小學生們坐在綠絨毯似的草地上,盡情地歡唱。她會溫柔地將學生摟在懷里,愉快地給學生們打拍子。箐坡峽谷里水聲潺潺,一只小黃麂從山林跑出,孩子們張開手臂熱情地歡迎這位客人。女教師走在孩子們身后,她露出杜鵑花似的笑容。這幅其樂融融的景象不禁讓人聯想起《論語·先進》里孔子帶著眾弟子們到泗水河邊春游的故事。孔子要大家談論人生理想。曾點一邊彈琴一邊說他的理想是:暮春之時,能與青年朋友和兒童們結伴出游。大家在沂水中游泳,在河邊吹吹清風唱唱歌。孔子對曾點的回答表示贊賞,其原因就在于從山水之樂中,人們可以體味生命情趣,達到理想的人生境界。《醉麂》中女教師沒有局限于課堂的書本教育,而是引領學生們置身于大自然中陶冶情操。明媚的陽光、碧綠的草地、機靈的醉麂與充滿活力的兒童共同組成了一幅生機無限的生命圖景。在自然和諧的氛圍中,女教師完成了對學生的生態教育。
喬傳藻認為,在兒童的世界里,他們的想法都是能被允許的,他們的行為也是合理的。他們有一套較少受外界束縛的認知方式。兒童保留了人與生俱來的真實的性格特點,擁有掙脫束縛、憧憬自由的天性。相較成人,他們缺乏一定的自制力,克制不住嘴饞貪吃的天性。《吃算術》中,老師給趙小水做課后輔導。老師給了趙小水一把蠶豆,讓他把蠶豆分作三份,數清楚每份有多少。趙小水在數蠶豆的時候竟然把這些小豆豆都放到嘴里吃了。老師發現時,趙小水只好羞紅著臉說:“老師,你就教我數鵝卵石算了。”短短的描寫中,一個天真調皮卻不失可愛的頑童便躍然紙上。喬傳藻兒童文學中的兒童,想玩的時候就要玩得愉快盡興,有時甚至樂不思蜀、忘乎所以。他們在山場學校背后的栗樹林里打架干仗,在波光粼粼的響水河里徜徉,在古木參天的原始森林中穿梭。抓魚、摸蝦、打水仗成了他們的拿手功課。20世紀70年代的云南邊寨鄉村,保留了原始野性的氣息。喬傳藻筆下的兒童在這里獲得了釋放天性的原初活力。
喬傳藻筆下原始的云南生態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云南的土地為當地的兒童提供了生長的場所,棲居于不同大地上的生靈萬物,將潛移默化地受到了當地環境的影響。相比現代社會對兒童天性的壓抑,兒童在大自然中的活動,更益于他們心靈世界的發育。
成人有責任通過一系列的引導教育來塑造兒童的品德。稱職的家長會把豐富的人生經驗傳授給他們的子女。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把良好的道德品質灌輸給了后代。在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看來,兒童的道德觀全然有賴于自身的觀察、體驗、感覺與適當的引導。這些都是成年人應該予以提供的外部條件。洛克特別指出,家長必須引導兒童對動植物釋放出善意,培養孩子保持較高的道德水準。[2]如果沒有成人的教育引導,兒童缺乏正確的善惡觀念,可能會肆無忌憚地傷害和折磨那些落在他們手里的小生靈,并以此為樂。因此,兒童文學如何向兒童讀者傳達自然萬物的整體意識和人類自我反省意識,便是其生態教育的題中之義。
喬傳藻通過在兒童文學創作中對人與自然之間和諧關系的描述,進行著對兒童的生態教育。人與自然的這種關系如滄海一粟,被保留在現代文明社會的一隅,存在于邊遠的密林鄉村。西雙版納熱帶雨林里的大象,默默守護著原始村落里的鄉民,它們留下的道道腳印,震懾著豺狼不敢隨意出沒。(《野象谷》)身為護林員的“我”對一只野猴產生無限的掛念,因為我們彼此真誠用心的相處連接了不同物種的語言。幾顆香噴噴的炒蠶豆,一株株嬌艷欲滴的蝴蝶蘭,是我們友誼的見證。(《野猴》)音樂不僅僅是人類才懂得欣賞的藝術品,深山里的猴子也會被優美的琴聲所陶醉。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宇宙生靈整體之間都存在著普遍性和一致性的生命韻律?人與自然萬物天然同一,密不可分。(《琴猴》)春日溪澗,善良淳樸的孩童,乖巧懂事的小黃麂,共同構成一幅萬物有靈的生命圖景。小黃麂似乎知道自己不能在學校里盡情撒歡,便乖乖地坐在了學校的大門前,安靜地聽著老師給學生們上課。(《醉麂》)喬傳藻以滿含愛意的目光注視自然主體。他在兒童文學創作中將具有生命意識的對象范疇從人類兒童擴展到了非人類個體。他沒有帶著人類的優越感去俯視眾生,面對自然生命,他總是懷著敬畏和欣賞的眼光,與之平等交心。面對西雙版納熱帶叢林里生命力頑強的植物,他不禁感嘆:“‘打不死’啊,這就是你再生的秘密。你的信念正如你的根莖一樣頑強。我敬佩你!”(《打不死》)“盡管我不是佛教徒,站在你的面前,禁不住也要雙手合十了。”(《鐵心樹》)
敬畏生命是生態教育的基本道德原則。人類既然進化為思考型動物,就更加要懂得如何敬畏生命。人類應該去敬畏自然里每個獨立存在的生命體,宛如敬畏自己的生命一般。人類需要將共情的對象范疇從人擴展到一切自然生命體。獵人扎山看到扭角羚趴在草窩中給幼崽喂奶時,他放下了舉起的獵槍。(《黑眼圈》)生物系何老師見證了蟒蛇夫婦一里一外分工守護洞中的蛇蛋,喃喃道:“我們在這里做出的任何響動都是對大自然的褻瀆。”(《采集標本》)而自出生便生長于此的山林兒女們早已同自然萬物水乳交融。他們也更懂得如何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他們從不肆意掠奪,不恃強為大,從始至終都以赤子的心靈感悟自然,學習自然,用行動保護著自然。與生俱來的使命感讓他們倍感珍惜這些和他們同呼吸、共患難的生命。
喬傳藻筆下強烈的兒童生命
回顧歷史,人類的生命力往往只有自身與生態萬物置身于自然的生存環境時才能得到充分的釋放。自然環境能夠激活人的生命力量。喬傳藻對兒童形象的塑造,展示了人在自然環境中煥發的生命力。喬傳藻在接受《民生報》采訪時說過:“貧窮中的美麗是彌足珍貴的。”喬傳藻筆下的兒童生活在云南邊寨山區的原始密林里,擁有最充沛的活力和最自由的活動天地。他們宛如天地之間的精靈,無論是呈現的外在形象還是內在品質,都迸射出一種勃發的原始生命力。他們擁有健康的體魄,在大自然中學習到了生存的技巧和本領。他們把象耳朵葉折起來當杯子拿去舀山泉水喝,他們身手敏捷地爬到樹上采摘牛肚子果來充饑,他們熱了就跳進響水河里沖涼降暑。兒童們獨特的個性沒有受到壓抑與束縛。他們思想獨立,勇敢正義,富有探險精神。正是在這種原始生命力勃發的狀態下,他們在面對生活中的苦難時顯得愈發堅韌。
在相同的年紀,城里一些兒童被家長們眾星拱月般呵護著,享受無微不至的照料。而喬傳藻塑造的兒童形象,他們早已結束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階段。大自然促使他們迅速成長,也使他們具備了更加完備的生活能力以及豐富的生存技巧。這些兒童通過自我探索以及經驗積累,在大自然中鍛煉出了各種本領。
他們往往身穿青布衣褲,腰上斜掛長刀,背挎桑木硬弓。他們將象耳朵葉做成扇子,用長刀劈開攔路的刺藤,砍下一截金竹當作杯子。《箭蜜》中刻畫了一個原始生命力旺盛的少數民族兒童形象。其故事背景是喬傳藻年輕時上山下鄉做知青時的地點——西雙版納。這些兒童生活在滇南野霧茫茫的原始森林。懸崖峭壁、參天古樹、野生動物伴隨著他們成長。在大自然的孕育下,他們獲得了躍動的生命姿態。
昂揚的生命力使得喬傳藻筆下的兒童面對困境時顯得更加堅韌。當挫折和困難來臨時,作為孩童的他們也會猶豫和害怕,但憑借著過人的魄力以及堅如磐石的毅力,他們選擇勇往直前。在《鬼箐》中,基諾族兒童沙約遇到危險。他沉著冷靜、從容應對,順利解決了村民的心頭“大患”。沙約的表弟把家中的小牛犢給放丟了。為了小表弟不被責罰,沙約帶著黃毛獵狗便只身前往“克拉摳”山箐找牛。這條山箐的名字,翻譯過來便是“鬼的峽谷”。平日里,幾乎無人敢涉足這塊禁地。沙約始終只是個兒童,他也考慮過折返,知難而退,但他意外地遇到了將小牛犢吃入肚中的白花黑尾蟒。聯想起村里關于“山鬼”的傳言,沙約智斗大蟒,不僅破除駭人聽聞的傳言,而且幫表弟解了圍。
結語
生態教育為審美教育提供了指導,可以提高兒童的審美能力以及培養兒童的審美創造力。它能幫助兒童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審美。難能可貴的是,它還可以發揮出一些特殊的作用。比如,通過對自然的審美活動來表現出對非人類生命的關懷,保證人類的精神生態平穩發展,彰顯自然個體的生命光輝。對兒童來說,生態教育既為他們提供了參與解決生態危機的實踐途徑,又能培養他們的同情心和想象力,以及對生命的感受力。同時,生態教育也對兒童文學創作和兒童文學批評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喬傳藻創作著具有能喚醒人類生命意識的兒童文學,強調尊重兒童的發展理念,用兒童文學創作與生態教育展開對話,引導兒童身心全面發展。
作者單位:中共楚雄市委黨校
參考文獻
[1] 王泉根.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三次轉型與五代作家[J].長江文藝評論,2016(03).
[2] 付玉琪.生態批評視閾下的現代中國兒童文學研究[D].蘭州:蘭州大學,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