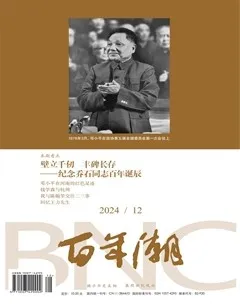我與陳翰笙交往二三事

在我眼中,陳翰笙是一位偉大而可愛的老頭。他有79年的革命經歷,而其中長達25年是從事地下工作的。引導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李大釗。直到1959年,他才公開了中共黨員的身份。他童心未泯,88歲時硬說自己28歲,90歲時說自己剛9歲,活了107歲又3天,2004年他逝世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哀悼。胡耀邦稱他“是個好老頭”。
陳翰笙老有教無類。劉少奇、陳云、宋任窮、童大林等受沖擊時,他們的孩子被稱為“黑幫子弟”,他就義務給這些孩子補習英語。我的朋友舞蹈家資華筠想出國交流,但不懂英語,翰老也收她為徒。翰老補習過的學生累計300多人,未收分文。我此前是一個初中語文老師,后來想從事文史研究,翰老認為我勤奮好學,對我有問必答,有求必應。我至今收藏有一摞翰老的親筆信函,他既有青光眼,又有白內障,這些信都是他在視力僅有0.02的情況下勉力寫出來的。

我初識翰老應該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當時還住在北京東華門一處四合院里。客廳中掛著他夫人顧淑型的畫像。他跟夫人于1919年相識于美國,報效祖國的共同理想使他們結為伉儷,相愛到白頭。1968年11月5日,顧淑型死于癌癥,翰老痛不欲生。此后每年夫人忌日,翰老都會靜坐一天。翰老無子女,我去看他時只有他的九妹陳素雅陪伴照顧。翰老是性情中人,談到社會上或官場上的歪風邪氣,氣得直哆嗦。這時素雅阿姨不停地撫摸他的胸口,連聲說:“哥哥,哥哥,別生氣!別生氣!氣壞身體無人替。”這種畫面我從未見過,所以清晰如昨。
翰老跟我說他原名樞,因為屬雞,《禮記》中把“翰音”作為雞的代稱,所以小名翰生。后來他在“生”字上面加了一個竹字頭,就變成了“翰笙”。他問我哪里人,我說籍貫湖南長沙。他說他對長沙熟悉得很,初中上的是長沙明德中學,高中上的是長沙雅禮中學。我說我中學上的也是雅禮中學。他笑了,又跟我說了一件趣事。“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知道“四條漢子”中有一位陽翰笙,所以要揪斗他。他忙辯解說:“我姓陳,不姓陽。”紅衛兵不信,他只得拿出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請柬證明身份,紅衛兵才散了伙。
我問及翰老1939年至1942年在香港的情況,他說當時主要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協助宋慶齡搞“工業合作運動”,動員了2.5萬多名失業工人,組成了1700個工業合作社,將經費用于支援抗戰。此前“工合”總部的很多貸款都撥到了國民黨統治區。他出任“工合”國際委員會秘書長之后,通過廖承志在上海銀行的一個親戚,把2000萬美金的捐款轉到了延安,他看過一張收據,簽收人就是李富春。他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創辦英文半月刊《遠東通訊》,第一次向國外報道了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的真相,在很短時間籌集了一大批物資,支援重建的新四軍。
翰老原來是第三國際成員,1935年才轉為中共黨員。他轉入中國共產黨是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和副團長康生,但他對這兩人印象都不好。當時王明讀了一份文件給他聽,他打斷王明,說其中有幾個詞不妥當。王明說:“這不相干,你聽我讀完。”他當時就感到王明自命不凡,盛氣凌人。康生問他:“誰是中國哲學史上的第一個唯物主義者?”翰老說:“是不是柳宗元?”康生說:“可以討論,可以討論。”當時康生交給翰老一個任務,讓他把巴黎《救國時報》的鉛字搬到美國紐約去,另辦一份《華僑日報》。1936年至1939年,他在美國的主要工作就是協助饒漱石辦《華僑日報》,聯絡海外華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
翰老是一位淵博的學者,一直把學術研究當作革命工作來干。在中國工業化理論,中國農村調查,南亞、非洲和太平洋問題研究諸方面,都有卓越貢獻。晚年,他除了負責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的“外國歷史”分卷(300多萬字)之外,還要顧及《人民公社》《土地改革史(1922—1952)》《保加利亞的農業改革》《蘇聯的農業機構改革》四部書的編撰工作。他強調,從事外國歷史研究必須服從時代要求,他舉例說,“現在我在跟非洲各國建立友好合作關系,但我們的歷史小叢書中,介紹非洲的就很少(當年只有一本《金字塔》)”。在進行農村經濟調查的過程中,他感覺到研究華僑問題十分重要。華僑不僅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進行了大力支援,而且西方文明有些方面也是建筑在華工的血汗之上的,所以應該把華工問題當成中國近現代史來研究,當成國際經濟問題來研究。翰老主編了一套《華工出國史料匯編》,皇皇十卷。他深有感慨地說,有些人口頭上整天掛著“無產階級”這四個字,但不關注中國第一代無產階級的歷史,這樣怎么行!翰老跟我談這番話時,這套《匯編》還只出了3卷,每卷只印了3000冊,直至1985年,該《匯編》才由中華書局出齊。在治學方法上,翰老特別反對形而上學。他說,“孔夫子”(指照搬舊傳統)加“老毛子”(指照搬蘇聯經驗)等于形式主義,這會害死人。
1980年8月間,我寫了一本《許廣平傳》,因為許廣平跟宋慶齡有交往,而宋慶齡又是翰老的密友,我就突發奇想,希望由宋慶齡為拙著題寫封面,請翰老轉達我的不情之請。翰老果然給宋慶齡去了信。當年9月15日,宋慶齡用英文寫了回信。譯文是:“親愛的朋友:我的右手再次受傷,所以手腕無法控制毛筆,關于這位作者的請求,我有一個好建議:廖夢醒是許廣平的好朋友,而且她寫的中文真的非常好。所以叫辛西婭·廖(即廖夢醒)為他寫是最適合的。她的地址是復興門外國務院宿舍七組三十八號。我相信,為許廣平做這件事,她會感到光榮的。匆匆,SCL(宋慶齡的英文縮寫)1980年9月15日。”

我清楚地記得,這封信是宋慶齡派身邊的工作人員送到翰老家的,沒有通過郵局。翰老閱后直接交給了我。我興奮得沒有對他表達謝意就騎車直奔廖夢醒大姐家。當年我住在復興門外,離廖大姐的宿舍很近。我到達時,她正獨自一人吃晚飯,表情既慈祥又嚴肅,因為我畢竟是一個陌生人,又一副風風火火的樣子。廖大姐接過信后只溜了兩眼,即刻放下飯碗,到書桌上寫了“許廣平的一生”這六個大字。這個書名是翰老改的,他認為比《許廣平傳》要好一些,理由我并沒有聽明白。1981年5月,我這本書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12月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再版。對于宋慶齡、翰老和廖大姐的這份恩情我將永志不忘。

因為研究魯迅后期的革命活動,我曾向翰老了解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情況,翰老說,1931年8月,蔣介石政府緝拿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宋慶齡用英文寫了一份抗議宣言,派他送到申報館,轉交《申報》總經理史量才。蔡元培也寫了一封保釋信,請他送交蔣介石的親信陳誠。但是36歲的鄧演達仍然被蔣介石殺害了。這件事,讓宋慶齡深感有必要組織一個團體,爭取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利。于是,1932年底,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宋慶齡任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魯迅等為執行委員。鑒于翰老的特殊身份,宋慶齡建議他不要正式參加這一團體,只秘密協助同盟開展一些活動。之后陳翰笙參加過營救牛蘭夫婦的活動,牛蘭夫婦是泛太平洋產業同盟的秘書,1931年6月以“國際間諜”罪被刑拘。宋慶齡為牛蘭夫婦聘請了一名瑞士律師,翰老負責在宋慶齡和這位律師之間傳遞信件。宋慶齡還通過史沫特萊跟翰老單線聯系,經常護送一些處境危險的革命者安全離開上海。目前有人質疑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歷史作用。我認為這個團體的確有中國共產黨、第三國際和蘇共(布)的背景,但同盟不僅營救過陳賡、羅登賢、廖承志等革命者,也為劉煜生、林惠元等被侵犯人權的普通人伸張過正義。正因為這個團體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構成了威脅,國民黨特務才暗殺了同盟的秘書長楊杏佛和《申報》總經理史量才。魯迅寫過一首七言絕句《悼楊銓》,可見同盟的歷史功績是不能抹殺的。
1982年12月底,我拜訪翰老時,談到自己參與編撰《魯迅大辭典》,其中就有介紹他的詞條。魯迅1927年7月7日致章廷謙信說:北新書局“已多出關于政治之小本子”,“陳翰笙似大有關系,或者現代派已侵入北新,亦未可知”。翰老1924年從德國留學歸國,即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擔任教授,時年27歲。因為他是歐美留學生,曾為《現代評論》周刊撰寫國際問題評論,被魯迅的論敵陳西瀅稱為“吾家翰笙”,故魯迅把他跟陳西瀅統稱為“現代派”。翰老跟我解釋說,“這是一個誤會”。他那時在北大任教,1925年3月,李小峰創辦北新書局。李小峰原是北大學生,又是北大新潮社成員,希望翰老寫點外國歷史讀物,翰老認為,學術專著的讀者面小,不如多出版些普及讀物,于是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國際新局面》,另一本叫《人類的故事》,交北新書局出版,每本3萬字左右。他在《現代評論》發表文章,跟北新書局毫無關系。
翰老補充說,1932年1月28日淞滬戰爭爆發,他從日本回到上海。有一次在上海郵政局的一個大廈跟宋慶齡秘密會晤,魯迅也在場,跟魯迅僅此一次會見。至于他對魯迅的間接了解,主要是通過兩個人,一個是史沫特萊,一個是茅盾。史沫特萊跟魯迅和翰老都熟。茅盾曾到他北平東華門大街的寓所來談過魯迅的事情。此外,1951年1月底,他在北京飯店參加宴會,旁邊兩位女性:一位是許廣平,另一位是楊之華。這就是他跟魯迅全部直接和間接的關系。魯迅跟宋慶齡曾秘密會見,我是從翰老這里初次聽到,魯迅日記中并無記載,但我相信翰老的說法。魯迅在《華蓋集續集·馬上日記》中寫道,他的日記“寫的是信件往來,銀錢收納,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魯迅會見紅軍將領陳賡,是確鑿的史實,同樣也未寫進日記,否則就談不到“秘密會見”了。
翰老給我留下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在中國文化中,有一種“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的傳統價值觀,但翰老不這么想。1951年,周恩來總理請他吃飯,動員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長。翰老對周總理說:“你今天請我吃中餐,我用慣了筷子、調羹,吃起來很痛快,如果請我吃西餐,我用不慣刀叉,那就心煩了。”周總理不讓他為難,當即表示:“那你就擔任外交部顧問好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員會副主席的陸定一曾有一次建議翰老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他同樣也推辭了。1997年北大百年校慶,翰老正好跟北大同庚,北大學生堅持要翰老講幾句話,他還提到不要當官迷,要好好讀書寫書,特別是要培養青年人才。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到了毛主席的《紀念白求恩》這篇名文。毛主席提倡做人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心中翰老就是這樣的人。
(責任編輯楊琳)
作者: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