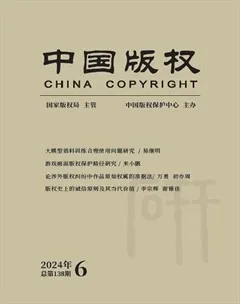游戲畫面版權保護路徑研究
摘要:在游戲畫面的法律屬性界定上,盡管其符合作品的構成要件,但關于其應歸屬于何種作品類型,理論與實務界長期存在爭議。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攝制”應作廣義解讀,涵蓋“拍攝”與“制作”兩種形式。游戲畫面作為動態視覺表達的載體,其在電子設備上的穩定呈現,遵循開發者預設的邏輯框架,表現出的預設性與預期性滿足“固定性”要求。隨著互動電影、互動視頻等“交互式”視聽作品的興起,“交互性”已非游戲畫面的獨有特征,且玩家操作引發的權屬問題可通過“演繹作品”制度有效解決。因此,游戲畫面應納入視聽作品范疇予以保護。以“計算機軟件”路徑保護游戲畫面,難以全面覆蓋游戲畫面的動態視覺表達;以“游戲作品”這一新作品類型作為保護路徑具有合理性,但面臨著保護范圍界定的理論質疑,以及與視聽作品范疇重疊的現實難題。因此,將游戲畫面認定為視聽作品賦予版權保護,依然是當前最為適宜的法律路徑。
關鍵詞:游戲畫面;游戲作品;計算機軟件;視聽作品
一、游戲畫面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一般認為,威利·海金博塞姆(WilliamHiginbotham)博士在1958年創作的《雙人網球》(TennisforTwo)為世界上第一款電子游戲。而電子游戲產業化的起點,則通常被認為是1972年,當時新成立的雅達利(Atari)公司將其開發的《乓》(Pong)游戲安裝在酒吧中,隨后該酒吧的顧客數量大增,甚至出現了投幣箱被大量硬幣填滿而無法投幣的尷尬情況。游戲產業從小酒吧的“招財貓”變成如今具有11773.79億元規模的龐大市場,其迅猛的發展也引發了諸多法律爭議。{1}而最初的版權爭議焦點,在于游戲是否屬于“作品”。
(一)游戲畫面具有可版權性
《伯爾尼公約》第二條第1項規定:“‘文學和藝術作品’一詞包括文學、科學和藝術領域內的一切成果,不論其表現形式或方式如何”;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的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一般認為,除獨創性這一實質要件外,作品有三個形式要件:第一,作品是智力成果;第二,作品是能夠被他人客觀感知的外在表達;第三,作品必須限于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2}
1.游戲畫面屬于智力成果
對智力成果保護的必要性,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紀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出的“勞動財產理論”,其認為創作行為屬于一種智力勞動,成果應像其他勞動成果一樣受到財產權保護。隨著啟蒙思潮的興起,智力成果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豐富,不僅被視為勞動成果,更被視為作者人格的延伸和精神的體現,對智力成果的保護成為“天賦人權”的必然要求。無論理論基礎如何,對智力成果的保護都離不開創作者的智力勞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中確認:“從人格權的角度,智力勞動系個人運用智力、思想、認識的過程,被視為個人思想的延伸;從財產權的角度,作品系個人智力的付出,智力勞動的結果亦應當歸屬于付出者。”{3}
游戲畫面的形成是智力勞動與創意的結晶,其誕生融合了計算機圖形學、美術繪畫、特效渲染等多領域的專業知識,涵蓋了軟件開發、藝術設計、音樂創作和游戲劇情編寫等多方面的創作工程。創作團隊通過無數次的嘗試、修改和完善,將各種元素巧妙地組合在一起,從構思到游戲畫面的最終呈現,無不凝聚著游戲開發者們的智慧和汗水。這一過程蘊含著復雜的智力勞動,游戲畫面無疑是開發者的智力結晶,其法律屬性符合“智力成果”的基本要求。
2.游戲畫面屬于外在表達
依據傳統的思想與表達二分法的判斷標準,著作權法只保護外在表達而不保護思想,即著作權法不保護抽象的思想、思路、觀念、理論、創意、構思、概念,而只保護以文字、音樂、美術等各種表現形式對思想的具體表達。然而,并非所有外在表達均受保護。由于表達和思想之間的密切關系,當某些思想的表達方式只有一種或極其有限,或者表達過于簡單以至于無法清晰地區分表達與思想時,這種表達將無法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這就是所謂的“有限表達”原則。{4}
在早期游戲產業,游戲畫面能否構成作品曾受到質疑。早期的電子游戲表現形式和內容普遍較為簡單,通常僅包括黑色的背景、簡單的可移動像素點以及基本游戲功能,因難以明確劃分表達和思想范疇,無法被認定為作品。{5}不過,這種質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當時的計算機軟件編程技術尚處于起步階段所導致的。隨著編程技術的進步和設備硬件性能的提升,游戲的表現力得到飛躍。美國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最終認可了電子游戲屬于“固定在有形媒介中”的作品,并將游戲畫面認定為視聽作品。{6}
3.游戲畫面屬于“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
游戲作為一種融合了計算機代碼與多元藝術元素的計算機程序,其外在表現形式無疑屬于科學范疇內。2020年8月,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等五部門聯合印發《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標準體系建設指南》,確定了智能游戲在人工智能標準體系結構中的支撐地位,進一步肯定了游戲在推動現代科技進步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游戲畫面并非僅限于科學范疇,其豐富的色彩設計和畫面表現,融合了文學、藝術等多種元素。游戲畫面不僅僅是像素與色彩的簡單堆砌,更是情感與想象的視覺化表達。它借鑒了文學的敘事手法,通過細膩的場景描繪與角色塑造,講述著或壯麗或溫婉的故事,引導玩家在虛擬世界中遨游,體驗不同的人生與情感。游戲設計者和開發者們如同藝術家般,以屏幕為畫布,以代碼為筆觸,創作出令人嘆為觀止的視覺作品。從光影的巧妙運用到色彩的精妙搭配,從角色設計的獨特韻味到場景構建的宏大氣勢,每一處細節都凝聚著設計開發者對美的追求與創作。這種融合了現代科技手段的藝術表達,不僅拓寬了藝術的邊界,也讓游戲畫面成為科學與藝術完美融合的典范,被玩家稱為自繪畫、雕刻、建筑、音樂、詩歌、舞蹈、戲劇、電影后的“第九藝術”,成為傳播我國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魅力的重要渠道和窗口。{7}
(二)游戲畫面版權保護路徑的分歧
在學術理論與司法實踐中,盡管游戲畫面的作品屬性已獲得廣泛共識,但其在著作權法框架下的具體作品類型認定仍然存在爭議。早期司法判決傾向于將游戲畫面作為視聽作品加以保護,尤其是在奇跡MU案之后,法院普遍傾向于將游戲畫面認定為“類電作品”(即現行法中的視聽作品)。{8}同時,也存在將游戲畫面認定為計算機軟件的構成部分,納入“計算機軟件”范疇的案例。{9}此外,網易《率土之濱》與靈犀互娛、廣州簡悅《三國志·戰略版》著作權侵權案中,創新性地提出了“游戲作品”這一概念,{10}將其視為傳統八種法定作品類型框架之外的新型作品,為游戲畫面的版權保護開辟了新的視角。
從技術層面而言,游戲畫面無疑是計算機軟件程序運行后的直觀展現;但從法律層面來看,其也充分滿足了視聽作品的構成要件,展現出獨特的藝術價值和表現形式;從用戶直觀體驗的角度,游戲畫面確實蘊含著區別于傳統視聽作品的“交互性”,這也是游戲畫面在作品歸類上爭論不斷的根本原因。
二、以“視聽作品”保護游戲畫面的路徑分析
將游戲畫面認定為“類電作品”(即“視聽作品”的一種)是司法實踐較為常見的保護策略,這一路徑涉及對游戲畫面固定性要件的深入分析,以及二創行為認定的探討。
(一)游戲畫面滿足視聽作品的構成要件
我國《著作權法》自2001年首次修改至2020年第三次修改之前,長期沿用了“電影作品”與“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簡稱“類電作品”)的分類方式。然而,2020年《著作權法》修改后,這一作品類型被簡化為“視聽作品”,并將“電影作品和類電作品”修改為“電影、電視劇作品”和“其他視聽作品”。盡管現行《著作權法》并未明確界定“視聽作品”的概念,但可以基于“視聽作品的實例是帶有聲音的電影作品和所有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表現的作品”{11}的理解,并參照《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四條規定來界定視聽作品的構成要件。
在當前法律框架下,視聽作品需滿足以下三個要件:首先,作品必須“攝制在一定介質上”;其次,作品應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最后,作品應能“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學界對游戲畫面是否滿足“攝制在一定介質上”存在爭議。{12}具體而言,就創作方式來講,游戲并非通過“攝制”過程產生,且游戲的畫面由程序生成,其圖像顯示受用戶操作和設備硬件等因素影響具有多樣性和可變性,因此有觀點認為游戲畫面不符合“固定性”要件“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的要求。{13}
1.“攝制”包含“拍攝”與“制作”
“攝制”一詞,在傳統理解中通常指涉利用攝像機等物理設備進行影像的捕捉和記錄,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回溯我國動畫產業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在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后,手繪動畫占據主流,{14}動畫片同樣需要依賴攝像機拍攝才能完成最終作品的制作流程。{15}然而,進入新世紀后,電腦制作動畫成為主流,Flash等軟件的應用極大地簡化了動畫制作流程,減少了手繪與拍攝的繁復步驟。此時,若固守“未使用攝像機拍攝即不構成視聽作品”的觀點,將導致大部分現代動畫(包括全部3D動畫)被排除在“類電作品”的范疇之外。
從比較法角度來看,將“攝制”作為類電作品構成要件的立法例并不存在。{16}事實上,我國“類電作品”的概念移植自《伯爾尼公約》1948年布魯塞爾文本“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式創作的作品”,{17}當時電影作為新興產業,包括動畫片在內的類電作品均需要通過相關物理設備進行拍攝,故這種表述在當時并無不妥。但《伯爾尼公約》1971年巴黎文本將“類電作品”的概念更新為“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式表現的作品”,{18}用“Express”替代了“Produce”,強調“表達”而非“創作”。《伯爾尼公約》并未對類電作品做任何技術上的要求,而是外在呈現,《伯爾尼公約指南》明確對此類作品并不考慮它的“工藝方法”。{19}在《現代漢語詞典》中“攝制”的含義被解釋為“拍攝并制作(影視片等)”,{20}但從立法目的出發,若嚴格依照“拍攝并制作”的含義認定類電作品,將導致其外延過于狹小而無法發揮應有的功能,因此,應當將“攝制”的法律含義理解為“拍攝或制作”,并將兩者之間的邏輯從先后順序變更為兩者擇一,將包容性更強的“制作”納入“攝制”的內涵中。
這種解釋同時也是目前司法實踐的主流觀點。例如,在樂迪熊公司與華夏金馬公司案中,樂迪熊公司認為涉案MTV未使用膠片拍攝,不符合“攝制”的條件;法院則指出,現行法律并未排除以Flash軟件制作、保存在數據光盤中的制作方法和固定方式,故而未支持樂迪熊公司的主張。{21}在夢幻西游2不正當競爭案中,法院更是明確表達了“不宜對攝制作字面文義的狹隘理解,以制作工藝來限制對作品的保護”的觀點。{22}
2.游戲畫面符合“固定性”要求
“固定性”是指視聽作品需要穩定地固定在有形物質載體上。{23}在游戲誕生之初,便有對游戲畫面是否符合固定性的質疑。這種質疑主要源于技術層面的考量。受限于存儲設備的限制,早期的電子游戲無法將畫面完整地儲存于設備中,而是基于實時演算技術對游戲中的各元素進行組合并展示于屏幕之上。對此,有人認為“計算機只是在隨時生成新的畫面,而其本身并未固定在任何介質之中”。{24}然而,如上文中對“攝制”的討論,這種觀點忽視了視聽作品的本質在于表現形式而非技術手段,若過于強調技術要素可能會導致立法目的的偏移。美國第七巡回上訴法院也明確指出,盡管游戲畫面的復制技術與錄像帶不同,但國會已允許將這種可能性固定在“現在已知的或后來開發的”表達媒介中。{25}
游戲畫面受玩家操作影響的特性也引發了對游戲畫面“固定性”的另一種質疑。由于玩家的不同操作,游戲畫面難以保持完全一致,似乎并不符合“固定性”的“重復性畫面”要求。有學者認為,早期的游戲因為比較簡單、體量較小,故畫面可以窮盡,而自從網絡游戲誕生后,基于早期游戲可以通過排列組合“窮盡”玩家操作,從而將游戲畫面認定為視聽作品的理論基礎已被動搖。{26}然而,這種觀點存在認識上的誤區。首先,若將畫面是否可窮盡作為判斷游戲畫面是否構成視聽作品的標準,那么自從卷軸游戲誕生之后,由于游戲的背景不斷發生變化,且玩家的前進、后退、跳躍均會對游戲呈現的畫面造成影響,游戲的畫面實際上已經難以窮盡。其次,司法實踐中法院也從未將游戲畫面的“可窮盡”作為確認標準。在SternElecsv.Kaufmank案中,法官將游戲畫面認定為視聽作品的關鍵在于游戲圖像、聲音等預設元素的重復出現。{27}盡管無法對《魂斗羅》《超級瑪麗》等游戲的畫面進行窮盡,但是如敵人的位置、攻擊方式、角色的可操作性以及游戲的背景、地圖、配樂等,仍然可以令玩家對操作引起的畫面變化形成預期,玩家對畫面的影響始終在開發者預設的框架內發生。
因此,構成游戲畫面的預設元素的存儲才是認定游戲畫面“固定性”的關鍵。該觀點可見于我國法院的諸多裁判中,例如《夢幻西游》案、《奇跡MU》案、《昆侖墟》案、迷你世界VS我的世界案、《王者榮耀》《穿越火線》《英雄聯盟》等游戲視頻侵權案等。{28}法院均依據組成畫面的元素已預先存儲在游戲資源庫中的事實認定游戲畫面符合“固定性”的要求。需注意的是,當前司法實踐領域對傳統“固定性”概念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對達成“固定”所需時長和介質有形性做出了全新的判斷,例如將“直播信號”視為承載連續畫面的介質,從而將連續畫面固定于信號之上的體育直播納入了視聽作品的范疇。{29}相較于通過信號“固定”的直播畫面,存儲在服務器或電腦內存中的游戲畫面無疑更加符合固定性的要求。
(二)“交互式”視聽作品屢見不鮮
有觀點認為,游戲的交互性特征與視聽作品的“單項式、被動式和敘事式”特征存在差異。{30}在游戲中,用戶不再是單純欣賞、被動接受內容的“觀眾”,而是成為通過輸入指令、推動和“控制”游戲劇情發展,具有能動性的“玩家”。這一觀點并非我國學界所獨有。1998年,日本游戲廠商艾尼克斯(Enix)向東京地方法院上訴,以侵犯“電影作品”的發行權為由要求法院禁止被告對二手游戲的銷售。{31}東京法院以游戲的互動性不符合電影作品的特點為由,認定游戲畫面不能獲得著作權保護。{32}
然而,僅憑某段畫面是否具有“交互性”來判斷其是否屬于視聽作品顯然是不合理的。隨著媒體形式的演進,傳統的視聽作品中也開始融入交互元素。例如,美國奈飛公司(Netflix)于2018年12月上線的影片《黑鏡:潘達斯奈基》中,觀眾需要在觀看的同時選擇主角的行為,從而使劇情進入不同的分支。2019年,我國最大的彈幕式視頻內容分享平臺嗶哩嗶哩也上線了“互動視頻”功能,創作者可制作包含不同選項的交互式視頻,從而使觀眾獲得更強的沉浸感和體驗感。由于嗶哩嗶哩“互動視頻”將用戶的選擇作為推進視頻進度的必要條件,若用戶仍然保持在影院銀幕或電視機前的被動習慣,不予配合,則視頻內容也將陷入卡頓與停滯。事實上,在艾尼克斯提起上訴的同時,卡普空、科樂美、南夢宮、史可威爾、索尼和世嘉六家游戲廠商也于大阪提起了對二手游戲商家的訴訟,法院文書便援引了互動電影的例子,認定游戲畫面構成電影作品,{33}且該觀點最終得到了日本最高法院的支持。{34}
(三)“演繹作品”制度足以解決與玩家間的權屬問題
從實踐經驗來看,某些游戲畫面的形成依賴于玩家的創意性操作,例如《我的世界》和《元夢之星》等游戲,其核心玩法在于用戶生成內容。著作權法中明確規定了視聽作品版權歸屬于制作者,盡管目前尚未對“制作者”概念予以明確定義,但無論是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提出的“首先采取行動并承擔財務責任”標準,還是草案中“組織制作并承擔責任”的表述,都指向了游戲開發商。在《三國志·戰略版》與《率土之濱》案中,一審法院指出,玩家行為對畫面獨創性的影響是游戲不宜作為“視聽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玩家不能享有游戲畫面的版權,那么游戲公司構建玩家創意平臺的合法性基礎將受到動搖。然而,關于因玩家創作性行為而產生的游戲畫面是否能夠通過“演繹作品”得到保護,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1.玩家游戲操作畫面難以構成“演繹作品”
在游戲設計中,大多數游戲傾向于限制玩家的個性化創作空間,游戲的核心元素,包括劇情演出、角色形象、裝備道具、技能特效、文字設計、音樂音效等,均由游戲開發商預先設計并存儲固定在游戲資源庫中。玩家在游玩過程中,需要遵循既定的規則和流程,通常無法自由引入外部素材或創造游戲中原本不存在的元素。因此,即便是玩家間的社交互動畫面或是競技對抗畫面,也大多局限于開發商預設的畫面可能性范圍內。美國法官在Midway案中的比喻恰如其分:玩家在游戲中的操作類似于“使用遙控器更換電視頻道”。{35}在我國司法實踐中,這一觀點也獲得認可。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關于網絡游戲知識產權民事糾紛案件的審判指引(試行)》(以下簡稱《游戲指引》)第二十條第1款中規定,如果游戲畫面是由游戲程序根據玩家的操作指令、按既定規則調用游戲開發商預先設置的游戲元素自動生成的,那么玩家的操作行為不應被視為創作行為。
玩家在游戲中的操作主要體現了對游戲玩法的理解、技巧的運用和策略的實踐,而非在原有作品的基礎上融入新的獨創性元素而產生的新作品,因此,這類游戲畫面難以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演繹作品”。
2.玩家“二創”衍生畫面的“演繹作品”認定
“二次創作”(以下簡稱二創),亦稱“再創作”或“衍生創作”,在影視、動畫、網絡文學等多個藝術領域,粉絲的二創活動頗為普遍。常見的二創形式包括:基于原作角色性格和經歷撰寫新小說(比如同人文章),對原作畫面進行剪輯、編排并添加音樂的MAD視頻以及通過配音、剪輯、情節設計等手法制作的“惡搞”視頻等。例如,網絡用戶通過重新剪輯和重組動畫《名偵探柯南》的配音及片段,將原本代表正義、善良的主角“柯南”顛覆性重塑為一名殘忍、冷酷的反派角色。二創行為的本質是對原作品的一種改編(或匯編),若其滿足著作權法中的“獨創性”要求,則應當屬于“演繹作品”范疇。
同樣,在游戲領域,玩家可以通過錄制、配音、剪輯等手段,為游戲畫面注入新的創意,從而構建超越原設定的情節脈絡。例如,《反恐精英》玩家“甜咖啡”創作的《生存》(toSURVIVE),描述了反恐精英們并肩作戰、精誠團結,在與恐怖分子緊張刺激的戰斗中,成功護送VIP安全撤離的故事,將游戲畫面轉化為一部扣人心弦的短片;{36}再如,《跑跑卡丁車》玩家“knat123”歷時5年制作的《海盜三部曲》,講述了角色“皮蛋”與“海盜船長”之間的恩仇故事。{37}盡管這些作品在游戲過程中未超出游戲開發商預設的操作空間,但玩家憑借其才能和創意為畫面賦予了全新的故事內核和情感表達,從而客觀上可能已經實現了從游戲素材到“作品”的轉變。
3.一定創作空間下玩家創作行為的演繹作品認定
隨著“元宇宙”概念的興起,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Content,以下簡稱UGC)在游戲產業中的價值日益凸顯。在主流UGC游戲的用戶協議中,普遍存在關于用戶內容權利歸屬約定的類似條款,例如《我的世界》游戲開發者MojangStudios公司,在其協議中聲明:“您的內容(例如,您創建的世界)歸您所有……我們保留包括游戲本身(包括其內容,如我們的方塊的紋理和我們的角色皮膚)、我們的服務以及各自的衍生品的所有權”;騰訊游戲的用戶協議也明確指出,若用戶創作內容包含騰訊享有知識產權內容的,其傳播或商業利用需經騰訊公司許可。《刀塔傳奇》曾因涉嫌抄襲基于《魔獸爭霸3》地圖編輯功能誕生的DOTA中的人物形象和技能,遭到暴雪公司和維爾福集團共同維權,最終開發商承認侵權并與暴雪公司和解。{38}這些約定和案例體現了游戲行業對UGC內容權利歸屬的共識——雖未直接使用“演繹作品”的表述,但均認同企業對UGC擁有一定的控制權。
在司法實踐中,《游戲指引》第十七條第3款規定,游戲畫面符合類電作品要件的應予保護;第二十條第2款規定,若游戲預留創作空間并提供創作工具,玩家創作的新元素符合作品構成要件的,以該玩家為作者。盡管未直接使用“演繹作品”表述,但鑒于玩家通常不符合視聽作品“制作者”的條件,《游戲指引》的規定從司法實踐角度支持了UGC作為“演繹作品”的性質。此外,在《游戲指引》發布一年后,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迷你世界VS我的世界”案終審判決中,明確指出UGC內容屬于對游戲開發者創作內容的演繹作品。{39}
盡管創作自由度有所提升,玩家的創作行為依舊受限于游戲開發商預設的素材和框架,如音樂、美術素材、人物模型、說明文字等,這些基礎元素構成玩家創作行為的基石。UGC本質上與二創行為相似,都是將個人創意與游戲預設內容結合,通過對游戲預設內容的編排、挑選、重新組合形成全新的表達,符合我國《著作權法》第十三條規定的“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即“演繹作品”的基本要求。
三、以“計算機軟件”保護游戲畫面的路徑分析
司法實踐中也存在將游戲畫面納入計算機軟件范疇的做法,這一路徑的合理性與可行性尚需進一步探討。
(一)游戲畫面不屬于“計算機軟件”
根據我國《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的規定,計算機軟件是指計算機程序及相關文檔。在著作權法視域下,計算機程序特指代碼化指令序列或可自動轉換為序列的符號化指令/語句序列,而不包含被調用的資源或數據。現代游戲往往通過“游戲引擎”實現對預設資源的調用,在著作權法意義上,只有“游戲引擎”本身屬于計算機程序的范疇,而諸如美術、聲音、地圖等預設資源則不屬于計算機程序,應通過其他作品類型尋求保護。{40}這一觀點在司法實踐中也有所體現,例如在英國的諾瓦與馬佐瑪案(Novav.MazoomaGames)中,面對被告游戲軟件對原告游戲軟件構成實質性相似的指控,由于被告未獲得原告軟件源代碼,法院將審理重點轉向了軟件中所體現的“美術作品”“戲劇作品”和“電影作品”;{41}國內也有大量類似案例,如北京網元圣唐娛樂科技有限公司與成都云格致力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計算機軟件著作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法院明確指出僅以計算機軟件作品保護涉案游戲,無法覆蓋涉案游戲中更為豐富且為公眾所知的內容。{42}
當然,深入分析因游戲畫面相似而引發的計算機軟件侵權案件可以發現,法院并未直接將游戲畫面等同于軟件代碼本身,在無法獲取源代碼的情況下,法院通常會借助軟件運行時呈現的外部特征——如操作界面、角色形象、故事情節等,逆向推定代碼層面的相似性。最高人民法院在相關案件中指出,鑒于游戲開發的獨創性和復雜性,獨立開發的游戲軟件出現高度相似的外在表達的可能性較小,從而“可以推定兩者構成實質性相似”。{43}
(二)無法適應游戲產業的實際情況
在游戲產業的早期階段,由于游戲開發商的員工流動性較大,游戲侵權的主要形式表現為離職程序員攜帶游戲軟件源代碼離開,經過簡單修改后推出新的游戲,例如暢游公司與麒麟公司《成吉思汗》游戲軟件侵權案中,法院在《成吉思汗》游戲源代碼中發現了原告公司工程師的名字。{44}然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尤其是反編譯技術的進步和編程語言的多樣化,這種初級抄襲行為因易于辨識而逐漸減少。目前的“換皮游戲”通常通過重寫代碼、改變編程語言、調整程序細節等方式制作,即便游戲畫面高度相似或素材完全相同,也可以規避計算機軟件侵權的認定。
此外,將游戲畫面納入計算機軟件的組成部分予以保護也引發了新的問題。由于計算機軟件的版權無法控制向公眾展示軟件表現畫面的行為,例如,學者在學術會議上展示幻燈片、Word文檔或政府在宣傳屏幕上展示使用Windows系統顯示的“桌面”,并不會構成對微軟公司版權的侵犯。因此,僅依靠計算機軟件著作權也無法阻止未經許可的網絡直播游戲畫面行為。同時,考慮到游戲引擎的開發需要豐富的經驗積累和較高的資金投入,多數獨立游戲開發商已將重心轉向包括地圖、關卡、人物、劇情在內的核心游戲資源的設計和豐富,游戲制作行業已經形成了游戲吸引力更依賴于內容質量的共識。在這種背景下,將游戲視為整體計算機軟件進行保護可能會導致游戲引擎這一相對次要的部分被過度強調,從而在使用同一引擎開發的游戲中,由于代碼重復部分較多而難以判斷是否構成侵權。相較而言,以游戲畫面為核心,將游戲外在表現作為保護重點,對游戲進行版權保護,不僅符合法理,也更契合當前游戲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
四、以“游戲作品”保護游戲畫面的路徑思考
將游戲畫面認定為新型“游戲作品”賦予版權保護,構成一種新的保護路徑。此種方式具有其獨特優勢,但同時也面臨一系列挑戰。
(一)創設“游戲作品”的優勢
在《三國志·戰略版》與《率土之濱》案中,廣州互聯網法院采用“游戲作品”這一新的作品類型進行保護的實質原因在于構建對游戲規則的法律保護,法院指出,游戲的獨創性體現在游戲規則、游戲素材和游戲程序的具體設計、選擇和編排中,并且游戲規則對于游戲畫面的形成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因此,應當將游戲作為一種新的作品類型。{45}無論游戲規則保護的依據是否充分,可以確定的是,游戲作品概念的確立為棋牌類游戲等傳統上難以符合視聽作品標準的游戲提供了直接的保護途徑,從而避免了僅能通過計算機軟件或美術作品等間接方式獲得有限保護的局限性。同時,那些通常難以單獨構成作品的游戲元素,如獨特的特效與音效設計,作為游戲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可以獲得版權保護。
此外,創設游戲作品這一分類對于構建游戲的整體保護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游戲權利人維權過程中普遍面臨維權成本高和損害賠償不足的雙重困難。司法實踐中,法院通常采用“抽象歸納法”對游戲中的各個要素進行拆分,將未重復的部分以及雖重復但不構成“表達”的部分排除在保護范圍之外。這種要素拆分式的保護往往導致侵權行為的侵權后果與盈利之間存在較大差距,例如在《爐石傳說》與《臥龍傳說》案中,法院通過拆分和過濾后,僅支持了對類電作品“牌店及打開擴展包動畫”和美術作品“爐石標識”的侵權,判決被告承擔75710元(含25710元的維權支出)的賠償責任。{46}盡管在理論和實踐中均可在視聽作品的框架內對游戲進行整體保護,但如果將游戲作品明確界定為獨立的作品類型,無疑更能凸顯立法者對于游戲產業的重視與支持。
(二)“游戲作品”面臨的挑戰
1.理論質疑:游戲規則是否屬于思想范疇
游戲規則是一個寬泛且復雜的概念,在一款游戲中,游戲規則既可能指代操控角色行動的基礎操作規范,也可能涉及玩家的起始地點、屬性及屬性點的分配、裝備的數值等所謂的“機制”和“數值”。在《三國志·戰略版》與《率土之濱》案中,法院創造性地將利用現有規則的獨創性組合視為一種獨創性的表達,并認為其應當獲得版權保護,{47}這一觀點引發了學界的廣泛討論與質疑。
有學者指出,游戲規則與專利技術方案在本質上有相似性,法院通過“情節化”或“操作化”的方式將游戲規則納入版權保護范疇,混淆了思想與表達、操作方法與藝術創作的界限。{48}正如樂譜雖可指導演奏,但其受保護的核心仍在于音樂作品中的獨創性表達,而非演奏技巧本身;攝影作品亦然,其保護的是感光材料上記錄的獨特影像,而非拍攝過程的技術操作。因此,如果游戲規則的獨創性僅僅體現在對既有規則的創造性編排上,而未通過新的藝術或文學等形式表現出來,則難以直接獲得版權保護。同時,也有學者認為,游戲規則與電視節目模式類似,都是在既有規則中進行選擇、編排而形成的具有獨創性的組合,然而我國司法實踐中尚未有保護電視節目模式的先例。{49}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調研報告中強調,對游戲規則的保護可能導致對游戲玩法的壟斷。如果三千年前就有法律保護游戲規則,那么中國象棋、日本將棋、國際象棋、泰國象棋都可能面臨侵權指控——因為“馬走日”“象走田”“車行直線”“將軍”“一回合走一步”這些玩法和規則,都源于印度象棋“恰圖蘭卡”。此外,由于《暗黑破壞神》的廣受歡迎,市面上出現了大批玩法相似、規則相近、表現類似的游戲,形成了所謂“暗黑Like”的游戲類型,涌現出許多優秀作品。{50}我國并非沒有對惡劣“換皮”游戲的法律規制,實踐中已有通過反不正當競爭實現對換皮游戲制裁的案例。在已有法律保護路徑的前提下,將游戲規則納入版權保護范疇,需要更堅實的理論依據和必要性論證。
2.現實難題:需要建立與視聽作品的區分標準
將游戲單獨歸類為“游戲作品”在事實區分上存在困難,尤其是如何精確地界定其與視聽作品的界限。若以能否可以交互作為衡量標準,互動視頻似乎應當歸入“游戲作品”的范疇,因為確實有用戶將觀看帶有劇情選擇和人物能力設定的互動視頻體驗描述為“玩游戲”。但是,互動視頻的多樣性意味著其除了院線上映的電影(比如首部互動電影便于1967年上映),{51}還包括制作精良但不含劇情的“塔羅占卜”或“周易六爻”等“算卦視頻”,雖然都具有互動性,但缺乏游戲體驗,難以符合公眾對“游戲”的認知。那么,是否可以通過創作完成的標志來判斷作品屬性?法院在判決中指出,“電影作品”創作完成的標志是全部電影畫面均已固定;但電子游戲創作完成的標志,并非游戲畫面的固定,而是整合了游戲規則、游戲素材和游戲程序后的游戲包體的形成。{52}然而,這個答案依舊是否定的,因為并非所有游戲都具有“游戲包體”。例如,使用Flash動畫軟件制作的游戲完成后會生成后綴為“Swf”的文件,這種文件既可能代表游戲(例如4399網站上的Flash小游戲),也可能代表動畫(如曾經風靡一時的《東北人都是活雷鋒》的MTV畫面),兩者在制作過程中均可能涉及代碼的應用與外部資源的使用,{53}并且都可以不使用外部資源而全部自行繪制。在一些Flash游戲或動畫制作過程中,交互功能是與畫面的制作同步進行的,這意味著當畫面固定時,其游戲或動畫便已創作完成。“游戲包體”實際上是將游戲所涉及的各個文件打包壓縮的過程,是基于傳播安全和便利考慮而采取的特殊存儲方式,其在法律上與將電腦制作的電影壓縮成zip文件并無本質區別。同時,以目標為導向的區分標準同樣存在不足。游戲通常設有明確的目標,如完成任務、收集物品、贏得比賽等,而電影則側重于講述故事,通過視聽和情感的沖擊觸動觀眾。然而,現代游戲作品中不乏以故事敘述為核心的游戲,它們同樣以傳遞故事為主要賣點。因此,如何構建一個科學、精確的區分標準,是以“游戲作品”保護游戲畫面這一新路徑所面臨的現實難題。
五、結語
“游戲作品”概念的提出及其在實踐中的應用,標志著我國在游戲版權領域的法律保護水平在國際層面已達到較高水平。該概念旨在解決司法實踐中長期存在的維權難度大、維權成本高及賠償額度不足等問題。游戲作品的概念還具有一定的法律宣示意義,免除了游戲權利人在尋求行政或司法保護時,需詳細說明游戲的可版權性及其所屬作品類別的復雜程序。同時,這一概念也體現了對未來法律發展趨勢的前瞻性考量,例如,其在元宇宙等新興領域的潛在適用性。盡管如此,關于游戲作品的保護范圍、保護方式等問題,目前尚未形成較為一致的理論共識,實踐操作中亦面臨區分游戲作品和視聽作品的挑戰。鑒于此,將游戲畫面納入視聽作品范疇進行保護,不僅契合法理邏輯,而且在視聽作品的框架下也可以實現對游戲的整體保護,有效應對當前實踐中的諸多難題。在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選擇視聽作品作為游戲畫面保護路徑,無疑是既考慮法律適用性又滿足現實需求的最優方案。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