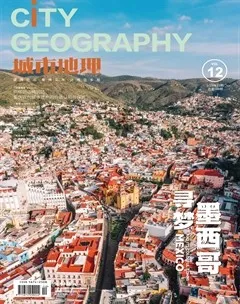別樣的山城記憶:重慶近代城市遺產(chǎn)的價(jià)值認(rèn)知與保護(hù)







前言
在歲月的長(zhǎng)河中,那些被時(shí)光輕撫的城市遺產(chǎn)①,往往不似文物建筑那般璀璨奪目,卻以一種樸素的姿態(tài),靜默地訴說著過往。它們悄無聲息地融入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隨著城市的脈動(dòng)而逐漸演變。特別是近代城市遺產(chǎn),雖然大部分因缺乏定期維護(hù)而日漸衰落,但其所蘊(yùn)含的豐富歷史元素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建筑風(fēng)貌,是一座城市不可多得的文化資產(chǎn)。如何妥善保護(hù)與更新,使其在新時(shí)代煥發(fā)出新活力,這需要我們帶著理性思維和敬畏之心,從它們的價(jià)值本身出發(fā),耐心探尋。
1. 百年尋根:摸清重慶近代城市遺產(chǎn)發(fā)展脈絡(luò)
重慶建城3000 余年,定名800余年,歷史悠久,源遠(yuǎn)流長(zhǎng),巴渝文化、三峽文化、抗戰(zhàn)文化、革命文化、統(tǒng)戰(zhàn)文化、移民文化在這里交相輝映。按照重慶在發(fā)展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形態(tài)、功能及相互作用的特征,其歷史脈絡(luò)大致可劃分為4 個(gè)階段,即開埠前、開埠后—1936 年、1937 年—1949 年、新中國(guó)成立后至今。其中,近代城市遺產(chǎn)主要形成于開埠后—1936 年、1937 年—1949 年這兩個(gè)歷史階段。
1.1 開埠后—1936 年
1890 年中英《新訂煙臺(tái)條約續(xù)增專條》的簽訂,使重慶成為約開埠城市②,西方帝國(guó)主義國(guó)家陸續(xù)在重慶設(shè)立通商口岸[1]。隨著外國(guó)商船、商人的進(jìn)來,外國(guó)宗教建筑、洋行建筑、領(lǐng)事館建筑相繼建成,本土建筑三峽文化、抗戰(zhàn)文化、革命文化、統(tǒng)戰(zhàn)文化、移民文化在這里交相輝映。按照重慶在發(fā)展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形態(tài)、功能及相互作用的特征,其歷史脈絡(luò)大致可劃分為4 個(gè)階段,即開埠前、開埠后—1936 年、1937 年—1949 年、新中國(guó)成立后至今。其中,近代城市遺產(chǎn)主要形成于開埠后—1936 年、1937 年—1949 年這兩個(gè)歷史階段。1.1 開埠后—1936 年1890 年中英《新訂煙臺(tái)條約續(xù)增專條》的簽訂,使重慶成為約開埠城市②,西方帝國(guó)主義國(guó)家陸續(xù)在重慶設(shè)立通商口岸[1]。隨著外國(guó)商船、商人的進(jìn)來,外國(guó)宗教建筑、洋行建筑、領(lǐng)事館建筑相繼建成,本土建筑文化與外來建筑文化從最初的抵制到相互融合學(xué)習(xí),新技術(shù)、新材料的使用,也為重慶留下了別具風(fēng)味的建筑與城市空間[2-3],典型者如南岸區(qū)馬鞍山的外國(guó)辦事機(jī)構(gòu)與洋房群,海棠溪的洋行倉(cāng)庫(kù)[4](圖1、圖2)。
1.2 1937 年—1949 年
1937 年,抗日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南京國(guó)民政府移駐重慶,機(jī)關(guān)、學(xué)校、工廠、金融機(jī)構(gòu)等陸續(xù)遷入,重慶市區(qū)面積在1939 年—1945 年間擴(kuò)大了近4倍,市區(qū)人口增加了近3倍[5]。這期間,大量辦公、學(xué)校、醫(yī)院、工廠等公共建筑涌現(xiàn),盡管抗戰(zhàn)條件艱苦,但建筑創(chuàng)作思想活躍,不乏國(guó)民大會(huì)堂、國(guó)民政府辦公樓等早期現(xiàn)代主義設(shè)計(jì)思想的代表作[2][6]。而普通市民住宅雖然受到建設(shè)成本、建設(shè)條件等限制,多以“竹、木、石、土”等為建造材料,卻真實(shí)展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的生活環(huán)境與人們對(duì)抗戰(zhàn)的樂觀精神[7-9]。1945 年抗戰(zhàn)勝利后,國(guó)民政府還都南京,內(nèi)遷的學(xué)校、工廠、金融機(jī)構(gòu)等也陸續(xù)搬離,市區(qū)人口稍有減少,城市建設(shè)基本維持1945 年時(shí)的狀況。
2. 賡續(xù)歷史:探析重慶近代城市遺產(chǎn)價(jià)值
2.1 重慶近代城市遺產(chǎn)內(nèi)涵認(rèn)知
建筑既是人類社會(huì)活動(dòng)的場(chǎng)所,也凝聚著人類對(duì)于社會(huì)習(xí)俗、意識(shí)形態(tài)、倫理道德和技術(shù)水平的整體認(rèn)知。近代城市遺產(chǎn)對(duì)于重慶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其中西合璧的建筑藝術(shù),更在于它們代表著重慶在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文化、城市空間等方面發(fā)生的巨大改變。一則重慶由封閉的內(nèi)陸港口城市逐步成為外向型的商貿(mào)城市,城市經(jīng)濟(jì)空前發(fā)展,商業(yè)、金融、交通、工業(yè)四大支柱產(chǎn)業(yè)形成。二則因新思潮的涌入,重慶人也逐步走向了近代化、市民化,突破封建思想束縛,接受新民主主義思想。三則伴隨大批高等院校、文藝協(xié)會(huì)的集中,重慶文化學(xué)術(shù)昌明、民主潮流上漲[1]。同時(shí),這些城市中的新興事物也徹底改變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城市空間特有的街- 坊- 巷的構(gòu)成,城市生活圍繞學(xué)校、醫(yī)院、大型商場(chǎng)、公園等公共活動(dòng)空間展開,而望龍門纜車、電車等公共交通工具的誕生,則大大便利了人們的出行,推動(dòng)城市空間拓展與功能分區(qū)。
2.2 重慶近代城市遺產(chǎn)價(jià)值
近代城市遺產(chǎn)既是重慶近代歷史發(fā)展階段的重要物質(zhì)空間載體,同時(shí)也蘊(yùn)含了隱藏在遺產(chǎn)本體背后的各種社會(huì)人文信息和由此構(gòu)建的城市記憶,它們的價(jià)值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一是近代城市遺產(chǎn)獨(dú)特的城市肌理和組成其肌理的建筑與空間的整體性,較完整地反映了當(dāng)時(shí)的民俗文化、生產(chǎn)方式與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形制,記述了城市由鄉(xiāng)土社會(huì)向現(xiàn)代化轉(zhuǎn)型的過程,中西文化碰撞與國(guó)內(nèi)沿海開埠文化對(duì)內(nèi)陸城市的影響;二是近代城市遺產(chǎn)由“竹、木”等本地建筑材料與依山就勢(shì)的建筑空間所構(gòu)成的獨(dú)特的風(fēng)貌特征,展現(xiàn)了重慶人在艱苦的抗戰(zhàn)環(huán)境中積極樂觀的民族精神,“這些修建在陡坡江岸的頑強(qiáng)建筑里,脈動(dòng)著遠(yuǎn)東抗擊法西斯最強(qiáng)烈的心跳”(圖3、圖4);三是近代城市遺產(chǎn)大部分至今仍作為普通市民的生活工作場(chǎng)所而使用著,具有的樸實(shí)的使用價(jià)值以及不易被人們察覺的社會(huì)價(jià)值,既包括人們對(duì)抗戰(zhàn)這段歷史的記憶,也涉及重慶人對(duì)“鄉(xiāng)愁”的追憶。
3. 守正創(chuàng)新:細(xì)數(shù)重慶近代城市遺產(chǎn)保護(hù)更新案例
審視重慶近代城市遺產(chǎn)保護(hù)歷程,從最初的重視不夠、投入不足[10],到現(xiàn)今的主動(dòng)保護(hù)、創(chuàng)新保護(hù),雖然曾經(jīng)迷茫過、躊躇過,但隨著對(duì)歷史文化資源認(rèn)知的不斷深化,對(duì)中華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自信的不斷堅(jiān)定,越來越多的近代城市遺產(chǎn)片區(qū)得到有效保護(hù)利用傳承。結(jié)合資源調(diào)查、評(píng)估認(rèn)定,最新版《重慶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hù)規(guī)劃》明確將中心城區(qū)范圍內(nèi)李子壩、山城巷等近20 處近代歷史文化遺產(chǎn)片區(qū)納入歷史文化街區(qū)或傳統(tǒng)風(fēng)貌區(qū)(表1),并支持鼓勵(lì)各方主體積極參與近代歷史文化遺產(chǎn)片區(qū)保護(hù)傳承的規(guī)劃、建設(shè)、管理各環(huán)節(jié)。正所謂“路漫漫其修遠(yuǎn)兮”,以下重點(diǎn)對(duì)一些優(yōu)秀案例進(jìn)行詳細(xì)回顧,以資學(xué)習(xí)借鑒,推進(jìn)近代城市遺產(chǎn)的保護(hù)更新。
3.1 李子壩抗戰(zhàn)遺址公園
李子壩片區(qū)位于渝中區(qū),背靠佛圖關(guān),面臨嘉陵江(圖5),抗戰(zhàn)時(shí)期是國(guó)民黨軍統(tǒng)機(jī)要處駐地。新中國(guó)成立后,李子壩成為了重慶重要的工業(yè)基地,有大型國(guó)有企業(yè)紅巖汽車配件廠、三峽電器廠等[6] [11],成為繁華一時(shí)的核心地段。2000 年后,國(guó)企改革,大批職工下崗,整個(gè)片區(qū)也日益顯得破舊、凌亂。
2008 年5 月,渝中區(qū)政府啟動(dòng)李子壩片區(qū)危舊房改造項(xiàng)目,在拆遷過程中,發(fā)現(xiàn)片區(qū)內(nèi)留存有李根固舊居、國(guó)民參議員舊址、交通銀行學(xué)校舊址等抗戰(zhàn)遺址,引起社會(huì)各界關(guān)注。渝中區(qū)政府遂即停止施工,成立專項(xiàng)調(diào)查小組,對(duì)這一片區(qū)內(nèi)的抗戰(zhàn)遺址進(jìn)行了調(diào)查、梳理,邀請(qǐng)專業(yè)機(jī)構(gòu),制定了李子壩片區(qū)的整體保護(hù)與再利用規(guī)劃,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采用原地復(fù)建與遷建抗戰(zhàn)建筑遺址的方式,以市民公園的模式,建成李子壩抗戰(zhàn)遺址公園,免費(fèi)向公眾開放[12]。李子壩公園占地12 公頃,于2010 年正式開園,是重慶首個(gè)抗戰(zhàn)遺址公園,也是國(guó)內(nèi)首次以主題公園的形式展示歷史文化保護(hù)成果的公園(圖6)。目前對(duì)外開放的抗戰(zhàn)歷史文物建筑共5 組9 棟[13],集中展示了重慶抗戰(zhàn)時(shí)期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軍事、外交、金融等方面的歷史風(fēng)貌[14]。
3.2 山城巷
山城巷,原名天燈巷(1972 年改名),地處渝中區(qū)交通要道,建于古城墻崖壁之上,起于南紀(jì)門中興路,止于領(lǐng)事巷,連通重慶上下半城[15](圖7)。明清時(shí)期,山城巷便已建成,為城市居民生活區(qū)。開埠后,隨著上半城的發(fā)展以及靠近外國(guó)領(lǐng)事館區(qū),山城巷成為城市高級(jí)住宅區(qū),片區(qū)內(nèi)建有仁愛堂醫(yī)院、天主教堂等。2000年后,山城巷整體居住環(huán)境下降,原住民大量外遷。
2015 年,重慶開展《主城區(qū)歷史文化風(fēng)貌保護(hù)規(guī)劃》編制工作,發(fā)現(xiàn)山城巷不僅分布有10 處文物保護(hù),還有若干具有一定價(jià)值的歷史建筑和大量傳統(tǒng)建筑,老重慶風(fēng)貌和整體格局猶存,遂即列為傳統(tǒng)風(fēng)貌片區(qū)。2016 年,渝中區(qū)啟動(dòng)山城巷征收和修復(fù)工作。不同于過去推倒重建的做法,山城巷的保護(hù)修復(fù)采用微更新模式,以留和改為主,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街巷傳統(tǒng)空間、建筑風(fēng)貌和文化景觀,如對(duì)于具有一定傳統(tǒng)風(fēng)貌的危舊房,采取保留外側(cè)墻體,在建筑內(nèi)部植入新的結(jié)構(gòu)體系的做法,既能增強(qiáng)建筑的穩(wěn)定性,又滿足建筑內(nèi)部空間使用[16-17]。經(jīng)過3 年改造建設(shè),2020 年,山城巷正式運(yùn)營(yíng),其原生態(tài)的建筑肌理、既有的街巷格局、市井的城市生活場(chǎng)景,將城市更新與歷史人文有機(jī)結(jié)合,成為凸顯重慶地方特色重要名片(圖8、圖9)。
3.3 下浩老街
下浩老街由下浩正街和周家灣河街構(gòu)成,地處南岸南濱路、東水門大橋北側(cè)(圖10),百年前曾是南坪、海棠溪、上浩到彈子石的官道[18]。下浩老街三面環(huán)山一面臨水,因擁有良好的碼頭條件,南宋年間便已人丁興旺,到1891 年重慶開埠,更是成為外國(guó)商船停泊區(qū)、外國(guó)商人聚居地,洋行、醫(yī)院、別墅遍布其間,與巴渝傳統(tǒng)木構(gòu)建筑相得益彰,成為了山城江岸一道旖旎的風(fēng)景。1990 年后,隨著水運(yùn)碼頭功能的消逝、當(dāng)?shù)毓S生產(chǎn)經(jīng)營(yíng)的下滑以及南岸區(qū)城市發(fā)展重心的轉(zhuǎn)移,下浩老街片區(qū)逐步衰落[19]。
2008 年,下浩老街納入舊城改造片區(qū)計(jì)劃。2014 年,范圍涉及下浩老街、上浩老街、米市街等的慈云寺- 米市街- 龍門浩列為市級(jí)歷史文化街區(qū),開啟下浩老街發(fā)展的新機(jī)遇。2016 年,慈云寺- 米市街- 龍門浩歷史文化街區(qū)編制城市設(shè)計(jì),提出“保留、復(fù)蘇、創(chuàng)新”的規(guī)劃理念[20]。2021 年,南岸區(qū)政府啟動(dòng)下浩老街更新改造,命名為“下浩里”。借鑒山城巷的更新經(jīng)驗(yàn),按照“原址、原建、原面積、原高度、原風(fēng)貌”的原則對(duì)85 棟建筑進(jìn)行改造、更新[20-21],以最大程度地保護(hù)原始場(chǎng)地高差及場(chǎng)所精神(圖11、圖12)。2023 年,“下浩里”正式開街。相較洪崖洞的“網(wǎng)紅屬性”,“下浩里”保留了下浩老街原有的生活氣息,溪澗、筑臺(tái)、疊檐、院落將下浩老街的歷史與鄰里生活巧妙串聯(lián)[22],而充滿趣味的藝術(shù)空間又為老街注入新的經(jīng)濟(jì)活力。
4. 未來可期
在山城重慶的深處,近代城市遺產(chǎn)如同沉睡的寶藏,見證著歲月的流轉(zhuǎn),承載著歷史的厚重,雖然時(shí)光的流逝給它們?nèi)旧狭诵┰S的斑駁,但它們依舊散發(fā)著不可磨滅的光芒。回顧近30 年的保護(hù)歷程,從臨江門的變遷到李子壩的堅(jiān)守,從江北城的重生到山城巷的復(fù)興,每一次保護(hù)的嘗試,都是對(duì)歷史的尊重,對(duì)未來的承諾。我們以“走小步,不停步”的精神,努力找尋保護(hù)與更新的平衡點(diǎn),讓其重新煥發(fā)活力,讓更多人體驗(yàn)到藏身于城市角落中“平凡”遺產(chǎn)的魅力。
編輯+ 王旭
文獻(xiàn)參考
[1] 隗瀛濤. 近代重慶城市史[M]. 成都:四川大學(xué)出版社,1991.
[2] 劉川. 重慶近代建筑的形成發(fā)展及其主要特征[J]. 建筑學(xué)報(bào), 2000 (11): 55-58.
[3] 歐陽(yáng)樺. 山地風(fēng)貌與建筑形態(tài)——重慶近代西洋建筑特色[J]. 重慶建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3(04): 1-5.
[4] 歐陽(yáng)樺. 山地環(huán)境中的重慶近代西洋建筑特色[J]. 四川建筑, 2003(04): 12-14.
[5] 潘洵. 重慶抗戰(zhàn)文化資源保護(hù)、開發(fā)的現(xiàn)狀與對(duì)策[J]. 西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 2003(06): 55-60.
[6] 杜春蘭,李燕. 重慶抗戰(zhàn)遺址的保護(hù)與利用研究[J]. 重慶建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 2008(05): 10-14..
[7] 何智亞. 重慶老城[M]. 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8] 陳卓. 重慶近代居住建筑研究實(shí)例[J]. 重慶建筑, 2006 (02): 21-24.
[9] 齊子軒,孫雁. 重慶近代民居類歷史建筑的空間解析[J]. 室內(nèi)設(shè)計(jì), 2013, 28 (02):93-98.
[10] 潘洵. 論重慶抗戰(zhàn)文化資源的特點(diǎn)、價(jià)值及開發(fā)思路. 重慶社會(huì)科學(xué), 2004(01):116-121.
[11] 歐陽(yáng)樺. 重慶近代城市建筑[M]. 重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0.
[12] 漆琴, 王政. 舊城改造背景下重慶抗戰(zhàn)遺址保護(hù)對(duì)策研究——以重慶1938·抗戰(zhàn)遺址公園為例 [J]. 四川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4, 24 (05): 22-26.
[13] 李明明. 重慶李子壩抗戰(zhàn)遺址公園開園[J]. 中國(guó)旅游報(bào), 2010-06-25 (003).
[14] 楊樂, 辜元, 李鵬. 重慶市危舊房改造片區(qū)中城市遺產(chǎn)的保護(hù)與利用實(shí)踐活動(dòng)解析[C]// 中國(guó)城市規(guī)劃學(xué)會(huì). 多元與包容——2012 中國(guó)城市規(guī)劃年會(huì)論文集(12. 城市文化),2012.
[15] 劉星滟. 傳統(tǒng)風(fēng)貌區(qū)景觀保護(hù)與活化設(shè)計(jì)研究[D]. 重慶工商大學(xué), 2023.
[16] 眾匯山城. 山城巷新生,保護(hù)規(guī)劃如何走進(jìn)現(xiàn)實(shí)? [EB/OL].(2021-12-03)[2021-12-03].https://mp.weixin.qq.com/s/hfGq0Y--uYI7rv6ZY4U8ZA.
[17] 眾繪山城. 山城巷保護(hù)更新記[EB/OL].(2021-12-03)[2021-12-03].https://mp.weixin.qq.com/s/c4gtEPPL2b1dwzTggXks5A.
[18] 歐陽(yáng)樺. 碼頭水岸下浩河街( 重慶)[J]. 重慶建筑, 2017, 16 (02): 65.
[19] 李向北, 李文霞, 辜志鵬, 等. 城市單元的重建與活化——以重慶龍門浩歷史街區(qū)拓展區(qū)為例 [J]. 城市發(fā)展研究, 2023, 30(10): 6-11+18.
[20] 眾繪山城. 長(zhǎng)江南岸“舊重慶的標(biāo)本”——下浩里老街[EB/OL](2023-10-01)[2023-10-01].https://mp.weixin.qq.com/s/XrhQ3hT4IigcAha33wQDow.
[21] 商界青年. 重慶下浩里|重塑老街新貌 打造青年綠洲. [EB/OL].(2024-08-06)[2024-08-06]. https://www.kanshangjie.com/article/183130-1.html.
[22] 毛燕 , 無二 , 左小朵 , 等. 老街巷的“逆生長(zhǎng)” 從時(shí)代里破冰的城市更新樣本 [J].城市地理, 2024(07): 6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