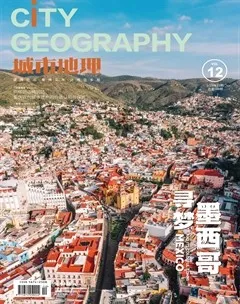內江走走停停 張大千的甜城往事




在自貢和樂山紛紛以美食“出圈”的當下,位居重慶、成都兩大城市之間中心地帶的內江,卻成了川渝地區(qū)存在感最低的小眾城市。與人們熟悉的熱辣川味不同,內江到處都有甜的痕跡,除此之外,這座實打實的“甜城”與“川南咽喉”,還孕育了中國近現(xiàn)代最偉大的國畫大師。
在川菜盛行全國后,香辣這個標簽早已成為整個川渝美食的代名詞。在大家的印象中,似乎只有冷鍋串串、麻辣香鍋、冷吃兔、水煮魚,這些花椒和辣椒鋪得滿滿一盆的江湖菜才是正兒八經(jīng)的川渝美食。以至于當大家吃到宮保雞丁時,深感疑惑:“川菜居然有甜的?”沒錯,宮保雞丁也是正宗的川菜,四川人吃甜,也是祖?zhèn)鞯摹V袊a(chǎn)糖七成在四川,而四川產(chǎn)糖七成在內江。在四川南部,這座彌漫著甜蜜氣息的城市——內江,被四川人親切地稱為“甜城”。
“內老三”的誕生
內江,原名中江,在隋文帝時期,為避太祖楊忠之諱,遂改名為內江。它位于四川盆地東南部沱江下游中段,東漢時建縣,曾稱漢安、中江,距今已有2000 多年的歷史。內江東鄰重慶,南界瀘州,西連自貢、眉山,北鄰資陽。它曾是蜀漢時期的軍事要地,歷經(jīng)千年滄桑變遷,依然保留著許多珍貴的歷史遺跡。
在冷兵器時代,一座城市修筑城垣的首要功能是為了防御外敵的入侵。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古內江恢復縣制,明朝成化元年(1465年)秋,漢安知縣謝熙奉令復修城垣,由原來的土墻改修為內填泥土,外圍砌石,高一丈七尺,厚一丈五尺,周長九厘三分,共有垛口3721 個,城垣內面積約一平方公里,并設立八個城門,東面正門稱朝東,副門為觀瀾;南面正門曰向南,副門為景陽;西正門呼鎮(zhèn)西,副門為通川;北面正門是拱北,副門為臨清。由此奠定了內江城墻的基礎。內江古城墻也成為中國現(xiàn)存保存最完整、規(guī)模最大的明清古城墻之一。
詩仙李白曾贈友人范金卿“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的名句,描述的就是悠悠沱江穿城而過的清新意境,句中“東城”正是內江城。自古以來,內江以舟楫為主要運輸方式,這使得內江沿岸的渡口日趨興盛。
那時,內江沒有橋梁,陸地交通不發(fā)達,人們往來貿易只能通過渡口過河。渡口又分設官渡、私渡、義渡,其中義渡為免費,內江東渡就是著名的義渡。從明朝開始,官紳捐資造舟,冬春搭浮橋,夏秋則安排了20 余艘義舟,通宵擺渡,因此民間也有“走遍天下路,內江好過渡”之說。據(jù)《內江地區(qū)交通志》記載:在秦漢時期,資陽、資中、內江城區(qū)的靠河沿岸已形成了物資集散港埠,兩岸石板鋪路,停滿了船舶,不同船隊在沿岸建倉,好不興盛。
要說沱江流域船隊最多的地區(qū),當屬內江一帶。每當夜幕降臨,許多船只前來停靠,沿江兩岸燈火輝煌。上百只船的工人在江河兩邊點著馬燈,頗有幾分“江楓漁火”的味道。這些船工也常到岸上購物,因為他們高頻次、大幅度的消費,東興老街的經(jīng)濟也得到了極大發(fā)展,甚至衍生了一些專門為船老板服務的茶館、酒家等。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與陸地交通的進步,20 世紀50 年代末期,全內江地區(qū)整頓渡口船舶,除保留少數(shù)義渡外,其余全部收費。后來機動船興起,木船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如今,東渡碼頭仍在經(jīng)營中,江面依舊波光粼粼,只是來往的不再是載滿貨物的老木船,而是極具現(xiàn)代感的觀光游船。
地處成都和重慶兩大城市之間的中心,扼守川東南乃至西南各省交通樞紐的“川南咽喉”內江,在經(jīng)濟發(fā)展上,曾一度成為四川盆地內僅次于成渝雙城的城市,“內老三”的名號也由此而來。它也是除成都、重慶外,四川省最早通鐵路、高速和高鐵的城市,在城市建設上很有韻味。由胡歌和高圓圓主演的電影《走走停停》,就曾在內江的西門橋疊象街等地方取景,若是看慣了成渝兩地的風景,不妨抽個周末去內江逛逛。
滲進骨髓里的“甜”
中國是世界最古老的三大甘蔗種植地之一。1716 年,福建人曾達一帶著甘蔗來到內江龍門鎮(zhèn),開啟了內江種蔗制糖的歷史。內江的土壤、水利、日照等地理條件優(yōu)越,有利于農作物生長,為內江種蔗制糖、發(fā)展糖業(yè),提供了良好的灌溉和運輸條件。《中國食糖史略》記載:“康熙年間,以沱江流域的內江地區(qū)為中心發(fā)展成為西南最大的糖業(yè)基地。”清末時期,內江就已經(jīng)有糖坊、漏棚3000 多家,“三里一糖坊,五里一漏棚”,當時的內江與福建、中國臺灣并稱為全國三大糖業(yè)基地。民國初期,內江制糖業(yè)達到歷史最高水平,糖產(chǎn)量占全川70%、全國50%。
《漢安竹枝詞》曾寫道:“天下蜜餞出漢安,人間美食在甜城。坊間婦孺煮蜜餞,始信漢安是甜城。”內江城東(今內江市東興區(qū))是唐代制糖中心。那時的產(chǎn)品單一,主要是黃糖和蜜餞。黃糖即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紅糖,內江人依據(jù)糖的顏色為其取名;蜜餞則以紅橘最具代表性。制作蜜餞時,選好大小合適的紅橘,用刀劃成八瓣,壓扁,之后用竹編成網(wǎng)狀筐,裝上兩百斤,沉入沱江優(yōu)質水段浸泡三天,目的是除去石灰;從江中取出紅橘后,再放入鍋中用蔗糖煮制成蜜餞,這種工藝一直傳到民國。到清末民初,內江的糖產(chǎn)品已經(jīng)非常多樣化了,有白糖、紅糖、冰糖、蜜餞(紅橘、柑磚、瓜果)、雜糖(糕點、切片和小食品)等幾類。
可以說,當時內江的經(jīng)濟發(fā)展正是依靠著制糖業(yè)拉動的。內江糖廠曾位居亞洲第三、西南第一,支撐和推動了內江的“三白經(jīng)濟”:白糖、白紙、白酒,不但增加了地方財政收入,對內江的城市建設和社會發(fā)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蔗糖業(yè)的發(fā)展也促進了內江金融業(yè)的繁榮。據(jù)1944 年統(tǒng)計,內江一地各銀行錢莊設有分行辦事處者多達41 家。這時的內江不僅是沱江流域的糖業(yè)中心,同時也是沱江流域的金融中心,影響力甚至一度超過成都和重慶,成為川內的重要經(jīng)濟中心。抗日戰(zhàn)爭時期,四川作為抗戰(zhàn)大后方,那時軍用和民用車輛汽油匱乏,大量使用酒精作動力,為解決抗戰(zhàn)緊缺物資的需求,從甘蔗中提煉酒精充當燃料,成為戰(zhàn)時的一項重要任務。國家的需要促進內江制糖業(yè)走到使用現(xiàn)代機器生產(chǎn)的階段,內江糖業(yè)也成為政府和社會資本投資的對象,得到迅速發(fā)展。
不過,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當?shù)鼐用竦奈镔|生活逐漸豐富,糖已不再是人人向往的稀有資源。內江糖業(yè)逐漸衰退,沱江河畔大片甘蔗林失去蹤影,失去貨源的糖廠與依靠甘蔗為原料的紙廠和白酒廠也陸續(xù)倒閉。內江,這個以糖為武器,對抗日戰(zhàn)爭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的城市,終于也要面對不可回避的時代傾軋。沱江兩岸望不到盡頭的甘蔗林,江岸碼頭來來往往的人群,絡繹不絕的船只,都漸行漸遠,為興盛了幾個世紀的內江糖業(yè)畫上了句號。但是,其留下的糖文化依然獨特而珍貴,甜蜜仍流淌在內江這座城市的血液里。
張大千夢中的遠方
談內江,除了繞不開的糖,更有一位繞不開的傳奇——國畫大師張大千。張大千可謂是中國近代畫史上屈指可數(shù)的罕見天才,也是最具爭議的國畫大師。他被西方譽為“東方之筆”,被徐悲鴻稱為“五百年來第一人”,無論山水、花鳥、人物、工筆、寫意、潑墨、書法無一不精。在多病纏身的晚年,他還獨創(chuàng)了極具震撼力的青綠潑彩畫法。張大千出生于內江,早期專心研習古人書畫,特別在山水畫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因思念故鄉(xiāng),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山水畫以慰鄉(xiāng)情。哪怕見過無數(shù)山水,他總忍不住將他鄉(xiāng)風景與故鄉(xiāng)比較,其中尤以《四川資中八勝》為最。一句“為寫資中八景,以慰羈情”,可見其思鄉(xiāng)情切。他甚至在家書中寫上“小園可以下榻,一切并如在內江也”。
盡管張大千年少就離家求學,但無論在哪里,他都是說一口地道的內江話。出國幾十年,沒有加入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國籍,始終是中國人,說中國話,吃中餐,穿傳統(tǒng)的中式服裝。對于終老他鄉(xiāng)的張大千而言,內江,是回不去的遠方。內江人也以“大千故里”為傲,從大千畫到大千菜,“張大千”的烙印在這座城市隨處可見可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內江人。數(shù)十年來,“張大千”三個字幾乎成為內江這座城市最耀眼的文化標簽。
張大千故居,原來叫張家院子,坐落于內江市市中區(qū)的半坡井。而今,張家老屋已不復存在,市中區(qū)政府在原址立碑“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出生地原址”。大千園是依沱江而建的一個山地公園,張大千故居在山腳,紀念館在半山腰,博物館在山頂處,層層遞進,讓人登高膜拜,宛若置身于他的山水畫中。
無論懂不懂書畫,張大千紀念館都是值得一去的景點。它是中國近現(xiàn)代畫家紀念館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個,以時間為線,以張大千的人生歷程為點,以五個單元為主題,勾勒出張大千從國畫大師成長為世界級繪畫大師的過程。淡雅的畫作,心魂的彌漫,讓游客在觀賞過程中可以走入大師的內心世界,就像讀一本名著,或許在當時并沒有什么觸動,但心境已在不知不覺中悄然變化。走出博物館再往上爬,山頂?shù)淖罡咛幱幸蛔髁止潘拢樦爬系氖A拾級而上,能感受到它的古樸莊嚴。站在寺廟門口,看著穿城而過的沱江,身后的西林寺就像佛的化身,端坐蓮花之上,慈愛地望著腳下的眾生,守護著內江的子民。
張大千在美食方面也很有研究,是一位當仁不讓的美食家。他調侃“以藝事而論,我善烹調,更在畫藝之上”,足見他對美食的熱愛。被評為“中國菜”四川十大經(jīng)典名菜之一的大千干燒魚,就是張大千的家傳菜,流傳至今,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內江飯店的招牌菜,是當?shù)厝朔浅O矏鄣拿牢都央取?/p>
編輯+ 李錦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