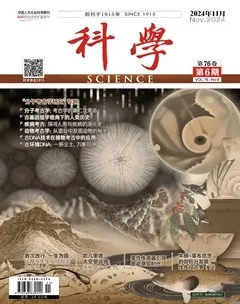中國蚯蚓資源與保護

蚯蚓是最重要的大型土壤動物類群之一,在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發(fā)揮著關鍵作用,被譽為“土壤生態(tài)工程師”。達爾文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腐殖土的形成和蚯蚓的作用》中,稱蚯蚓是“未被贊頌的生物,難以計數(shù)的它們改變了陸地”[1]。蚯蚓作為廣泛分布的大型土壤動物類群,不僅在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物質循環(huán)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還為農業(yè)生產和環(huán)境保護做出巨大貢獻[2,3]。
我國的蚯蚓物種多樣性十分豐富,而且分布廣泛,涵蓋了從炎熱的南方熱帶雨林到寒冷的東北地區(qū)的各種生態(tài)環(huán)境。然而,隨著農業(yè)發(fā)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的蚯蚓資源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
蚯蚓的物種多樣性與地理分布格局
世界蚯蚓物種多樣性與地理分布格局
目前世界上已發(fā)現(xiàn)的蚯蚓超過6000種。在分類學上,它們歸屬于環(huán)節(jié)動物門(Annelida)寡毛綱(Oligochaeta)下的單向蚓目(Haplotaxida)和正蚓目(Lumbricida),共有18個科,其中巨蚓科(Megascolecidae)、正蚓科(Lumbricidae)和真蚓科(Eudrilidae)是陸生蚯蚓中分布最廣的3個科,也是已知最大的3個蚯蚓類群[2]。巨蚓科的物種在1500種以上,主要分布在中國、東南亞、日本、韓國、朝鮮、澳大利亞、新西蘭,部分物種甚至廣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正蚓科和真蚓科已知的物種都在500種以上,前者主要分布在歐洲和北美洲,后者多見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熱帶非洲地區(qū)。
蚯蚓幾乎見于世界所有溫濕度合適的土壤中。然而,據(jù)2019年美國《科學》(Science)周刊一篇論文,全球蚯蚓的地理分布格局與其生存的土壤溫度和濕度密切相關[4]。
我國蚯蚓物種多樣性與地理分布格局
我國是全球蚯蚓物種多樣性最高的國家之一,已確認的蚯蚓有9科28屬700多種,包括許多特有種。我國的蚯蚓主要來自巨蚓科、鏈胃蚓科(Moniligastridae)和正蚓科,其中巨蚓科占我國已知蚯蚓物種總數(shù)的90%以上,是我國蚯蚓中最具優(yōu)勢的科[5]。巨蚓科的遠盲蚓屬(Amynthas)和腔蚓屬(Metaphire)為我國蚯蚓的絕對優(yōu)勢屬,占我國已知蚯蚓物種總數(shù)的88%以上;該科其他屬的物種較少,其中巨蚓屬(Megascolex)、環(huán)棘蚓屬(Perionyx)和多環(huán)蚓盲屬(Polypheretima)都只有1種,近盲蚓屬(Pithemera)有3種(僅在臺灣地區(qū)有記錄),而扁環(huán)蚓屬(Planapheretima)有4種。鏈胃蚓科在我國被記錄到的種數(shù)曾經并不多,不過近期的科技基礎資源調查表明,我國農田土壤中該科的杜拉蚓屬(Drawida)的種數(shù)被嚴重低估。
我國蚯蚓的地理分布受氣候、地形、土壤類型、水熱分布等自然環(huán)境因子的深刻影響,不同區(qū)域的蚯蚓在物種的數(shù)量和生態(tài)適應性上均表現(xiàn)出顯著差異。東北地區(qū)和華北地區(qū)氣候寒冷干燥,蚯蚓種數(shù)較少且多為廣布種,但通常具較強抗寒性和耐旱性,依賴夏季短暫的溫暖濕潤完成生長和繁殖,而在低溫的冬季通過休眠和其他適應性行為生存。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氣候溫暖濕潤,土壤類型多樣,為各種蚯蚓提供了理想的棲息地,因而蚯蚓種類較豐富,特別是在丘陵地帶。華南地區(qū)和西南地區(qū)氣候濕熱,植被豐富,山地和丘陵密布,是我國蚯蚓物種最多樣的兩個地區(qū),尤其是西南的山地和高原環(huán)境獨特導致蚯蚓高度特化。西北地區(qū)氣候干旱、降水稀少,因而蚯蚓分布相對稀疏,絕大多數(shù)為廣布種,通常對水熱條件不佳的環(huán)境也具較廣的適應幅度。
我國巨蚓科的種數(shù)分布總體呈現(xiàn)“南多北少”現(xiàn)象:大多數(shù)物種分布于溫濕條件較好的南方諸省,其中有4個省份(廣西、海南、臺灣和四川)都超過79種;整個北方僅記錄到13種,且多數(shù)是適應能力較強的廣布種。這種格局主要是由上述影響物種分布的自然環(huán)境因子不均勻造成的,但也可能與對北方蚯蚓的采樣活動較少有關[4]。至于位居我國蚯蚓種數(shù)第二、第三的鏈胃蚓科和正蚓科,由于迄今報道較少,其分布格局有待更多研究來探討。
研究者通過對我國蚯蚓進行系統(tǒng)調查,掌握不同蚯蚓類群的分布現(xiàn)狀,不僅可用于揭示蚯蚓的地理分布格局,還可結合氣候、分子序列等數(shù)據(jù),預測某些蚯蚓類群的潛在分布區(qū)及其分化、擴散趨勢。例如,2024年的一項研究整理了可入藥的參狀遠盲蚓(Amynthas aspergillum,藥品名為“廣地龍”)在我國(大陸地區(qū))的采集地點,發(fā)現(xiàn)它主要分布在北回歸線附近,這為后續(xù)探討該物種的演化歷程提供了科學基礎[6]。
蚯蚓的演化
世界蚯蚓演化簡史
寡毛綱的祖先歷史可追溯到約6億年前的地球生命快速輻射進化的前寒武紀時期。它們最早出現(xiàn)在潮濕的泥炭沼澤和淡水湖泊,然后逐漸演化出適應陸地環(huán)境的特征,大約在3.4億年前的石炭紀與蛭綱發(fā)生分化。此后,寡毛綱中的蚯蚓在漫長的地質年代里隨著大陸漂移和氣候變化擴散到全球各地,形成如今的地理分布格局。
雖然迄今尚無化石數(shù)據(jù)用于分化時間的校正,但依靠形態(tài)、分子序列和古地理歷史氣候數(shù)據(jù),也可對蚯蚓各類群的起源、分化與擴散等演化過程進行驗證與探討。研究者基于現(xiàn)有證據(jù)發(fā)現(xiàn),蚯蚓起源于泛大陸(Pangea,即聯(lián)合古陸)的南半球部分——岡瓦那古陸 [Gondwana,包括現(xiàn)在的印度半島、阿拉伯半島、非洲(除阿特拉斯山脈外)、南美洲(除西北部外)、澳大利亞和南極大陸],然后在侏羅紀到白堊紀時期傳播到勞亞古大陸(Laurasia,涵蓋現(xiàn)今北半球大部分陸地)。抵達勞亞古大陸的蚯蚓祖先在經歷二疊紀—三疊紀大滅絕事件和三疊紀—侏羅紀大滅絕事件后,分化出巨蚓超科(Megascolecidea)、正蚓超科(Lumbricoidea)和舌文蚓超科(Glossoscolecoidea)等超科,而巨蚓超科再向亞洲板塊和澳洲板塊擴散,又分化為巨蚓科等5個科[7]。
巨蚓科的起源時間可能在距今2.2億~1.1億年的侏羅紀時期,此時岡瓦納古陸還未發(fā)生分裂。該科在白堊紀后期出現(xiàn)科內分化。

鏈胃蚓科的種類主要分布在緬甸、印度尼西亞、印度和中國。它們和巨蚓科的種類都具有印度—馬來區(qū)的特點,可能有相似的起源和物種分化與擴散歷程[2]。
正蚓科起源于晚白堊紀的古北區(qū)歐洲板塊,它在我國分布的物種可能多為外來種[8]。
從形態(tài)上看,蚯蚓的祖先在從水體向陸地的演化過程中,挖掘洞穴的生存需要促進了體型的增大、前部隔膜的增厚、體壁肌肉組織的形成和消化器官的改變,進而影響了鄰近體節(jié)腔室中性器官的發(fā)展。當蚯蚓演化到陸棲生活階段,各科的種類為了適應不同的環(huán)境,各自演化出多樣的外部形態(tài)和內部結構特征。根據(jù)對地表土層特化的適應能力和生態(tài)服務功能,蚯蚓可被劃分為3種主要生態(tài)類型:表層種、內層種和深層種。或許是適應洞穴生活的一種進化,蚯蚓是動物界中為數(shù)不多的雌雄同體類群,同一個體往往兼有雄性生殖系統(tǒng)和雌性生殖系統(tǒng),而且孤雌生殖在研究較多的正蚓科和巨蚓科中比例較大[5]。
我國巨蚓科蚯蚓演化歷史

分布于我國的巨蚓科下的遠盲蚓屬和腔蚓屬的祖先大約在晚白堊紀末期到新生代(從距今6600萬年至今)初期起源于中南半島[4]。它們在晚白堊紀末期主要分布于現(xiàn)今云南或廣西所在位置,并分化為14個主要的進化類群。在晚白堊紀末期到新生代初期,這些進化類群主要在亞洲大陸內向北、向東擴散,逐步占據(jù)適合的棲息地。

我國島嶼上的巨蚓科蚯蚓祖先來自亞洲大陸。海南島的巨蚓科祖先大約在始新世初期(距今約5060萬年)從亞洲大陸擴散而來,先到該島南部,隨后主要在島內分化與擴散,少數(shù)物種的祖先又在始新世中期(距今約4213萬年)經陸橋擴散回大陸。臺灣島的巨蚓科蚯蚓的祖先主要來自亞洲大陸東南部,而臺灣海峽的陸橋在冰川作用活躍的更新世(距今約260萬~1萬年)周期性出現(xiàn),為臺灣島和亞洲大陸的一些物種提供了隔離演化的機會。
從總體演化歷程上看,我國的巨蚓科蚯蚓的演化時間不長,但新生代獨特的地理穩(wěn)定性為其演化出豐富的物種創(chuàng)造了客觀條件[5]。它們在新生代早期物種數(shù)目大幅增加,但在上新世后物種增速大幅下降,其原因既有可能是第四紀冰期造成的一些物種滅絕,也有可能是區(qū)域環(huán)境容納量趨于飽和,物種擴散、分化速率變緩。我國北方地區(qū)的蚯蚓物種很少且多是廣布種的原因,除前述的自然環(huán)境因子等,還與其演化歷史相關:據(jù)推測,我國北方原有蚯蚓物種多數(shù)已在第四紀冰期滅絕,僅有少數(shù)孑遺物種幸存下來,而現(xiàn)有的廣布種大多是在冰期后南方類群向北擴散的結果。
蚯蚓的生態(tài)服務功能與應用價值
生態(tài)服務功能
蚯蚓在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通過物理和生物活動,直接或間接影響土壤結構、肥力和生物多樣性;二是促進有機質的分解與轉化,調節(jié)陸地碳匯,對陸地生態(tài)系統(tǒng)具有深刻影響;三是研究土壤健康和生態(tài)服務功能的重要生物指示類群[3]。它們不僅是土壤健康的維護者,而且是生態(tài)系統(tǒng)可持續(xù)性的推動者。
蚯蚓的生態(tài)服務功能具體表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蚯蚓通過掘土和通氣活動,改善了土壤的物理結構。在蚯蚓活躍的土壤中,存在大量縱橫交錯、網狀的蚯蚓孔道。例如在法國1公頃草場土壤中,蚯蚓孔道總長度達4000~5000千米,而且這些孔道往往被蚯蚓糞粒(蚓糞,即排泄物)填充,蚓糞又互相堆疊形成許多非毛細管孔隙。網狀孔道和孔隙大大增強了土壤的通氣和透水能力,還增強了土壤的抗壓縮性,減少了表面徑流和侵蝕風險,有助于土壤儲水保水,為植物提供穩(wěn)定的生長環(huán)境。在極端氣候條件下,蚯蚓活動的作用更加突出。
其次,蚯蚓有助于促進土肥相融和提高植物營養(yǎng),維持土壤肥力。在歐洲的平原上,1噸深層種蚯蚓(相當于平均每公頃深層土壤中的蚯蚓生物量)每年吞食約250噸土壤,這對土壤中的有機質分解有巨大貢獻[7]:蚯蚓不僅將土壤中的有機質轉化為植物可吸收的養(yǎng)分(如氮、磷和鉀),還能促進有機質礦化,釋放出大量的無機養(yǎng)分,提高土壤的肥力水平。相關研究表明,在有微生物參與的情況下,蚯蚓明顯促進了土壤有機質和植物殘落物中的碳和氮的循環(huán)、轉化,增加土壤中可供直接利用的碳和氮。土壤中養(yǎng)分循環(huán)速度加快、有機質含量提高和土壤團粒結構改善,都可顯著提高農作物等植物的生長速度和產量。

再次,蚯蚓在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和食物網中發(fā)揮重要作用。一方面,蚯蚓的活動為其他土壤動物和微生物創(chuàng)造棲息的空間,影響土壤中其他生物的分布,增加土壤生物的多樣性。對天然草場的研究發(fā)現(xiàn),約50%的土壤固氮菌集中于蚯蚓孔道的壁上。另一方面,蚓糞富含有機質和微量元素,促進了土壤微生物的繁殖和活性,增強了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健康。此外,蚯蚓被土壤中和地上的許多肉食性和雜食性動物(如野豬、刺猬、狗獾、烏鶇)取食,成為這些動物重要的食物來源,以及整個食物網的重要組成部分。
應用價值
作為生物指示類群 蚯蚓對污染物(重金屬、農藥等)具有較高的敏感性,常被用作土壤污染的生物指示類群。通過監(jiān)測蚯蚓種群的健康和數(shù)量變化,可以評估土壤污染的程度和影響。
用于生態(tài)修復 蚯蚓在生態(tài)修復中的應用日益受到重視。在退化土壤的修復過程中引入合適的蚯蚓物種,可有效恢復土壤的結構和功能。這樣的技術不僅適用于農業(yè)土壤的恢復,還可用于工業(yè)污染地和礦區(qū)的生態(tài)修復。
用于農業(yè)生產 蚯蚓在農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中的價值已得到廣泛認可。通過推廣蚯蚓堆肥技術,可將農業(yè)廢棄物和有機垃圾轉化為高質量肥料,減少對化肥的依賴,提高土壤有機質含量。蚯蚓堆肥不僅富含植物生長所需養(yǎng)分,還含有大量有益微生物和生長激素,幫助作物生長。同時,蚯蚓還可減少農田中有害生物數(shù)量,降低農藥使用量,有助于實現(xiàn)可持續(xù)農業(yè)。
藥用 蚯蚓在醫(yī)藥領域的應用歷史悠久,具有重要的藥用價值。在我國傳統(tǒng)醫(yī)學中,蚯蚓的干燥體被稱為“地龍”,是一類重要的中藥材,具有清熱、解毒、利尿和消炎等治療功效。2020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收錄了4種巨蚓科的“地龍”藥材,分別為參狀遠盲蚓、櫛盲遠盲蚓(Amynthas pectieniferus)、威廉腔蚓(Metaphire guillelmi)和通俗腔蚓(Metaphire vulgaris),其中后三種被稱為“滬地龍”。
近年來,蚯蚓的藥用價值逐漸被現(xiàn)代醫(yī)學所認可。例如,蚯蚓體內富含的蚓激酶具有顯著的抗凝血、降壓和抗炎作用,已在治療心血管疾病、炎癥性疾病等方面展現(xiàn)出良好的效果。需要注意的是,上述4種藥用蚯蚓都被列入《有重要生態(tài)、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三有”動物名錄),其野生種群受到國家保護。對于藥用的“地龍”的市場需求,當前基本上可通過較成熟的人工養(yǎng)殖得到滿足,不應且不再需要掠奪野生蚯蚓資源。
經濟價值 蚯蚓在藥用之外的直接經濟價值逐漸被發(fā)掘和利用。一方面,蚯蚓軀體富含優(yōu)質蛋白質、脂肪和氨基酸,不僅是理想的動物飼料添加劑,而且可被加工成各種有機產品,在保健品、化妝品和食品添加劑等領域具有廣闊的市場前景,甚至直接作為人類食品。另一方面,蚓糞是一種高質量、對環(huán)境友好的有機肥料。
現(xiàn)階段蚯蚓面臨的威脅
盡管蚯蚓對生態(tài)系統(tǒng)和人類社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如今面臨著多重威脅。
一是蚯蚓的自然棲息地急劇減少。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被轉化為道路、建筑物等密實的硬質結構,使得蚯蚓的生存環(huán)境惡化,種群數(shù)量顯著下降。棲息地喪失對一些本地蚯蚓物種的生存構成嚴重威脅,尤其在城市周邊地區(qū),蚯蚓的多樣性和數(shù)量都呈現(xiàn)下降趨勢。
二是人類生產生活的污染對蚯蚓的生存帶來的巨大挑戰(zhàn)。農業(yè)大量使用的化肥、農藥和除草劑,不僅直接毒害蚯蚓,還通過污染土壤和水體間接影響蚯蚓的生存和繁殖。工業(yè)排放和礦業(yè)活動產生的重金屬(如鉛、鎘和汞)會在土壤中積累,通過食物鏈逐步危害蚯蚓的健康。

三是氣候變化對蚯蚓的顯著影響。全球氣溫的升高和降水模式的改變,可能導致蚯蚓棲息地的縮小或消失。此外,在極端天氣事件頻發(fā)的局部地區(qū),蚯蚓也面臨嚴峻的危機:極端干旱可能導致土壤水分迅速蒸發(fā),使得蚯蚓難以維持正常的生理活動;頻繁的暴雨和洪水可能導致土壤氧氣減少,影響蚯蚓的呼吸,甚至導致其因窒息而死亡。
四是過度捕捉嚴重威脅蚯蚓資源。一方面,“地龍”因其在中藥領域的廣泛應用而被非法大量捕捉,這不僅往往超出這些蚯蚓野外種群自身的更新能力,而且還間接威脅到同域分布的其他蚯蚓種類。另一方面,因經濟價值升高,近年來出現(xiàn)通過電擊違規(guī)捕捉蚯蚓的現(xiàn)象,不但導致局部地點內所有蚯蚓的數(shù)量銳減,還嚴重破壞了土壤食物網,影響了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健康和肥力。
五是外來蚯蚓對我國蚯蚓造成的沖擊。外來蚯蚓通常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和適應性,能在較短時間內在本地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中占據(jù)主導地位。例如,來源于中美洲的舌文蚓科南美岸蚓(Pontoscolex corethrurus)在我國北回歸線以南區(qū)域已表現(xiàn)出較強的適應能力,逐漸取代當?shù)氐尿球荆е峦寥澜Y構、物質循環(huán)和動植物多樣性格局等方面的改變。控制外來物種的擴散是當前蚯蚓保護的一大挑戰(zhàn)。
蚯蚓的保育與可持續(xù)利用策略
面對日益嚴峻的各種威脅,保護蚯蚓已成為刻不容緩的任務。為了蚯蚓資源的可持續(xù)利用,我國宜采取一系列綜合措施。
第一,國家在政策和法規(guī)層面的蚯蚓保護措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即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規(guī)定:“嚴厲打擊盜挖黑土、電捕蚯蚓等破壞土壤行為。”國家林業(yè)和草原局在2023年,首次將4種藥用蚯蚓納入“三有”動物名錄,因而擅自捕捉“地龍”將面臨經濟處罰甚至刑事處罰的風險。
第二,蚯蚓棲息地的保護。在城市規(guī)劃和土地利用政策中,有關部門應考慮到對蚯蚓棲息地的保護,避免不必要的土壤破壞和污染。同時,在珍稀和特有的蚯蚓集中分布地點建立自然保護區(qū)尤為重要,不僅可為蚯蚓提供安全的棲息地,還能作為開展相關科學研究的基地,甚至成為未來物種恢復的重要種源地。
第三,在農業(yè)生產中推廣生態(tài)友好型耕作方式至關重要。這種方式要求減少對化肥和農藥的使用,采用有機農業(yè)技術,保護或恢復土壤的自然屬性。如果農業(yè)部門鼓勵使用蚯蚓堆肥等有機肥料,可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促進蚯蚓的繁殖和生長。
第四,科學研究和公眾教育是蚯蚓保護中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之一。全面、深入的科學研究將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我國蚯蚓的本底情況和對環(huán)境變化的響應,為制定有效的保護措施提供科學依據(jù)。公眾教育可提高人們對蚯蚓及其生態(tài)價值的認識,促使更多的人參與蚯蚓保護行動。
第五,發(fā)展和推廣蚯蚓相關產業(yè)有助于蚯蚓資源的可持續(xù)利用。蚯蚓養(yǎng)殖作為一種新興產業(yè),猶如農業(yè)生產助推器,不僅可為農業(yè)種植提供高質量的有機肥料,同時為水產養(yǎng)殖業(yè)提供優(yōu)質的蛋白質飼料,還可滿足醫(yī)藥、保健品、食品等行業(yè)對蚯蚓產品的需求,從而帶動一系列產業(yè)的發(fā)展,促進農民就業(yè)與增收、農村經濟發(fā)展。更重要的是,人工養(yǎng)殖可用于替代野生捕捉,從而保護野生蚯蚓。
蚯蚓不僅是一類生物資源,更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環(huán)境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實施科學、合理的措施,我們可有效地保護這些土壤生態(tài)工程師,維持健康的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以便它們充分發(fā)揮其不可替代的生態(tài)服務功能。同時,通過推進蚯蚓資源的可持續(xù)利用,有利于社會的綠色發(fā)展和環(huán)境的改善,長遠造福社會。
[1]Darwin C R. The formation of vegetable mould through the action of worms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ir habits. London: Ed. John Murray and CO., 1881: 1–326.
[2]陳義. 中國蚯蚓.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56.
[3]邱江平. 蚯蚓與環(huán)境保護. 貴州科學, 2020, 18(1-2): 116–133.
[4]Phillips H R P, Guerra C A, Bartz M L C, et al. Global distribution of earthworm diversity. Science. 2019, 366: 480–485.
[5]蔣際寶, 邱江平. 中國巨蚓科蚯蚓的起源與演化. 生物多樣性, 2018, 26 (10): 1074–1082.
[6]Li J L, Jiang J B, Jin Q, et al. 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reflects high genetic divergence of Amynthas aspergillum (Oligochaeta: Megascolecidae) in southern China. Ecology and Evolution, 2024, 14: e11452.
[7]Bouché M B. The establishment of earthworm communities // Satchell J E (eds). Earthworm ecology.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1983.
[8]Qiu J P, Bouché M B. Révision des taxons supraspécifiques de Lumbricoidea. Documents pédozoologiques et intégrologiques, 1998, 3: 179–216.
關鍵詞:蚯蚓 物種多樣性 地理分布格局 演化 生物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