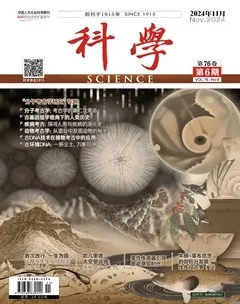呂彥直與中國科學社
呂彥直(1894—1929)是中國現代杰出的建筑師,尤以設計、監造了南京中山陵和主持設計了廣州中山紀念堂而名垂后世。盡管在呂彥直辭世后他的名字很快湮沒在歷史的煙塵中,但是1980年代后期,他的事跡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關于呂彥直生平、求學經歷、職業生涯和建筑思想的研究不斷豐富,代表性的成果有盧潔峰著《呂彥直與黃檀甫——廣州中山紀念堂秘聞》《廣州中山紀念堂鉤沉》《中國近現代建筑奠基人:呂彥直傳》,殷力欣編著《建筑師呂彥直集傳》,賴德霖著《閱讀呂彥直》,達志翔、周學鷹著《中國近現代建筑奠基人:呂彥直研究》等。鮮為人知的是,呂彥直在其短暫而燦爛的人生中不僅為探索中國建筑的新民族風格而殫精竭慮,他還一度結緣中國科學社及該社創辦的《科學》雜志,在中國現代科學啟蒙中留下了鮮明的印記。本文試述其詳。
入股中國科學社,成為中國科學社的早期社員
呂彥直是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留學期間結緣中國科學社的。
1911年,清華學堂初設,呂彥直經考試就讀于清華學堂留美預備部,1913年畢業。1914年,呂彥直獲庚款資助留美,入康奈爾大學,“初習電學,以性不相近,改習建筑”[1]。

就在呂彥直啟程赴美的前夕,先期赴美留學的任鴻雋、胡明復、過探先、趙元任等于這一年的夏天在康奈爾大學校園發起成立了中國科學社(此時名科學社,1915年10月25日改組為中國科學社,本文統稱中國科學社)——一個旨在通過出版和發行《科學》雜志,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為宗旨的“興趣小組”。此時的中國科學社還不是一個學術團體,它深受國內實業救國思潮的影響,采取股份公司形式,以股金作為出版和發行《科學》雜志的資本,把《科學》作為一種實業來經營,“股東有享受贏余的權利”。按《科學社招股章程》,中國科學社資本暫定400美元,發行股份40份,每份10美元,其中20份由發起人承擔,其余20份發售[2]。呂彥直雖然與中國科學社的動議與成立失之交臂,但是他還是趕上了中國科學社的第一次招股,并參加了目前發現的中國科學社的最早合影[3]。根據中國科學社“認股一覽表”[4],中國科學社有股東76人,認股106份,呂彥直認1股。根據中國科學社“交股一覽表”,呂彥直分別于1914年11月8日(5美元),1915年2月2日(3美元)、6月8日(2美元)分3次交齊了股金10美元。
對中國科學社“認股一覽表”和“交股一覽表”等檔案資料加以研究不難發現:①并不是所有的認股者都很快兌現了“諾言”,有的取消部分股份,如馮偉和劉鞠可本來各認2股,1915年5月各取消1股;有的僅交部分股金;有的完全沒交。這些變化或許與認股者的經濟狀況有關,也可能與他們在熱情冷卻之后的再思考有關。②呂彥直第一次交納股金的時間是1914年11月8日,此時他抵美僅2個月,剛剛踏入康奈爾大學校園,足以說明他對中國科學社宗旨的認可和積極響應。③不少人(包括呂彥直在內)是分多次交清股金的。我們不妨略微分析一下當時10美元的“含金量”。當時,“清華獎學金一個月只有六十元,全部開支(包括學費)在內”[5],對于幼年失怙、家道中落的呂彥直來說10美元確實不是一個小數目。趙元任回憶中國科學社剛成立時一些人試圖從牙縫里省出錢來支持它,有段時間他自己“以湯和蘋果餅作午餐,以致得了營養不良癥”[5];他還參與了同學J. C. S. Tung發起的吃經濟飯比賽,“有一次一天吃五角錢,另一次吃三角五,不久我們兩人全都得了感冒而病倒”[5]。因此,呂彥直分3次交清10美元股金亦在情理之中(可作為參照的是胡適認1股,亦分3次交清)。
中國科學社“交股一覽表”截止時間是1915年7月3日,列有交納股金者65人,呂彥直名列其中,因此呂彥直是中國科學社的創始股東和早期社員。根據《科學社股東姓名住址表(1914年8月)》[4],呂彥直的社員號為33。《科學》雜志1916年第一期發布的社友錄亦有呂彥直的信息,筆者收藏的1921年刊《中國科學社社錄》和1924年刊《中國科學社社錄》上均載有呂彥直的信息。《科學》雜志在創刊初期舉步維艱,常“因印刷需費甚巨,不敷支用”,呂彥直多有捐助。根據“中國科學社股東股金處理情況表”[6],呂彥直將其股金中的5美元轉換為“特別捐”;根據《科學》雜志1917年第一期發布的《會計報告》, 1915年10月(中國科學社改組)前,“特別月捐”6美元,中國科學社改組后,“特別月捐”8美元,合計14美元;根據《科學》雜志1918年第一期發布的《會計報告》,第一次常年會后、第二次常年會前,“特別捐”4美元。這些錢款也許微不足道,卻表達了他對中國科學社未來發展的堅定信心和奉獻。
擔綱《科學》編輯,編譯撰寫科學文章

楊銓擔任《科學》雜志的第一任編輯部長,他本有從事報業的經歷,在課堂上學得的管理知識在《科學》雜志的運營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編輯部辦事規則就如科學實驗,由簡陋的起點到現在的地位,隨時改良,不拘舊例”。由他為首制訂的《科學月刊編輯部章程》,明確了編輯部的組成、 職責、任期及部內分工。
編輯部的部員分為兩種,一種是“編輯員”,另一種是“撰述員”。“凡社員擔任本期刊編輯事務者為編輯員”,“凡社員自愿擔任本期刊文字,經本編輯部認可者為撰述員”。呂彥直首先是一名“編輯員”。《科學》雜志創刊的第一年即1915年,編輯部職員有11人,他們是任鴻雋、呂彥直、何運煌、周仁、胡明復、唐鉞、陸鳳書、楊銓、廖慰慈、趙元任和錢治瀾。第二年增至42人,呂彥直仍然名列其中。“編輯員”團隊又有角色細分,設修辭員、名詞員、圖畫員、校讀員、印式員各若干名,其中“設圖畫員一人或一人以上,專司選擇審定本期刊中圖畫……有時撰述員須用圖畫,不能自繪者,得以鉛筆圖樣交圖畫員代繪”。具備美術功底的呂彥直,當為《科學》編輯部編輯員中的“圖畫員”。呂彥直也是一名“撰述員”,他在繁忙的課業之余積極編譯外國科學著作。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正酣,《科學》編輯部將第一卷(1915年)第四期命名為“戰爭號”。呂彥直在這一期翻譯發表了《海底水雷》一文。通過這篇文章,呂彥直向國內讀者介紹了水雷、魚雷的研發過程,講述了水雷、魚雷如何從不為人知,不為人用,到日俄戰爭時一躍而為海戰明星,直至成為與戰艦、巡洋艦等并駕齊驅的攻擊性武器裝備的歷史。以筆者之見,呂彥直之所以選擇編譯《海底水雷》一文,與其出生于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年,其父呂增祥曾經供職于北洋水師營務處,又于甲午戰爭前出使過日本,與其家庭有多重關系、對其成長有重要影響的嚴復曾任職海軍界等背景有關。此文或許蘊藏了呂彥直在一戰已經爆發、中國面臨日本敲詐威脅之際,提醒國人必須重視海防,重視水雷、魚雷的研發,在海戰再次到來時積極應對,避免重蹈甲午海戰覆轍的苦心。
1915年,呂彥直在《科學》第一卷第十一期編撰發表了《愛迭生年譜》。在這篇文章中,呂彥直高度概括了愛迭生(今譯“愛迪生”)的主要經歷和代表性發明成果,其科學救國之意不言而喻。上述兩篇文章遣詞用字均精準簡約,頗有“呂彥直風格”。
探究張衡地動儀的復原,繪制發表復原模型圖片

我國東漢時期的科學家張衡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驗震器——地動儀。張衡地動儀制成后,因淪落亂世而不知所終,其制作遂成千古之謎。北齊時的《器準》和隋代初年的《地動銅儀經》中還記載有地動儀的圖式和制法,后來這兩本書亦遭亡佚。自宋代開始,中外學人憑借《后漢書·張衡傳》196字的記載,對張衡地動儀之功用多有爭論,亦有復原其原貌的嘗試。英國礦物學家、現代地震學的奠基人米爾恩(J. Milne)在1879—1893年研制地動儀,他和在日本工作的英國工程師尤因(J. A. Ewing)仿照張衡地動儀的懸掛擺驗震器,首先制作了第一臺懸垂擺地震儀。呂彥直是近代以來第一位探究張衡地動儀復原工作的中國學者,他根據米爾恩的設計,參考《后漢書·張衡傳》的記述,對米爾恩復原的地震儀進行了藝術裝飾,對部分結構做了補充,例如對儀器臺座和圖案布置進行了補充和修整。[7]呂彥直繪制的張衡地動儀復原模型圖片于1917年首次發表于《科學》第三卷第九期,1935年《科學》雜志第十九卷各期又使用該圖片作為封面。
設計中國科學社社徽,為中國現代科學啟蒙留下經典記憶
呂彥直的設計才華亦曾應用于中國科學社的社徽設計。此項工作的緣起當追溯到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常年會的籌辦。西方社會擁有悠久的徽章文化,常常用作榮譽標識和標明佩戴者的身份。在美國,大學、學會和協會等組織一般都擁有一枚專屬的展示自我形象的徽章。得歐風美雨之吹沐的中國科學社發起者自然也會想到為其社員設計一枚表征身份的徽章。事實上該計劃付諸實施了。在1916年9月2—3日舉行的第一次常年會的“預備應用物件”中就有供到會社員佩戴的“佩章”。“所用佩章式樣,由社員呂彥直君打樣,惟以未經本社之正式承認,所用式樣僅為暫時之用。”[8]這枚徽章的實物及圖案目前雖未得見,但是根據中國科學社檔案解讀,其主要思想和圖案在社徽定稿方案中得以繼承。

1916年9月2日上午,第一次常年會召開社務會,其中“提議事件”的第一項就是社徽問題:“社長請眾先決本社采用徽章與否。鐘心煊君提議本社應用徽章,眾一致贊成。論及徽章格式,眾意似欲用兩種。一種較大者可于本社圖書上作為蓋印,或于開常年會時可佩于衣衿,一種較小者則可作為佩簪或社匙之用。因此事一時不能詳定,孫學悟君遂提議由董事會委任熟悉此事者之人詳細研究后報告本社,眾一致贊成。”[9] 13日,中國科學社董事會根據此次常年會的議案成立了一個“三人小組”,以推進社徽設計。“本社徽章,照常年會議案應由董事會派特別委員三人,畫成大小兩種圖式,以待來年常年會公決。民國五年九月十三日董事會開會,指定周仁、廖慰慈、呂彥直三君為本社徽章圖式委員。”[10]
1917年9月6—7日,中國科學社在美國羅得島州布朗大學召開第二次常年會。在9月7日上午舉行的第二次會議的第四項議程是“討論社徽”,會后發表的《第二次常年會記事》對此記述尤詳:“社長言社徽問題去年常年會討論未得結果。原樣為呂君彥直所制,去年常年會所用會徽即此樣也。今年董事會復請呂君加制新樣數種合去年原制以備今年常年會采擇。言畢以社徽樣本傳觀會眾。楊銓君言原樣極確當大方,似宜采用,且去年用為常年會徽,用者并無不滿意之處。動議仍用舊樣,大多數同意。侯德榜君言‘科學社’三字凡橫書時皆由左向右,舊社徽獨由右向左,宜改。王孝豐君主張由右向左,謂與中國文字書法同向。社長付表決,眾贊同侯君言由左向右。所制樣中另有一小者作篆文‘科學’兩字,以為佩針之用。趙元任君言此樣甚佳,惟形宜略小,且‘科學’下應加‘社’字,眾同意通過。”[11]

以上會議記錄,坐實了以下歷史:
(1)呂彥直是中國科學社社徽的設計者。《第二次常年會記事》所謂社徽“原樣為呂君彥直所制”,“原樣極確當大方”,“動議仍用舊樣,大多數同意”等已很確鑿。當前為公眾熟知的中國科學社社徽當在呂彥直方案的基礎上修訂而成。
(2)第二次常年會還確定了一枚形狀小巧、篆書“科學社”三字,供“佩針之用”的社員徽章方案。這枚徽章應該是“三人小組”集體創作的結果。惜流年風雨,物不堅固,這枚徽章的樣式目前已失考。
1929年3月18日,呂彥直英年早逝,中國科學社發布《呂古愚略傳》,稱頌呂彥直擔綱的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設計,“以西洋物質文明,發揚中國文藝之真精神,成為偉大之新創作”,又為其“劬學成疾”,不幸逝世而惋惜[1]。斯人雖已長逝,但他在中國現代科學啟蒙中留下的印記仍新鮮如昨。
[1]呂古愚略傳. 科學, 1929, 14(3): 455-456
[2]曹伯言. 胡適日記全編. 第1冊.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307
[3]趙新那, 黃培云. 趙元任年譜.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8
[4]林麗成, 章立言, 張劍. 發展歷程史料.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5: 6
[5]趙元任. 趙元任早年自傳. 長沙: 岳麓書社, 2017
[6]中國科學社股東股金處理情況表. 科學, 1917, 3(1): 108-111
[7]王振鐸.張衡候風地動儀的復原研究. 文物, 1963, (2): 1-9
[8]常年會干事報告. 科學, 1917, 3(1): 123-129
[9]常年會紀事. 科學, 1917, 3(1): 69-88.
[10]中國科學社紀事. 科學, 1916, 2(12): 1366-1368
[11]楊銓. 第二次常年會記事. 科學, 1918, 4(1): 48-68.
關鍵詞:呂彥直 中國科學社 《科學》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