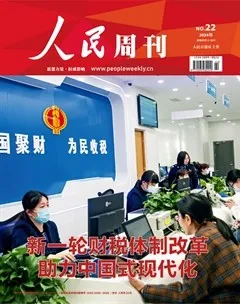把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著力點
從助力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把握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有關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特殊背景值得特別關注。這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先提出,繼而2024年3月的全國兩會再次重申,再到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系統部署。也就是說,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全國兩會再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經過近七個月的時間完成了系統部署。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年度工作會議和專題工作會議,主要任務有兩條:總結上一年的經濟工作,部署下一年的經濟工作。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是事關黨和國家事業全局的改革,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包括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各個方面。雖不能說財稅體制改革只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但從其不同于以往的行動路線可以看出,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提出、醞釀、謀劃以及具體部署,首先是和經濟問題相關,首當其沖是解決經濟領域的問題。
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有兩個重要論斷:其一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其二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這明確無誤地表明,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鞏固和增強經濟穩中向好態勢,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概括起來講,就是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
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首次把預期特別是預期轉弱問題引入宏觀經濟決策的視野,讓我們從過去的需求管理、供給管理擴展到了預期管理。在那之后,特別是2024年以來,預期問題一直成為宏觀經濟決策中的重要線索。
從2023年年末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2024年3月舉行的全國兩會,圍繞2024年經濟工作所做出的一個不同于以往的重要要求是,“多出有利于穩預期、穩增長、穩就業的政策”。對比此前“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的表述,可以發現兩個突出變化:其一是穩預期替代穩物價;其二是穩預期超越穩就業、穩增長,躍居三穩之首。兩個方面的突出變化告訴我們:今天的中國,宏觀經濟治理的重心或者經濟工作的重心之一是穩預期。
2024年9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推出了一攬子增量政策。我們發現,增量政策相對于過去的存量政策雖都屬于擴張性政策、刺激性政策,但增量政策的刺激和存量政策的刺激相比,有一個非常鮮明的變化,那就是增量政策在注重擴需求的同時也注重穩預期。也可以說,增量政策是從穩預期和擴需求的雙重維度加以部署的。
考慮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部署,圍繞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藍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健全預期管理體制。
當前中國經濟工作和中國宏觀經濟治理工作面臨最嚴峻、最復雜的挑戰,也是學術界應當研究的問題,就是要集中體現一個“兼”字——目標要兼容。不管出臺什么樣的政策,采取什么樣的舉措,都要兼容擴需求和穩預期,不能只顧擴需求,不管穩預期。功效上要標本兼治,不能只治標不治本。這就需要改革與政策雙引擎同向發力,助力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與改革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應該也必須是互補關系。刺激政策不論屬于逆周期還是跨周期調節政策,都少不了“周期”二字。一說到周期,就都是短期的,長期的問題靠什么解決?唯有改革。
經濟運行中同時存在三個方面的矛盾,需求層面的矛盾、供給層面的矛盾、預期層面的矛盾,單純的刺激政策所解決的更多的是需求層面的矛盾,預期層面的矛盾靠什么辦法解決?歷史經驗反復提醒我們,擴張性財政政策是正向作用和負向作用兼而有之,不能在注重正向作用的同時忘掉負向作用,而負向作用是需要改革加以抵消的。政策如果缺少改革的支持,不僅難以真正落地,也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就當前情況而言,主要有幾個方面應該盡早進入我們的研究視野:
一方面,史上最大規模的化債。這對當前的中國經濟無疑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常識告訴我們,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運行規律告訴我們,如果在化債的同時不輔之以央地財政關系的改革,完全有可能重復歷史上曾反復出現的軌跡。
另一方面,圍繞財政出臺更多、更大規模的擴張政策以促進消費、擴大消費的呼聲頗高,這無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要在調節收入分配和調節財富積累方面發揮作用,需要我們在稅收制度建設上補足短板。不僅個人所得稅制度需要調整,而且財富積累環節的稅收也要補足。這是建立現代稅收制度的重要出發點和落腳點之一,我們也不能不去研究。
除此之外,一系列圍繞財政如何支持投資擴大的政策建議,特別是支持民營經濟投資的建議,當然也是應當考慮的。但如果同時不輔之以財稅體制營造一流營商環境的改革措施,這樣的建議也難以真正落到實處,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局面。
總之,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主要著力點應當也必須是,以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助力財政政策調整,從而助力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本文為作者在第八屆財經發展論壇上的主旨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