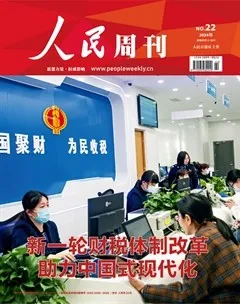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與提高國家財政能力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擘畫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戰略部署,核心是健全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完善財政關系。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為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建立穩固、平衡、強大的財政”,提高國家財政能力無疑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題中之義和必然要求。
我把國家財政能力簡單地分為三種,即財政汲取能力、財政治理能力和財政調控能力,三者相互依存,財政汲取能力是本源。在此,我僅從財政收入的角度來分析財政能力。從某種程度上說,財政收入規模可作為衡量財政汲取能力的代理指標,稅收收入和直接稅收入規模可作為衡量財政治理能力的代理指標,個人所得稅收入規模可作為財政調控能力的代理指標。
一、財政汲取能力
財政收入規模可以說是反映財政汲取能力的最直接、最簡單的量化指標。為了在比較分析時具有可比性,以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會保險基金預算等“四本預算”當年收入占GDP比率(以下簡稱“財政收入比率”)來度量財政收入規模。2013—2022年,我國財政收入比率從35.7%降至30.4%,2022年比2013年下降了5.3個百分點,或者說,財政收入比率降低了近15%。相比之下,同期11個中高收入國家平均從32.7%微增至33.5%,27個最發達國家平均保持在42%左右。
近十年來,我國財政收入比率明顯降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積極財政政策落到實處、卓有成效的重要體現。為了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新發展格局,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更多地轉向了改善供給側、減輕微觀經濟主體負擔、激發微觀經濟主體創新活力,從“減稅降費”到“減稅降費+緩稅緩費”再到“減稅降費+緩稅緩費+留抵退稅”,“稅費優惠政策步步加力、不斷擴圍”。2013—2022年,累計新增減稅降費和退稅緩稅緩費超13萬億元。這種空前的、大規模的、制度性減稅降費政策無疑會導致財政收入比率或我們日常說的“宏觀稅負”降低。
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進程中,“宏觀稅負”需要保持總體穩定甚至應有所提高。首先從國內發展需要來看:第一,減稅降費的邊際效應可能在遞減甚至可能只存在我所謂的“甜點效應”;第二,大規模減稅降費無疑要與財政可持續性(或者說財政承受能力)統籌考量;第三,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然需要一定的財政實力。其次從國際比較來看,前述數據表明,2022年發達國家平均財政收入比率高出我國11.6個百分點,發展水平接近的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財政收入比率也高出我國3.1個百分點。基于這些有待論證的簡要敘事和簡單的數據對比,不難看出,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進程中,要加強財政汲取能力建設。
二、財政治理能力
國家預算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一環,更是財政治理的主要載體。從國家預算角度來看,我國預算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因此,財政收入體系便由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收入構成。這四類收入的本質區別在于國家獲取收入的依據不同,可粗略地分為憑借政治權力、行政權力、財產權力。倘若將上述“四本預算”收入綜合起來大致分為兩類的話,一類是稅收收入,另一類是非稅收入。稅收收入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主體,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其余部分加上其他“三本預算”的收入可統稱為非稅收入。
稅收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取得收入,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從某種意義上說,稅收形式的法治性要強于其他財政收入形式,故在現代社會才有稅收法定主義之說。若以財政收入形式的法治性作為衡量財政治理能力的一個代理指標,那么,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下簡稱“稅收收入比重”)越高,在一定程度上就表明財政收入體系的法治性越強,財政治理能力越強。就此指標而言,如果與2022年38個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80%)相比,我國的稅收收入比重顯得比較低(57%)。因此,在落實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各種舉措時,需要關注稅收收入比重的變化。
同時,直接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下簡稱“直接稅收入比重”)越高,也可能預示財政治理能力越強。眾所周知,以稅收負擔是否能轉嫁為大致標準,稅收體系可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對于直接稅,納稅人通常無法將稅收負擔轉嫁出去,更直白地說,納稅人能直接感受到稅收負擔,或者說稅收感知度比較高。所以,直接稅收入比重的高低,不僅反映出經濟發展和稅收征管水平,也能反映出稅收道德和稅收文化水平,而稅收道德和稅收文化水平的高低蘊含著財政治理能力的強弱。從2022年的情況來看,我國直接稅收入(含社會保險費)比重為42%,比38個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59%)低近28%。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提高直接稅收入比重依然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
三、財政調控能力
這里所說的財政調控能力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穩定宏觀經濟能力,二是公平收入分配能力。如果僅從財政收入角度而言,這兩種能力都與財政收入體系的累進性有關,而財政收入體系的累進性主要取決于個人所得稅的超額累進稅率機制和收入規模。當這兩個條件得到充分滿足時,個人所得稅不僅能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助推宏觀經濟穩定運行,還能使可支配收入合理分布,有助于公平收入分配。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個人所得稅收入比例越高,穩定宏觀經濟能力和公平收入分配能力越大。
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的是超額累進稅率,比如綜合所得適用7級超額累進稅率,從3%至45%。應當說,個人所得稅稅率級次比較多,最高邊際稅率也不低,基本具備了穩定宏觀經濟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必要條件,但無論從我國歷次宏觀經濟運行調控的主要舉措來看,還是以基尼系數衡量的收入差距縮小來看,個人所得稅的作用并不顯著。原因何在?在我看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了“體量”這一充分條件,亦即個人所得稅的收入規模過小。
為了比較得相對充分一些,我用個人所得稅收入占GDP的比率(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比率”)和個人所得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比重”)來度量個人所得稅收入規模。2022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比率為1.18%,38個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為8.3%,其中,27個發達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為9.9%,5個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為2.7%。同年,我國個人所得稅比重為3.9%,38個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為20%,其中,27個發達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為23%,5個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為7.8%。展望未來,我國在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進程中,要加強財政調控能力,個人所得稅的制度建設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