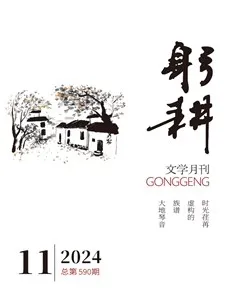鄉間道
再長的鞭子也驅不動一場風,風有風的道。匍匐于鄉間,當風起時,伸手抓一把鄉間的風,用十指一遍又一遍地搓捻,直到搓捻出“鄉間”的詞根,再重新種回到土里,任其野蠻生長。
種下這些詞根時,也種下自己,一并比肩生長。
——題記
且熬一壺時光
冬至,長夜如墨染,更若鐵一樣厚,白晝又蒙了一層幔,眼睛缺了著落。乏了一場雪,大地冰冷如磐。只見淺灰色從眼前一直鋪到天邊,貼著地面的房屋三五座相依,旁側再站立幾棵冷峭的樹木,淺灰色雖有了起伏,但清冷之感愈發強了。日上檐梢,布幔漸漸扯去,以藍為底色的天空像結了一層薄冰。此時,既無紛擾又無風,寒氣薄了些,貼面時,臉頰涼涼的,沒有刺骨的痛。月如薄玉,幾縷灰色輕著其上,猶如隱隱的瑕。難得這樣一個冷冷的清晨,正好打坐高空,冷眼大地、山川、人間。高處不勝寒,于是緘口不言,一份孤傲倒比寒氣還浸人。
行人漸多起來,言語開始是一粒一粒的,后來便有了一起一落的應和,再后來便扎堆了,偶起的開懷大笑向四周蕩開時,清晨有了很深很密的裂紋。
日上三竿時,西邊天際有了一帶淺黃。清泠漸弱,冷峭漸軟,一股溫暖化開了冬至的孤寒。
最有味的還是鄉間熬茶。冬天太過黏稠致密,在這里,似乎只有茶才能化得開。吃罷早飯,爐火通紅透亮,煤塊的骨有潤玉的質地。茶壺用開水醒過后,腆腹坐在茶爐上,嗞嗞的水聲從壺蓋縫隙間鉆出來,蹦到屋頂,又火急火燎地尋著檐下的縫隙鉆出去,散在院子里,早早招徠那些該來的人。壺嘴的水汽游絲樣,有一縷沒一縷地閑散地逛著。時間在水汽里也軟了,輕了,冬的灰白里多了幾縷詩意。沒農活催趕,一個村莊在冬的襁褓中都是軟的,散的。慢下來的時光中,最適合熬茶。爐中,火苗搖曳,正一點一點地從煤塊的縫隙里拔著熱量,也拔著煤塊黑色中潛藏的時間。爐火燃旺時,茶壺被燒得通透,壺底、壺壁把熱量傳遞給水。水沉默夠了,就借著熱量替時間注腳。嗞嗞聲響起來,時間便有了刻度。這是一場抗衡,又是一場互測,既然都是時間的產物,干啥要那么著急呢。煤塊耐得住性子,做茶壺的泥沙本就性子涼,水熬不到火候也不會發聲。莫小瞧了茶葉,纖細的葉片藏了生命的密碼,是最能熬得住、熬得久的。熬茶的人腳板下就是時間,走了半輩子,時間沒老,他們一個個都被時間熬通透了,自然也耐得住時間。這第一水不能熬得太久,火候過了,茶就被熬老了,就像人一樣,年輕時得慢慢磨煉,急不得。急了,好鐵就熬成了廢鋼。第二水他們會把火爐捅旺,茶壺里水添到七八分滿,直至沸騰的茶水頂起壺蓋,才緩緩地從火里拎起茶壺,提得高高的,然后慢慢傾斜,滾燙的茶水就從壺嘴劃著一條弧線落入杯中。茶水滾燙,落入杯中的聲音是滾燙的,時間也是滾燙的。當茶水觸著唇,沾著舌面入到喉,再沿著腸道緩緩進入腹中,時間瞬間有了具象。飲茶不就是飲時間么,茶壺里煮時間,喝到腹中,再把時間熬煮。熬透了,長出一口氣,七竅通豁了,身心也通豁了。身子輕了,時間更輕了,夜再黑再長,也就是熬一壺茶的工夫。
他們最愛熬的是花茶。一打開茶罐,一股香氣迎面撲來,神思頓覺一爽,眼睛里都有了光亮。別覺得花茶淺薄,其實是最經得起熬的。它的香氣是長在骨中的,愈熬愈是醇厚,就如摻雜在一團深褐色中的那一梗兩梗的白徑或一枚兩枚的白瓣,藏得悄無聲息,卻又清晰可揀,經久耐看。白,白得分明;香,也要香得分明。靜待有緣人,茶不馬虎,熬茶的人豈能馬虎?盡管時間洪荒,但也會開花,一瓣兩瓣的,花茶中的一髻兒白怕是時間種在花茶中的骨吧,熬茶的人就是熬這一截小小的骨。
一個冬季,寒氣把時間都回攏壓密了,時間沒了具象。走在田野,抓不到時間,空曠會把人吞噬掉。人回到村莊,回到低矮的瓦舍,時間隨人,就蜷伏在茶壺里。向茶中要時間,熬茶的人諳熟火候,熬得不釅不淡,當茶湯吊在空中,能吊出一根線時最好。喝茶的人啜著茶,一些時間也就順著線爬。爬一個上午,茶淡了,茶中的時光也淡了。一聲“散么”,人散了,時間散了,隱藏在眼底的情仇怨恨也散了,那一髻兒白卻的的確確把心滌蕩輕了。
鄉間,在一冬的熬煮后,輕得像山巔的一抹葦白。
向雨聲的深處走
熬茶的工夫,雪變成了雨。有雨的日子,斜臥炕頭,在一鍋旱煙里萃取雨聲,也是一景。這跌落鄉間的雨,恰如花開。零落時,是一樹桐花;繁密時,是一樹梨花;清晰時,是一叢野菊。
燕雀的叫聲稠密起來時,東風來了。吹一場,田野明亮一成;吹一場,柳條柔軟一度;吹一場,土地清醒一分。當然,天空也被吹高了,云也被吹薄了,說不上哪幾塊云中就藏了幾滴不安分的水珠,不小心一個轱轆就從云縫里掉下來,打在房檐上,向四周散開,似一個喇叭。一聲呼告后,同伴就紛紛從云頭跳下。一時間,啪啪聲四起,一聲比一聲砸得響亮。臥在炕頭的人,心里種著梧桐,一個雨滴炸開,就是一個紫色的喇叭,零零落落地掛在桐樹的枝頭。桐木的質地纖雅輕靈,最適合打制家具,做嫁妝,所以房前屋后總少不了栽植幾棵梧桐。筆直的干,碩大的葉,特別是喇叭形的花零零落落地掛在枝頭,說不上是寂寞還是清傲,但不扎堆生長,不扎堆開花卻是真的。種得梧桐樹,引來金鳳凰,梧桐樹碩大的花朵未引來金鳳凰,卻展示著一場春雨的樣子。大概初來的那幾滴是探路者吧,一旦找到落腳點,便砸出聲響來,砸成桐花的樣子和狀態。寂寞梧桐,但春雨并不寂寞。點點滴滴,把致密的時間疏離,鄉間便生了閑散。臥在炕頭的人抽著煙,也抽著時間,煙敗了,日子就薄了。難得一個“淡”字,才有了鄉間的不急不惱。
夏季的雨,絕對是一樹梨花。紛紛擾擾,洋洋灑灑,恣恣睢睢,不留一點兒罅隙。聲音密集到洪荒,密集到空洞,密集到壓抑。鄉間的一樹梨花開放時,所有的花骨朵肯定簽了契約,都擇了好日子,卯足了勁一齊開放。梨花壓枝低,這梨花的白得有多重,才能壓進春的骨頭,壓出一份孤傲來。夏天的雨有沒有簽訂契約,云是知道的,一旦來了,絕不低調,噼噼啪啪的,不打斷幾根骨頭誓不罷休。又是鋪天蓋地的,給天地洗一次澡,且要洗得酣暢淋漓。這雨一如梨花恣意的白,把鄉間塞得滿滿的。夏雨,又叫白雨,這白是梨花的白嗎?一場雨傾情清洗村莊的骨骼,不加一個“白”字,村莊怎么會有這曠世的輕盈呢?“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東坡的《和孔密州五絕·東欄梨花》中青白不浸,春色離離,自生清明,這不就是倍受排擠,而忍韌豁達的東坡嗎?淋慣了雨的人就如雨,盡管有風牽絆,奔赴大地就是執念,既是“回首蕭瑟處”,也是“也無風雨也無晴”。扛著雨聲細數日子,不就是一份篤定與豁達嗎。所以再急,鄉間的時間都是清明的。
一立秋,雨聲就稀疏了,但雨卻成了腳夫,揚起一聲一聲清脆的鞭響趕著遍野的莊稼找歸宿。趕著趕著,田野便被趕出一坨兒黃,一坨兒灰,一坨兒褐。雨腳不歇息,雨聲就一直淅淅瀝瀝,秋變得拖沓冗長。成熟的路并不好走,得熬,熬住了才能破繭成蝶,秋雨的鞭下雕刻著一句箴言。
野菊開得不擇地。場畔、地埂、路邊、山咀,一長一簇或幾簇,但花開得卻清清俊俊。細數,一定能數得清。秋季,大雨還是少點,離離散散最好,數菊花一樣數著雨聲,愁也是不密不疏。此刻,難得呷一個“清”字。
打撈月色的清涼
養得住雨聲的鄉間,也最能養得住月色。你聽:轆轤一圈一圈地轉著,月也一圈一圈地轉著。
樹影喑啞,柴垛俯臥,月色如紗,輕掩胡同。轆轤聲逶迤而來,如舟行浩渺處,只聞舟楫輕劃水面的聲音,卻不見隱約箬篷,江面如熨。此刻,夜正被月色熨帖。轆轤聲一圈一圈繞過后,更大的寂靜很快就漫漶過來。
浩渺的天空下,一丈高的土崖前,東西兩堵半人高的土墻之間,一個影子下肢站成弓步,上肢有節律地在月色中畫圓,上半身也有節律地或起或伏。井沿邊,一個下蹲的身影正伸出雙手交叉著呈攀爬狀。只見一輪明月從幽深的井底緩緩升起,耳邊偶爾還有滴水碎玉的聲音——一對母子月夜正在井邊打水。他們從亙古的地殼深處打撈清涼,不料,月色卻將他們從寂靜的夜里打撈出來,一幅水墨畫一樣,在夜里輕輕印染。
庸常的日子里,誰不是在打撈清涼?歲月把腳印刻在轆轤上,一圈一圈的勒痕嚙噬骨頭,疼痛化成吱扭聲,把夜撩撥得輕盈柔軟。舉重若輕,不是誰能輕易詮釋的。柔軟的井繩繃直的那一刻,每個毛孔都灌滿了審慎,錚錚骨響里,吊起歲月的重。嘩的一聲,當一輪圓月碎成流銀時,是不是如釋重負的宣泄。庸常即平常,水如月色一樣清涼,正好掬水洗心,舀月清骨。和著月色,吱扭聲合成一股繩索,人間被打撈起來。
一顆流星一閃而過,跌落的地方,一粒狗吠聲彈出來,穿過月色輕撩的巷子,不長的尾音后,夜更加深了。草叢試圖舉起月光,卻被流瀉的晶瑩輕輕著潤,似乎聽到一地的骨骼脆聲輕吟。昆蟲們禁不起這樣的夜的熨燙,都蟄伏在草間熟睡了,即使有偶爾的囈語,很快就被草葉劃撥開,只把月色逗出了一個小小的漣漪。
鄉村的夜太靜了,一棵樹就是一位丹青高手,執筆輕描著夜的靜,白晝離散的樹葉此刻抱成團涂抹著黑色的云。一團一團的云把樹根上沉淀的寂靜拔出來,舉得高高的,更深的寂靜就從黑色里氤氳出來。鳥棲息得早,月色不夠翠,但到夜半時分,偶爾淺睡的幾只一定會被翠到極致的月色驚著,輕啾一聲,翅膀急拍一兩下,卻未撼動黑色,很快就被淹沒了。
站在蒼穹的月亮自始至終都是玉顏含謹,碎步輕移。高處,有了另一層含義。
跟著羊兒去牧云
窄窄的塬上,荒圮的窯垴、孤寂的場畔、人跡罕至的小路都被草占了。雨就像鞭子,一場雨來,草都齊刷刷向高處長,向遠處跑,生怕落后了。一條塬成了草的天堂。
羊來時,風離得很遠,草頂著露珠挑逗陽光。一到塬上,羊鼻翼迅速抽動幾下,敏銳的嗅覺便引了羊向合口味的草探嘴而去。不見雙顎上下明顯開合,只有雙唇微微而急速地翕張,便聽到刀掠過草尖的聲音。若有風起,羊從不顧及,只順著鼻息走。一旦有人來,草再香,羊也會停下來,抬起頭,瞅向人來的方向,同時兩只耳朵聳起,耳廓也向著人來的方向。若人無危險的行為,羊邊嚼食口中的草,邊注目來人,不會跑,也不會有攻擊性的舉動。有的還會抬起頭伸長脖頸長咩一聲,有的上前來還會用頭蹭人的衣襟和腿腳。若是羊羔,定會扭動身軀跳躍幾下,操著奶油腔調咩一聲后,便向遠處奔去。草循著空隙長,草循著水的方向長,草循著向陽的地方長,羊只循著自己的氣息走。氣息彎曲,羊的步履也彎曲;氣息游蕩,羊的身軀也游蕩;氣息筆直,羊的奔跑也筆直。看似牧羊人牧羊,其實是羊放牧著自己。逢到合口味的草,羊吃得認真,但絕不會連根拔起。羊懂得與草為善,懂得與人為善。
吃飽的羊索性會臥到草叢,抬頭看天看地看人看蝴蝶起舞,耳朵時而耷拉時而聳起時而半垂半起,聽風起聽草動聽樹葉的交頭接耳聲,口中不忘認真仔細地反芻。羊羔卻是調皮的風、調皮的云,風逗云也罷,云嬉風也罷,羊羔都是風和云的孩子,頭羊、母羊是一團臥云,一臥,一座塬都輕了。
牧羊人躺在塬的高處,牧著羊,牧著云。其實,牧羊人又何嘗不是被羊牧著、被云牧著?以前,牧羊人身子重,熬不住時間,專揀草肥草厚的地方去。一個夏天,那些地方便露出了白色地皮,斑禿一樣,風見了都會被硌著。蟬聲操鞭驅趕時間,時間驅趕牧羊人,羊不走時,牧羊人就持鞭驅趕羊。起初,羊很順從。后來,羊開始違拗。沒辦法,牧羊人只得妥協。其實,羊自帶鞭子,它更愿意被自己的鼻息放牧。吃,只吃到七分飽,另外的三分得留給草,羊的齒間有一把尺子。羊有羊道,人有時太急了,不愿意琢磨,便以人的道放羊,那怎么行呢?再后來,牧羊人便順其自然,羊和人沒了嫌隙,草再也沒硌過風。躺在崖咀,看云,和云相看兩不厭;聽羊,和羊相聽兩不厭。羊也和山水相看兩不厭。
一場風可以挑逗羊,但絕不會引領羊,更不會引領牧羊人。始于隱秘處的東西,怎么會有定性呢?
風從彎彎曲曲的河道上彎彎曲曲地吹來。風里,流水聲也是彎彎曲曲的。灘頭,一叢燕麥挑著陽光舞蹈。風順著山坡向上爬,到了幾乎垂直的懸崖前,攀著崖縫向山頂的樹上走。樹摁著崖咀,山有了謙卑的樣子。向著溝口的一邊,幾根新的斷枝露出傷口,那些舊枝試探著向溝底眺望。背風的一面,恣睢得多了,正扯長目光向塬心探尋。深邃的歲月在一棵樹上突然就淺了,淺得讓那些大樹一下子就羞澀了。
風來到原野,囚在骨子里的野性才得以釋放,扯開長長的尾巴肆意游走。一路游走一路歌唱,幾句粗獷的調子四下沖撞時,曠野有了模糊的形狀。一個土坷垃伏身黃土,木訥慣了就索性沉默,一蹲身的時間就是一個村莊的時間,但讓風改道,或使風打個趔趄,或把風絆倒,一個土坷垃一分鐘的調皮就能做到。風只知道是土絆倒了它,其實是時間絆倒了它。
走在人世中,眼光都是從心上長出來的。一顆心里裝滿了稗子,聞風而動成為秉性時,歲月不抵一場風的淺薄。
羊肯定比風活得簡單。
白雪養大了炊煙
一臥,風都不忍喘息。羊反芻著,鼻翼一動,一朵云就在身邊暈染開來,一坨一坨的。飛到天上,再落下來,就是一朵一朵雪花。雪中,熟睡的村莊便被炊煙輕輕釣起來。
一朵雪花不知啃食了多少時間,下落時,不焦不躁、慢條斯理。把吃進去的時間再吐出來,那就一定要吐出時間的骨。時間的骨是柔的,雪花怎么不知道呢,所以輕滑著,舞蹈著,又不經意地繞一下,翩翩若蝶。眾多的雪花從天幕滑下來,盛若仙子的水袖長舞。對于天地的蒼黃和灰枯的點染,雪最能耐得住性子。
出了城,田野被雪熨著,少了褶皺,多了圓潤的起伏,被陽光一舔,水津津的,若一塊璞玉。屋子或零散或簇堆,往日勾勒出的生硬曲線,此刻被雪柔軟了。躺、臥、爬、伏,雪里都是百依百順。樹卻是另外一副樣子,杵起僵硬的身子,伸開嶙峋的指爪,硬是要撐起一股子堅強來,有幾棵更是不惜把斷裂的骨茬也裸露出來,以強硬的姿態作出一種強硬的提醒。
進了村子,雪落得更加慢條斯理,悠游自在。雖從高空下來,卻并不擔心去處。落在哪一處不是故鄉呢,歸來的雪似乎愈加的坦然了。
一朵一朵地落,落在瓦舍,落在坡頭,落在峁咀,落在一壺嗞嗞的茶聲里。一寸一寸的白向村子的胸膛熨去,向村子的四肢熨去,熨進村子的內里,熨進村子的血脈,聒噪與著急、惶惶與戚戚、繁雜與紛爭都被熨出去,讓白色骨子里斂著的平和溢出來,溢成晉宋丹青筆下的一幅小寫意。鳥兒掠過天空,鳴聲是一粒一粒的;狗臥在深巷,吠聲是一坨一坨的;貓伏在炕頭,叫聲是一痕一痕的。雞漫步庭院,趾形是一朵一朵的;麻雀落在場畔,爪影是一簇一簇的;豬逃出圈,蹄痕是一綹一綹的,若是喂崽的,觸地的乳頭定會劃出一道灰色的渠來。
雪摁住了焦躁,煙縷便耐住了性子,從檐下悠悠而出,裊裊上屋頂,散逸開來,給摁著屋頂的雪撩上了一層青紗。屋內,爐火輕燃,雪的白撞進來,漂著墻上的煙漬,漂著煙漬里的記憶,漂著陷在記憶深處的父親,一點一點地變白,一點一點地變得空洞。只見,父親的身軀一寸一寸地回縮,他的骨骼正被時間一節一節地嚙食。人把時間吃進去,也要吐出來。村莊里,像父親這樣的老人很多,他們都在吐時間。終有一天吐完時,他們就成了一抔黃土,而另一撥人卻在吃他們吐出的時間壯骨。村莊的時間沒老過,就在一茬一茬人的五臟六腑中轉圜著。
草木和村莊是鄰居
人長腳,草木、莊稼也長腳,向著水扎堆的灘上跑,向著地力肥沃的園子跑,向著陽光密集的地方跑,向著通風透氣的開闊處跑,在這點上,人被取舍羈絆,莊稼被人羈絆,唯有草木率性,即便被風隨意卷起又遺落,但根和梢都長著眼,靈醒得很。
一棵樹看似一年、十年、百年,甚至千年都守著一個地兒,守得天荒地老,樹梢舉著一片固定的天空,舉得篤定執著,舉著一窠鳥巢,舉得經年不累。一棵樹一站就站成了地標,樹梢上養著的家年年都會飛回一對舊燕,生出一窩新燕。但它埋在地下的腳絕不會沉默,那些生在腳趾上的末梢神經機敏著呢。只要土地的縫隙里有水滲進來,有風鉆進來,有漚熟的糞味飄進來,腳趾第一時間就會知道。于是,像聽到號令一般,都摳著土卯足了勁向一個方向攀爬。土地沒有哄騙樹,樹沒有哄騙天空,向水、向風、向糞的那面枝長、葉密、色翠。特別是栽在地畔的那些樹,地下的腳一定長了眼,向路的這一邊只顧著向深處扎進,偶有那幾行腳印嘗試著向地表爬,爬不到幾步便生生折了回來,而靠近地的這邊,除了向深處扎外,絕大多數都在地表匍匐蔓延,網一樣,把一塊地籠在了腳趾下。有一年,我蹲在地頭看四叔挖地,幾?頭下去,就挖出了一張埋在地下的漁網。和這些樹的腳斗了一輩子,四叔終是沒斗過,臨了只說了一句:樹和人一樣,都得活呀,沒樹,人心慌,村莊心慌,天空更心慌。于是,在鄉間,有些樹木比人活得還恣意。
身為大樹,從不和草爭。這律法不知誰定的,樹一直恪守著這個律令,和草百年、千年為鄰,即使被草的莖蔓捆綁得緊緊的,樹也不甩臉子,還會把肩頸遞過去、臂膊伸過去,供草登踩攀爬。特別是腳踝四圍,一任草蓬蓬勃勃,盡管有些小花開得零落,倒也安然,畢竟有大樹罩著,便從不擔心天會塌下來。當然,草也從沒想過長得超過大樹。人唇齒偶有不和,但草木更愿千年為鄰。有一年,天降暴雨,村莊一棵百年老樹被雷霆擊裂,露出了森森白骨,樹就是未倒。第二年,舉著的那窠舊巢里依然結出了繁碩的鳥鳴,裂縫中還長出了一蔓牽牛花。于是,黃蜂來了,螻蟻來了,鼠類也來了,紛紛都在裂縫中筑巢安家了。
草不會與大樹爭,但會與莊稼爭,草即便死在四叔的鐮下、鋤下,依然在爭。
一打春,最先醒來的是藏在土地褶皺與紋理中的水汽,春天它們舒活筋骨,它們給土地解鎖松綁。一旦醒來,它們就揀著縫兒向外鉆,向上拱,向地表浸,土地的身子便柔軟了。這柔軟一壟一壟的麥子感覺到了,吸著水汽,不幾天就由灰頭土臉變得鮮活青翠了。這柔軟一坨一坨的草也感覺到了,特別是在眾多草中較敏感的薺菜一觸到醒來的地氣便像打了雞血,迅速向四圍鋪展開身子,急欲占一席春光。幾天工夫,麥壟間就散布著它們蓬蓬勃勃的身姿。與其說蜷縮了一冬的村莊是東風舒活的,不如說是被薺菜的香撓醒的。一個漫長的冬天,鍋里沒了星點兒的綠,炊煙都是慵懶的,好不容易逮到春陽朗照的日子,媳婦、姑娘、孩子挎著籃子來到田野拾薺菜。一大片綠上,各色身影嵌上去,一粒粒的言語蹦出來,偶起的脆笑拖長尾巴,面前身后一縷縷炊煙就活色生香了。
草與莊稼爭,不是草與莊稼不睦,這是人取舍的結果。比鄰而生,各為所用,莊稼不會嫌棄一棵草的。莊稼長在草中,怎能不就是一棵草呢,草長在莊稼中,或許就會變成一棵莊稼。秋天,成片成片的玉米嘎嘣嘎嘣地把綠色往天上拱,嘩啦嘩啦地把綠色往天邊攆,一蔓牽牛花卻兀自繞著玉米小腿攀爬,幾個紫白相間的喇叭隱在黏稠的綠中不聲不響。不爭即是爭,獨處一隅,守著自己的寧靜。這不是難得的一景一境嗎?
人把地撂荒,草急忙趕過來填補。一垛草容得下螻蟻蟲鳴,引得來微風蝴蝶,舉得起雷鳴閃電。這些活在低處的東西更懂得與鄰為善。
其實,先于人而生的草木,又何嘗不是人之師呢?
貓狗在,星星不寂寞
牛太有定性了。一旦拴在樁上,臥在向陽的晾場,一臥就是一整天,甚至到月明星稀時,依然淡定。反芻不緊不慢,穩而有節奏,雙目看天看地看人,不喜不悲。
它只要臥在村莊的中心,風都吹不進來,村莊就平展展地、踏實實地臥在大塬的懷里。
貓、狗卻不一樣,只要有風撩撥,便活泛任性得很。
貓、狗該屬陰性吧,要不怎么白天都是慵懶狀,慵懶的眼睛瞇成一條縫,好幾個鐘頭都不睜一下?特別是冬來時,一個白天,都挑著向陽的地方,一直會曬到陽光隱去。
狗鼻子尖,貓耳朵靈,你千萬別自以為是地認為貓狗只屬于夜晚,它們機靈著吶。白天一定是半睡半醒,某幾條神經線是時刻處于戰備狀態的。它們的警惕性早已植到骨子里。
風最善挑逗。這不,一絲輕風來,卷起一片葉,擦出“嗞嗞”聲,貓狗雖閉著眼,耳朵卻早已支棱起來,鼻孔輕微地抽搐著。感性的辨識促著身體的變化,力量已迅速地集到腿上、腰上。它們伺著機會呢。
村莊里,貓輕易不戴繩索。糧食金貴的年代,鼠最遭人嫉恨。對于鼠的天敵——貓,人們便網開一面,任其率性出入廳堂。或臥懷上身,貼腹蹭臉;或爬樹上墻,攀花折枝,主人從不呵斥,反倒歡喜有加。累了半晌的人們靠窯腳一蹲,歇息的當兒,貓和風里的樹葉嬉戲,或逡巡于光里一片樹葉的影子,伺機用爪子謹慎地探探這是何方神圣。有趣的表演把心熨得平平展展、舒舒服服。這靈物知人垂憐,卻從不任性,亦不黏人。對于這位家里的小主人,家家戶戶都會在屋舍或窯洞的門檻下專門給它留一洞出入自由的門。貓永遠與主人同室而住,這是狗沒有的待遇。
有了貓,屋內屋外有了清趣,鼾聲有了味。
當然,金貴的貓也走失過。
一旦一大清早走出去,掌燈時分還不見回來,主人便會著急。剛端起的晚飯都顧不得吃,主人便東家串進,西家串出,挨門問個遍。再找不到,就去莊前屋戶、崖畔峁咀、胡同廢墟,學著貓叫,喚貓回家。此時,月清風輕,玉米葉子知趣地靜默著,一村都是“喵嗚——喵嗚——”的貓叫聲。
養貓不易,養只會抓鼠能認路不忘家的貓更不易。被貓丟怕了的人家便想出法兒,給貓用柔軟的布包裏起新棉花縫個精致的項圈,再系個精致的鈴鐺。貓一旦跑遠,風不欺騙人,會把鈴鐺聲傳回來。你愛的東西,他人更愛,貓還是在丟。于是,便給貓置辦了精致的繩索,這一拴,貓便被真真切切地豢養了。
繩索囚住了腳步,貓的眼神黯淡了,腰身也胖了,漂亮的貓步不見了,老鼠便肆虐了。
村莊沒有了自由的貓,風慵懶了,黑夜里,更缺了一雙锃亮的眼。
缺了貓出沒的村莊生出了一個空洞。
兔死狐悲嗎?狗的命運也沒好到哪里去。
和貓一樣,屬于夜晚的精靈——狗也曾被主人寵愛著。
風寂燈黑的夜晚,主人沒回時,大門開著,不能睡,狗明白這一點。此時,狗前肢直撐,后肢彎曲,臀部蹲地,腰身豎立,兩耳支棱,雙目凝視,門口一絲一毫的訊息都不容放過。
氣息不對!
步履不對!
缺了熟悉的味兒!
“汪汪”聲大作,身體直向路邊沖,繩索被拽得“錚錚”響。
濺香的旱煙味繞來,狗扭頭探身,尾巴撫地,發出半聲哼嚀。
嗵噗——嗵噗——一深一淺的腳步聲傳來,狗的哼嚀聲更加親昵,尾巴晃得更起,索性在原地打起轉來。
自持敏準的嗅覺贏得主人喜憐,靈性的狗活出了人氣,平素吃的食也和主人食得一樣了。
夜晚太過空曠,人心會慌,夢都太淺,所以一到夜晚,村莊把靈敏的嗅覺借給了狗。一旦村莊有了異味、異響,一狗叫,全村的狗都跟著叫。聲音此起彼伏,此消彼長,此急彼緩,此長彼短。一時間,一聲狗叫,全村狗醒,一盞燈亮,全村燈醒。狗喚醒了狗,喚醒了燈,喚醒了村莊。
其實,多數情況下都是虛驚一場,狗的敏感看似給村莊添了不和諧的音符,但主人除了嗔怪外,絕不會懊惱生氣。一個轉身后,主人的鼾聲更實,村莊的夢更深了。
有了狗,村莊的曲子有了起伏,夜愈加深邃了。
狗和貓一樣,成了村莊不可或缺的風景,但狗和貓是不知道的。
狗也想過和貓一樣被放養,但它害怕自己沒定力,會食了太多的氣味,所以寧肯只守一道門,只記一種味,只認一個人。
村莊里沒牛了。
村莊里貓少了,十家八家只見到一只,一逢人便跑。腰身粗得像水桶。
狗進城了。除了做寵物的外,多數是流浪狗。常三五一堆,或八九成群,追著叫花子瘋跑瘋叫一陣,又去追風,追風里的紙片,無端地朝天狂吠幾聲,便低頭循著氣味向下一個感興趣的目標跑去。
如今,還常回村莊。
走在村莊的小路上,走著走著,心就空了。
村莊大約確是離心越來越遠了。
道可道
土地上生草木,長莊稼,也養育六畜和人。除了具象的,水流、云霓也是土地生的,所有的蟲鳴、獸語、人言都是土地教給的。
站著、坐著、躺著,本就是一個文字,若連續起來流動或簇擁,就成了一句話。站得久了、坐得穩了、躺得平了,就成了一篇錦繡文章。這篇文章沒有結尾,土地引著一直向深處挺進扎根。地表上的枝繁葉茂、轉圜變化都是一種象,人的語言是這種象的派生。窮極一生,窮極一生累積的語言,人都難盡其詳。
時間熬人,人把時間嚼碎了,也未必能把時間嚼透,但時間確確切切把它的影子雕刻在了一些事物上。時間是個量詞,又是一個動詞,既是一種微距,又是一種洪荒,萬物都逃不出時間的丈量。空間是位置的哲學,一物一位,定位就是秩序,僭越只是暫時的恣睢。歸位是空間的道,時間是這種道的詮釋。在時間的鞭子下,人太急了,只專注于向遠處走、向高處走,卻忘了時間的道。人荒時間一時,時間荒人卻是一生,違拗的事情,草木不做。
把時間熬在茶爐上煮煮,酸甜苦辣觸著舌尖,流到嘴里,潤著腸道,五臟六腑回歸到自己身里,才知道站在合適的位置多重要。
走向大地,走進叢林,特別是走進被秋風疏離的山間,就會覺得“站位”從來都不是一個虛詞。叢林生態就是時間留給人間的箴言。一株素菊以蕊舉起一隅的寧靜,這就是菊的使命。一枚松針安臥于塵上,一個“斂”字輕輕舉起來。爭與不爭都是一個“位”字,守位而不逾矩。
綠色托起鳥鳴,鳥鳴高舉天空,天空上演大象,我把自己種在土里,傾聽草叢間纏繞的蟲吟,摩挲地底下纏繞的根系。風起時,借一抹綠色捎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