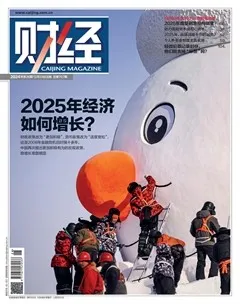深入日常生活的中東之旅

《看不見的中東》
姚璐 著
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2024年11月
一
在納西里耶的一天傍晚,伊拉克朋友穆罕默德邀請我去家里做客。
穆罕默德的家是一套平房,進門就是客廳,地上鋪了褐色的地毯,四周擺了一圈米色的沙發。我剛進門,穆罕默德的父親和弟弟就迎了上來,與我握手問好。一位姑娘端著茶水從里屋走出來,她的一頭黑色卷發束在腦后,眼睛像兩顆水晶葡萄,又大又圓。穆罕默德介紹說,這是他的妹妹朵阿,她大學學的是英國文學,畢業后,她找不到對口的工作,只能賦閑在家。朵阿低著頭,靦腆地笑笑,圓圓的臉上泛起了紅暈。
我與穆罕默德的父親和弟弟寒暄時,朵阿已經在地毯上鋪好了餐墊,端來了剛剛出鍋的春卷、餡餅和沙拉。把餐食安置妥當后,她坐到餐墊的角落位置,拿起一塊餡餅慢慢咀嚼。
穆罕默德正聊得興起,但他的英語詞匯量跟不上他的思維,每當卡殼,他就轉頭詢問朵阿,朵阿用左手遮住嘴唇,在哥哥耳邊輕聲低語,告訴他應該用哪個詞。當哥哥自信地說出朵阿傳授的詞匯時,朵阿總是睜大眼睛,嘴角上揚,一臉期待地看著我,像是等待被肯定和表揚的孩子。
“你是學英語的嗎?那我們應該可以聊天吧?”我看著朵阿的眼睛問道。她輕輕點頭,臉已經漲得通紅。她用哀求的眼神看著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領會了妹妹的意思,轉頭告訴我,朵阿從沒見過家人、朋友之外的陌生人,不善言辭,但她聽得懂我們的談話。朵阿用力地點點頭,給我加了點茶水。
吃飽喝足后,一家人把我送到門口。我穿完鞋正準備出門,朵阿突然踮起腳,湊到穆罕默德身邊,與哥哥耳語了幾句。穆罕默德告訴我,妹妹覺得我的談吐特別自信、自如,她很羨慕我。哥哥說完,朵阿吐了吐舌頭,像是在為自己的靦腆道歉。
我尷尬地擠出一個笑容,心里卻很難受。要知道,自信、自如這些品質并非與生俱來,而是在與陌生人的交往中、在獨當一面的旅行和生活中慢慢學會的。但有些女孩生而缺失這樣的權利,她們不被允許獨自面對世界,沒有機會接受挑戰、鍛煉自己。她們缺乏的不是能力,而是一雙把她們推向更大世界的手,和背后無條件的愛、認可、鼓勵和支持。
想到這里,我覺得無論如何都應該說點什么。我轉過頭,鄭重地對朵阿說:“我不是生來就自信的,你也不是生來就膽怯的。作為女人,我們完全可以獨自旅行和工作,也完全可以和陌生人談笑風生,獨立應對各種問題。你要相信你自己。”
朵阿的眼眶一下子濕了,淚水把她的大眼睛襯托得更加水靈。直到告別,朵阿也沒有對我說出一句英語。
每當聊起中東女性的生存現狀,我總是會想起穆罕默德破碎的英語和自信的表達,以及朵阿那雙膽怯的眼睛和牢不可破的沉默。倘若朵阿這樣的女性在成長過程中能夠不被性別偏見所限制,獲得公平的機會和同等的鼓勵,而非剝奪和打壓,她們的人生一定會很不一樣。
二
近代中東是一面放大鏡,在這里,沖突、戰爭、苦難頻頻上演。保守勢力和世俗勢力不斷交鋒,歷史、傳說、考古都成了斗爭工具,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某種敘事時,它便成了唯一的故事。在數不盡的真相與謊言中,人們彼此誤會、彼此仇恨、自相殘殺。
然而,這并不只是發生在中東的故事。縱觀人類歷史,矛盾、沖突、戰爭比比皆是,人們永遠都在分化為不同的團體,用各種借口爭奪資源、財富和權力。有的人因明面的沖突和炮火流離失所,有的人被暗處的歧視和偏見折磨一生。分歧之內還有分歧,仇恨之外還有仇恨。
打敗幾個敵人、贏得幾場戰爭,似乎無濟于事,因為造成這些悲劇的,是人性中深不見底的幽暗。
如小說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所說,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是驚人的相似。只要資源有限,只要人性中的邪惡、自私、貪婪尚存,悲劇就有可能在任何時代、任何土地重演。
每當想起戰爭中的個體,我的腦中總會浮現《南瓜花》書中士兵的故事。對于掌權者來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爭奪資源和利益的手段。對于普通士兵來說,那或許只是生命中一段莫名其妙的插曲。你不知緣起,身不由己就到了某個地方,進入某種境遇。你不得不扛起槍,為不知道什么而戰。戰爭結束時,你發現什么都沒有改變,你也并不憎恨敵人。一切匆匆收場,唯一的區別是,你老了。命運把你推入一個不可控的劇場,直到曲終人散,你都沒有真正明白到底發生了什么。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或全人類來說,十幾年、幾十年的動蕩不過是歷史長河中的短短一瞬,但對于個體來說,疾風驟雨中白白溜走的日子永遠都無法彌補。這就是我在中東與人們聊起戰爭時的感受。
在抽象的宏大敘事背后,一個個具體的人被犧牲、被拋棄。渺小的個體左右不了時代的方向,也逃不出時代的洪流。他們自身未必會走上戰場,卻親歷著真實的死亡。他們順從著,也孱弱地抗爭著,他們壓抑著,也零星地吶喊著。他們共同構筑起新聞之外一個有血有肉的中東。
三
在令人倍感無力的歷史洪流中,藝術或許是最大的慰藉。中東旅行的間隙,我抽空去了盧浮宮和大英博物館,觀賞來自中東的珍寶。
雖然人類時常互相憎惡、自相殘殺,但在藝術之下,人類有機會超越語言、民族、人種,作為一個共同體去理解彼此。在博物館里對著同一件展品嘖嘖稱奇的人,在同一個遺跡前贊嘆不已的人,常常是背景全然不同的陌生人。透過藝術作品,我們與相隔千年的時代、相隔萬里的人類發生對話,感知到在某些事情上,我們依然有驚人的共情。通過這彼此相通的共情能力,人類創造出了全然不同卻異曲同工的偉大作品。
為了表現超越此世、超越人類的力量,古埃及神廟用遮擋視線的巨大圓柱營造壓迫感,拜占庭建筑用開闊無遮擋的大穹頂塑造崇高感,波斯人用復雜精美的穹頂完成對天國的想象,巴比倫人用通天塔連接人類與神靈。
在權力更迭的輪回之中,藝術開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在那里,我們關注歷史洪流中個體的悲喜,關注人類共同的命運,感受愛,感受崇高,汲取源源不斷的生命力量。這股力量,可以幫助我們存下“善”的火種,抵抗“惡”的侵蝕。
四
走馬觀花的旅行容易讓人陷入獵奇和傲慢。看到迥異的食物、文化和信仰,人們時常傾向于驚嘆或排斥,而非嘗試理解背后的成因;遇到觀點迥異的陌生人,人們時常傾向于用刻板印象定義他人,而非理性、平等地交流。世界是復雜的,人是有限的。當人們自覺無力理解復雜的世界時,便容易轉向簡單的標語和口號,轉向簡化的思維方式。然而,簡單的愛與恨、簡單的群體認同,很可能導向群體的非理性,釀成大禍。
旅行提供了一個認識復雜世界的窗口。在旅途中,我重新審視以色列的建國,也親眼目睹了巴勒斯坦的苦難,我嘗試理解穆斯林,也試圖向他們解釋我們的價值觀,我看到了世俗改革的成果,也見證了弱勢群體付出的代價。我相信,每多敲開一塊歷史的墻磚,多聆聽一點不同的聲音,就會離真相更近一點。
千里之外的故事并非與我們毫不相干。在全球化時代,能源價格牽一發而動全身,地區矛盾也容易被放大,成為殃及全球的人道主義災難。沒有人可以真正置身事外。
關注他人,即是關注自己,認識世界,也是認識自己。
五
飛往德黑蘭時,我并不知道中東之旅可以完成到什么程度。四年間,我因頻繁的海關盤問、檢查站核查而焦躁不安,也因伊拉克、敘利亞的難以抵達而憂心忡忡。
歷經百轉千回,我終于有驚無險地完成了這場旅行。
遺憾的是,再深度的旅行和寫作都不過是驚鴻一瞥。中東的建筑、古跡、藝術、人文令人眼花繚亂,絕非一本書所能囊括。
為了聚焦于新聞之外的日常生活,本書中,我略去了伊朗中部老城、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地區、約旦佩特拉、以色列北部城市、敘利亞薩拉丁城堡、死海等精彩旅程。我喜歡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盡可能把自己交給不確定性,因為大部分難忘的回憶都發生在計劃之外。
旅途中要兼顧攝影、采訪、寫作,著實不易,迎合沙發主們的生活作息尤其令我疲憊。與晝伏夜出的阿拉伯人同住時,白天,我必須冒著酷暑外出拍照、游覽景點,深夜,我還得與他們一起暴飲暴食、談天說地。不過,超高的旅行強度放大了我對時間的感知,一個月的旅行,總是漫長如同一年。
國境線、語言、傳統、文化、信仰樹立起一道天然的屏障,把天南海北的人們隔絕在兩端,只言片語的信息又加深了彼此的誤會和隔閡。不過,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有機會打破人為劃定的界限,互相交流,修正偏見,獲得看問題的新視角。這是我在中東所經歷的最美妙的事。
(本文節選自《看不見的中東》;編輯:許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