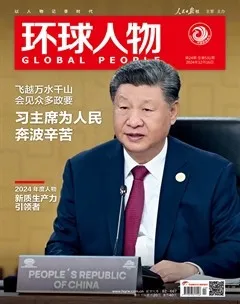沒“爹味”的是枝裕和


12月初的北京寒風料峭,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座無虛席,在場師生的熱情可抵寒風,他們剛剛看完電影《如父如子》的中國首映。不多時,現場一陣騷動后,掌聲響了起來,導演是枝裕和從幕布后現身,緩緩走向舞臺中央。
這位日本導演曾多次來到中國。7年前,他曾受北京國際電影節的邀請,和影迷進行交流,當時,北影節開設了是枝裕和8部電影作品的展映,套票上線46秒后被一搶而空。2018年,是枝裕和第一部在中國內地上映的作品《小偷家族》大賣,創下日本真人電影內地票房紀錄,至今未被打破。
“不管是《如父如子》還是《小偷家族》,都是這位導演最擅長的家庭劇情片,也是影迷們熟悉的是枝裕和風格。”北京電影學院電影文學系副教授、影評人杜慶春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在淡淡的哀傷中訴說親情,是日本各類文藝作品的一大傳統,所以是枝裕和也素有小津安二郎接班人之稱。”從電影處女作《幻之光》到去年的新作《怪物》,含蓄、柔軟、點到即止,是枝裕和的家庭片像一泓清泉,那些關于血緣、親情、人生的真諦在影片中汩汩流淌,欲說還休。就連導演本人也像其作品一樣溫吞慢熱,每當影迷就某個問題向他刨根問底時,他總是緩緩撓著頭,一臉敦厚地笑答:“請在影片里尋找答案吧。”
選擇血緣還是陪伴
2013年,日本新生兒數量創下歷年新低,《如父如子》就在此時上映。這部11年前的作品,是是枝裕和第一部在日本國內稱得上大熱的影片,如今再看,依然意韻悠長。
福山雅治飾演的白領精英野野宮良多家庭美滿,兒子慶多聰明乖巧。然而,一通來自慶多出生醫院的電話打亂了一切。原來,慶多并非良多親生,而是和另一個男孩兒琉晴錯抱了,一時間兩個家庭陷入窘境——是6年朝夕相處的陪伴珍貴,還是血緣重要?要不要換回孩子?父親母親們一時難以抉擇。
談及這部電影的創作動機,是枝裕和講了自己的故事。當年,他初為人父,卻一心撲在工作上,晚上回家時,看到自己的小女兒忽然感到陌生。第二天一早離家時,女兒隨口一句“你再來呀”,讓他心里一驚:“她不會認為我是一個常來做客的大叔吧?”這個瞬間擊中了是枝裕和,于是有了《如父如子》。
片中有兩個父親形象,一個奉行優績主義,認為給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資源、生活條件便是養育;一個實踐快樂教育,拒絕內卷,從不雞娃。“這樣的設定無疑戳中了在典型東亞家庭成長起來的觀眾的痛點。對現實的映射令這部作品常看常新。”杜慶春解釋道。
在《如父如子》的片場,是枝裕和更像后一種家長。演員福山雅治談道,是枝導演的片場非常自由,劇本里的情節幾乎每天都有新變化,這對他來說是一件特別有趣的事情。扮演小演員的兩個孩子更是沒有劇本,只是在每天開拍前,是枝裕和會告訴他們:“今天我們要拍攝去別人家里做客的戲哦!”僅此而已。“所以孩子們還沒搞懂故事情節,片子就殺青了。”是枝裕和笑著說。
至于兩個孩子最終是否交換回來了,影片沒有明確回答。首映當天,主持人做了個現場調查,偌大的禮堂里,認為應該選擇血緣、交換回孩子的,只有一名觀眾,余下的人都選擇保持原狀。對此,是枝裕和說:“整個電影創作過程中,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有意把良多放在一個困境里,讓a0tAysbf37lXZMe/zka39g==他在陪伴和血緣之間做出選擇,但我并不想設定一個答案。我想通過這部電影讓大家思考的問題是——怎樣成為一名稱職的父親?真的只要有血緣關系就能成為一個很有羈絆的家庭嗎?”一番話說完,臺下陷入沉默。
這就是是枝裕和,提出問題,引發思考,卻從不預設答案。
一個唱反調的人
是枝裕和并非科班導演出身。1962年,他出生在東京練馬區,小時候家里附近都是工廠和農田,一家人住在一棟有點傾斜的兩層木結構老屋里。爺爺患有老年癡呆,父親整日沉迷賭博,母親則要打工維持一家的生計,養活是枝和哥哥、姐姐3個孩子。長大后,抱著成為作家的理想,是枝裕和考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一度癡迷于劇作家向田邦子的作品。這位日本女作家用細膩的筆觸,寫出了日本昭和時期的家庭形態及生活畫卷。
1987年畢業后,是枝加入日本首家獨立電視制作公司“電視人聯合會”,以制作紀錄片開啟了職業生涯。教育自那時起就是他關心的話題。1988年,是枝裕和來到長野縣伊那小學。“有各種各樣的人到我們班來采訪,唯獨是枝先生好像不是來工作的。”一個孩子說。是枝花了3年與孩子們朝夕相處,用鏡頭記錄了他們飼養一頭小牛的點滴日常,該片取名《另一種教育》。他還把鏡頭對準自殺的官員、艾滋病患者生命最后的時光、失憶患者在生活中遭遇的困頓……

1995年,他轉換賽道,創作了劇情電影《幻之光》,講述一個女人調查丈夫自殺之謎的故事。該片一舉奪得威尼斯電影節最佳攝影、最佳新人獎,33歲的他自此成為國際影壇最受關注的日本青年導演之一。2004年,根據東京棄嬰事件改編的電影《無人知曉》獲得金棕櫚提名,時年14歲的男主角柳樂優彌成為最年輕的戛納影帝。母親去世后,是枝抱著“沒能為她做點什么”的悔意,創作了《步履不停》《比海更深》,一句“人生路上步履不停,為何總是慢一拍”成為經典臺詞。此后,他佳作不斷:《奇跡》歡樂輕快,《海街日記》清新治愈,《第三度嫌疑人》充滿思辨……直到《小偷家族》,令他最終邁進電影大師行列。
柴田一家6口靠奶奶的養老金和去超市偷竊過活,他們之間沒有直接的血緣關系,卻勝似親人,直到被警察發現。《小偷家族》改編自日本一樁犯罪案件。2018年,是枝憑借該片獲得第七十一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獎,成為繼黑澤明、衣笠貞之助、今村昌平之后,第四位獲此榮譽的日本導演。
“早期的紀錄片拍攝對是枝裕和的電影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首先,紀錄片關注人,這成為其電影作品很大的一個特點,他的電影故事總是緊緊圍繞孩子、中年人、老年人,父親、母親、兒子等不同身份的人展開。其次,紀錄片關注現實,所以我們發現,他的作品不少源自社會事件或個人真實感悟,但事件情節并不重要——人在一個倫理困境中的狀況、在家庭結構之外的社會結構中的狀況,才是他反反復復、樂此不疲討論的母題。”在杜慶春看來,是枝裕和與同時期日本導演濱口龍介、韓國導演奉俊昊以及泰國導演阿彼察邦等人,對于世界電影的一大貢獻在于,他們提供了非西方的對于現代性困境討論的切口,“雖然幾位導演的電影美學各有范式,但都面對全球問題提供了東方導演的獨特觀察”。
2017年,中國作家止庵曾與是枝裕和有過一場對談,止庵評價這位導演——他擁有作家的才華,他的電影講的都是普通人不完美的一生,揭露日本社會存在的問題。是枝裕和自己也說:導演,就是一個唱反調的人。

玉米天婦羅
如今,年過花甲的是枝仍然保持著高昂的創作熱情,他和法國團隊合作了電影《真相》,和韓國演員合作了《掮客》。去年,他又與坂元裕二合作電影《怪物》,坂本龍一在病中為本片配樂;2025年,由他改編并導演的電視劇《宛如阿修羅》也將上線。
作為中國觀眾最喜愛的日本導演之一,是枝裕和曾多次主動談到和中國的淵源,他說自己的拍攝風格深受中國臺灣導演侯孝賢的影響。他與中國第六代導演賈樟柯保持著親密的友誼,并時刻關注著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2024年中秋節,他冒著臺風搭乘航班到上海和中國青年導演、影迷交流。其間,他專門請裁縫量身定做了一套對襟盤扣的中式服裝,這次《如父如子》宣發時,他已經穿在了身上。是枝裕和還在B站開了賬號,他的新劇《舞伎家的料理人》是B站網友的新晉下飯劇……“他拍了那么多父親角色,卻一點也不‘爹味’。”“看是枝裕和總能讓人安靜下來。”“幾乎所有導演在拍攝底層家庭時都會有意無意地使用自上而下的鏡頭,只有是枝裕和永遠能夠保持溫暖的平視。”在豆瓣,觀眾對他不吝贊美。
“我了解到自己在中國很受關注,我很開心。要說原因,我想可能是因為家的故事。不論在哪兒都有相似之處吧。越小的細節越有普遍性,越能引起共鳴。”是枝裕和曾如此說道。《無人知曉》里褪色的指甲油,《比海更深》中的美津濃球鞋,《小偷家族》中放在泡面蓋上的可樂餅……電影里的細節之所以引發共鳴,是因為它們都無比真實。《步履不停》里,是枝花了不少篇幅不疾不徐地展現樹木希林飾演的母親炸玉米天婦羅的場景,這個細節是導演本人的童年經歷。“我喜歡媽媽做的玉米天婦羅。小時候家旁邊就是玉米地,不過是鄰居家的,所以玉米其實是偷來的,誰又能發現呢?偷偷掰回來玉米,偷偷把玉米粒剝下來,請媽媽幫忙炸得脆脆的,特別好吃。誰知晚上,鄰居又送來很多玉米給我們。”這個故事在電影中借演員之口被講出來,圍坐在餐桌前的一家人頓時笑作一團。窗外蟬鳴不止,院子里父親新種的樹,葉子青翠欲滴。
日子細水長流,似乎永遠不會有盡頭。
編輯 余馳疆 / 美編 徐雪梅 / 編審 張勉
是枝裕和
導演,編劇。1962年出生于日本東京,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早年因電影處女作《幻之光》受到國際影壇關注,2018年,憑借《小偷家族》奪得戛納金棕櫚大獎。近日,攜作品《如父如子》來到中國,引發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