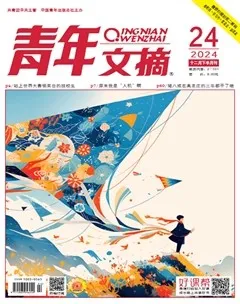瓦爾登湖邊,被投喂的梭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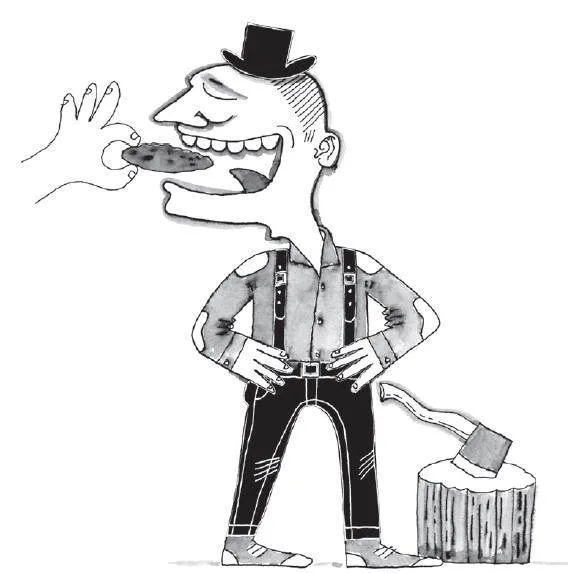
1845 年,亨利·戴維·梭羅踏上了著名的朝圣之旅:前往馬薩諸塞州的瓦爾登湖,住進森林中親手搭建的小木屋。此去林中,是“只面對生活中最基本的事實,看我能否學到生活要教給我的事,免得到了彌留之際,才發現我從未真正活過”。
自從讀過梭羅的森林朝圣之旅,我就十分艷羨,他的故事令我想起自身經歷的匱乏。我是一個城里長大的孩子;我有一雙柔軟的、沒有繭子的、作家的手;我的工傷就是被紙張割破手。如果把我放在瓦爾登湖畔的一個小木屋里,切斷電源、自來水和無線網絡,我根本就活不下去。
但是,讀到阿曼達·帕爾默的《請求的藝術》之后,我的態度開始改變。在這本書中,帕爾默披露了梭羅“自力更生”實驗背后的一些細節。原來,梭羅修建的那個小木屋距離他自己家不到2 英里(約3.2 千米)——并不像書中暗示的那樣,處于偏遠的森林之中。他幾乎每天都回到文明社會,因為康科德城就在附近,走路便可以到達。他定期去好友愛默生家吃晚飯。每個周末,梭羅的母親都會給他送來新鮮出爐的糕點。歷史學家理查德·扎克斯總結得好——“望周知:那位‘自然之子’會在周末回到家,把家里的曲奇罐子掃蕩一空”。它揭示了一個真相:被我們奉為偶像的人,往往活得沒有那么傳奇。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建議是錯的,只意味著他們也是人,你需要有所保留地對待他們說的話。
“網紅”的生活顯得那么光鮮亮麗,是因為他們用社交媒體的墻膩子蓋住了他們中彈后的彈孔。要是梭羅生活在照片墻的時代,他或許會在親手蓋的小木屋門口自拍幾張,但是不會拍下自己大嚼母親送來的新鮮糕餅的樣子。
網絡消弭了我們與偶像之間的距離。它允許我們追蹤偶像的一舉一動,不斷提醒我們與偶像的差距有多大。你艷羨的是他們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的生活,但那種景象跟他們真正的生活并不一樣。事實上,沒人會花那么多時間去看印象派畫作般的夕陽。
當我們只把別人生活中的零星片段截取出來跟自己的生活做對比時,我們就掉入了陷阱。你想要像她一樣富有,可你多半不愿像她一樣每周工作80 小時;你想要像他一樣健碩,可你多半不想要那副酷帥外表背后的嚴苛飲食與鍛煉。與他人競爭時,我們用他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我們想要跟他人一樣——但要比他們更好。結果就是,我們的生活變成了一場痛苦的零和游戲,任由我們與他人之間的距離來決定我們對自我的感受。
要擺脫我們與別人比較的心態,最好的辦法就是活得真實。“真實”二字已經被人用到俗濫,意思都快變味了。我所說的活得真實,意思是根據你自己的標準過一生,而不是根據其他任何人的標準。
我一直羨慕梭羅,直到我意識到自己并不想過他的生活。我一點也不想住在一個沒水也沒暖氣的小木屋里,我也不想要蚊子包、萊姆病和毒藤。下一次,當你聽到某些人精彩絕倫的人生自述,禁不住想把他們奉為偶像時,就想想梭羅吧——他在大嚼媽媽烤的甜甜圈。
(攸寧摘自《為自己思考:終身成長的底層邏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張云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