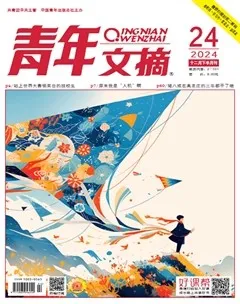Emo時,去爬一座山

一
要怎樣去形容四姑娘山呢?大概是馬糞混著淤泥的沼澤、散發怪味的熱水、漏風漏雨的帳篷、從凌晨2 點就開始下的大雨、被馬馱丟的板凳、被露水浸濕的冰冷手套……
四姑娘山的美呢?幾乎沒見到。
“長穿畢”(全稱為“ 長坪溝穿越畢棚溝”,是從四姑娘山 長坪溝穿越到畢棚溝)翻過埡口的那天,大雨瓢潑。埡口的最高海拔4600 米,從營地爬升800 米。可能是因為那天我晚飯吃得太飽,血液都流向了胃,我感覺頭昏腦漲,心臟狂跳。
凌晨2 點出發,我很快就被大部隊落下了。向導嫌我太慢,每走一段就停下來抽根煙,居高臨下地望著我。
天地都是黑色的,人在黑暗中的視野是那么局限。除了腳下一米的距離,我什么都看不到,既看不見山頂有多高,也不知道前路有多漫長。
起了霧的夜,不是黑色的,而是由成千上萬個白色的小水霧顆粒組成。夜晚是白色的。
燈光像是一柄沒有焦點的利劍,照不遠,看不清。于是偌大的天地縮成了孤身一人的我。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我,只有往前的一步又一步。
我問向導:“走了多遠了?”他說:“有欄桿的路走完了。”
我上氣不接下氣地問:“這算什么計量標準?”他沉默著悶頭向前跑。
我在絕望中口齒不清地問:“走了三分之一了吧?”他冷冷地拋下一句:“好遠了。”
就算他總是信口胡謅,我仍孜孜不倦地向他提問。在這樣的黑夜與沉默中,有人蓄意哄騙你,怎么不是一種煞費苦心,怎么不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呢?
向導是黑暗中唯一可見的一束光芒,像是燈塔,像是宇宙中孤獨的衛星。我像是貪婪的鬣狗一樣撲向他的身影。
我的眼睛被雨水迷住了,仰起頭,雨水順著臉頰流進耳朵。我說:“走不了了。”
當然,我知道,翻長穿畢的埡口不存在“走不了”的說法。翻過這座山是最簡單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因為后退就意味著要走28 千米的泥路,而往前,只剩800 米的爬升。
雨越來越大,我感到越來越冷,身上的濕衣服太沉了,像是一座大山,我害怕自己一停下來就站不起來,只能硬著頭皮,靈魂出竅般地爬。6點登頂時天才蒙蒙亮,本應最有意境的藍調時刻被籠罩在濃濃的霧氣中,我仿佛置身幽暗的海底。
從上山到下山,我最終花了10 小時才完成。
快結束時,我看到同行的人在山的那邊露出了頭頂。就是這兩個萍水相逢的人“心懷不軌”,勸說我在走完長穿畢之后,跟著他們一起去登頂二峰。
我心中充滿了怨恨,朝他們大喊:“不去二峰了,下山就回家。”
二
兩天后我卻食言,住進了二峰的大本營里。依舊是凌晨頂著雨出發登頂。二峰頂峰5276 米,從大本營爬升1千米。
我很疑惑為什么要凌晨出發登山,漫長的白天,大好的陽光,非要白白浪費不可嗎?我問向導,他也只是說:“晚上登山剛好看日出嘛。”
站在峰頂的時刻,我以為我會激動,會覺得自己不可能被打敗,會發出“一覽眾山小”的感嘆,但是沒有。我疲憊、腳痛、寒冷,一心只想下山,一絲多余的雜念都沒有。
我以為我會看到絕世的風景。比如,初生的金光從云層后面露出頭角,四姑娘山的各個山峰沐浴在永恒的金色之中。
但是沒有。山的那邊還是雨,除了黑色,什么都沒有。
從頂峰到大本營的下坡路,我有很多欲哭無淚的時刻。不是因為登頂的激動,而是被凍的。腳下無路可走,到處都是亂石。我在一路上摔了一跤又一跤,好在衣服里吸滿了水,我變成了一塊海綿,每次跌倒不過是從衣服里擠出一些水來,傷不到我分毫。
我原本以為登頂是最難的事,但是我錯了。從頂峰到大本營的7 千米快速下降才是真正的考驗。后來我發現自己又錯了,從大本營到四姑娘鎮15 千米的緩慢下坡,才讓人心如死灰。
從二峰到四姑娘鎮,從凌晨2 點走到下午4 點,14小時走了將近30 千米距離,海拔上升1 千米,下降2 千米。
我們一致同意登頂二峰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真正的困難是漫長的下山,山的那邊依舊是山,渾身的重量頂在腳尖,鞋陷在馬糞中拔不出來,褲腿上濺的泥斑層層疊疊,像在嘲笑我的渺小。
回程的車上我在馬糞的臭氣中沉沉睡去。醒來后才發現,我十指的皮都掉了。
什么時候愛上運動的呢?大概是從精神狀況不穩定開始的。從3 年前開始,我在上學和上進之間選擇了上山。山是我的庇護所,我像一個絕望的“受虐狂”,企圖在身體上受苦,以求緩解精神上的彷徨。
雖然我最初就想爬到山上來逃離自我,但最終發現自我也跟了過去。如果一定要嘗試去解釋爬山對我而言意味著什么,那就是我在精神的自由落體中企圖尋找對自身的控制,不為爬多高,把握住自己就是全部的意義。
因為站在山峰的那一刻,我的焦慮全部消失了,仿佛天地間只剩下一個完整的我,自由的我。
(余娟摘自《視野》2024 年第20 期,朱星圖)